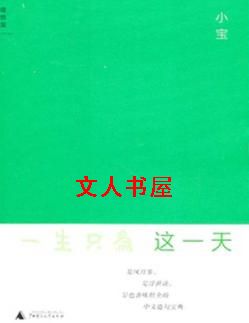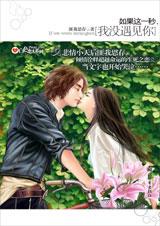这一代人的怕和爱-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献身于偶在个体的爱欲的“酸臭”与献身于革命的粗鲁,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故事中发生了一场历史性遭遇,并以无产者气的粗鲁羞辱贵族气的“酸臭”告终。它是否暗示,那场被认为“解放全人类”的革命以灭除偶在个体的灵魂和身体用最微妙的温柔所要表达的朝朝暮暮为目的呢?
我很不安,因为我意识到自己爱上了冬妮娅身上缭绕着蔚蓝色雾霭的贵族式气质,爱上了她构筑在古典小说呵护的惺惺相惜的温存情愫之上的个体生活理想,爱上了她在纯属自己的爱欲中尽管脆弱但无可掂量的奉献。她曾经爱过保尔“这一个”人,而保尔把自己并不打算拒绝爱欲的“这一个”抽身出来,投身“人民”的怀抱。这固然是保尔的个人自由,但他没有理由和权利粗鲁地轻薄冬妮娅仅央求相惜相携的平凡人生观。
我用“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和对这场大事的私人了解来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种经历和了解是片面的,世上一定还存在着别一种不同的革命,只是我没有经历过。“史无前例”的事件以后,我没有再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的形象已经黯淡了,冬妮娅的形象却变得春雨般芬芳、细润,亮丽而又温柔地驻留心中,像翻耕过的准备受孕结果的泥土。我开始去找寻也许她读过的那“一大堆小说”:《悲惨世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白夜》、《带阁楼的房子》、《嘉尔曼》……
这一私人事件发生在一九七五年秋天。前不久,我读到法国作曲家Ropartz的一句话:Quinous dira la raison de vivre?(谁会告诉我们活着的理由?)这勾起我那珍藏在茫茫心界对冬妮娅被毁灭的爱满含怜惜的这段经历,我仍然可以感到心在随着冬妮娅飘忽的蓝色水兵衫的飘带颤动。我不敢想到她,一想到她,心就隐隐作痛……
一九九六年三月
香港
湖畔漫步者的身影
——忆念宗白华教授
二十世纪的岁月已逝大半。那些随这个即将成为过去的世纪而逝去的老一辈学者们,留下了什么样的风尘身影呢?
如今,学术界已开始回顾那些与这个不那么称心如意的世纪同龄、从大灾大难中过来而又悄然逝去的一代汉语学者。这一代汉语知识分子被冠以“五四”一代的桂冠,由此标识出他们曾经有过的意义追寻。熊十力、金岳霖、陈寅恪、唐君毅、梁宗岱、朱光潜、宗白华……无数“五四”一代汉语知识分子,曾经以自己青春的激情,凭依学术研究的手段,反抗过在这个世纪中发生的意义毁灭和意义颠倒。对于半个多世纪以后出现的“四五”一代汉语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前辈——“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形象是亲切的。然而,这两代知识分子毕竟是两代人。
一个有趣的、也是“四五”一代知识分子恐怕无法回避的问题是:现代汉语知识分子在反抗历史中的意义颠倒时,历史颠倒过他们没有呢?知识分子在精神上与历史这个恶魔的搏斗,究竟谁输谁赢?这一问题涉及到学术是否应该或必得屈从于历史,是否应该或必得把决定世界的意义形态的决定权拱手让给所谓的历史。这一问题当然也不能掩盖或取代另一问题:现代汉语学者在反抗意义颠倒的同时,他们自己是否曾颠倒过意义秩序。
这些都不过是些空话、大话,无聊得很的问题。区区一介书生,怎能与历史相提并论。他们的精神和人格至多不过是历史的点缀,历史自走自己的路。一介书生们的意义追求,历史自会有评价,尽管糊涂书生并不知道这历史为何许人也。据说,只有那些主宰过几代人的命运、制造过无数人的悲欢离合的人,历史赐给他的身影才最庞大。
比起那些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来,宗白华教授留下的身影过于淡薄,比起其他著作等身,有宏篇巨制留世的学者来,他的著述明显过于零散,没有一部部头稍大的作品传世。在书籍淹没人灵性的当今世界,可有诚挚、透明的心性一席之地?
宗白华教授留下的身影不庞大,对我来说,却非常亲切。宗白华先生已逝去一年,他的风尘身影仍然时常倾近我,留伴在我身旁……
一
我刚进北大就听说,宗白华教授喜爱散步,尤其喜爱漫步于啸林湖畔和文物古迹之林。随着清丽飘洒的《美学散步》问世,这位美学大师作为散步者的形象更活龙活现了,仿佛宗白华教授真是清林高士一类人物。
一天,我例行去见他,不巧未遇。宗师母告诉我,他上外面走走去了。我回转去,刚到未名湖,就看到宗老先生身着旧式对襟布衣,肩上搭着个小布袋,拐着手杖,正匆匆往家走,看上去,他显得十分疲累;尽管他对我说出去散了散步,可我却看不出一点散步者的心态。
所谓“散步”,不管是从日常生活来讲,还是就隐喻而言,都具有清散悠闲的意味。无论如何,《少年中国》时代的宗白华绝不是散步者的形象;游欧回国后的宗白华,也不是文物艺品之林的散步者。《少年中国》时代的宗白华对儒道哲学的尖锐抨击,在宗白华成熟后的思想中虽已销声匿迹,此后看到的大多是对孔、庄人格的赞美,这并不意味着他已改宗“散步”哲学。明则“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隐则“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少年中国》时代的宗白华对生活的充实和深挚的巨大热情,依然不减当年。
如果说,晚年宗白华的形象是“散步者”形象,那么,这种形象是否真实;如果这位曾立下夙愿要“研究人类社会黑暗的方面”的诗人和学者,在晚年改宗了“散步”哲学,那么,这种情形是如何发生的,这些至今都仍是问题。
作为美学家,宗白华的基本立场是探寻使人生的生活成为艺术品似的创造。这与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有所不同。朱光潜乃是把艺术当作艺术问题来加以探究和处理,其早年代表作《文艺心理学》《诗论》、以及晚年代表作《西方美学史》——尤其是该书的基本着眼点和结束语,都充分表明朱光潜先生是一位有渊博学识的文艺学家。但在宗白华那里,艺术问题首先是人生问题,艺术是一种人生观,“艺术式的人生”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宗白华,朱光潜这两位现代中国的美学大师,早年都曾受叔本华、尼采哲学的影响,由于个人气质上的差异,在朱光潜的学术思考中虽也涉及一些人生课题,但在学术研究的基本定向上,人生的艺术化问题在宗白华那里,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少年中国》时代的宗白华,面对时代的混乱、人心的离散、民族精神的流弊,深切感到人格的改塑乃是最为首要的问题。要改造“机械的人生”、“自利的人生”,必须从生命情调入手。这些论点明显带有对现代性问题作出哲学反应的意味,恰如本世纪初德国生命哲学(狄尔泰、西默尔、奥依肯)是作为对现代性的精神危机问题作出反应而出场的。
毫不奇怪,本来就重视生命问题的青年宗白华,在接触德国哲学时,很快就与当时流行的生命哲学一拍即合。看得出来,青年宗白华熟悉西美尔的著作,在他留欧回国后的主要论文中,有很明显的斯宾格勒哲学思想的影响痕迹(例如他十分强调的空间意识这一概念)。严格他讲,宗白华先生首先是一位生命哲学家,而且,是中国式的。
华夏生命哲学与日耳曼的生命哲学,毕竟有实质上的差异。现代华夏式的生命哲学,就个性突显者而言,王国维之后,乃是宗白华。
二
五十年代初,全国各主要大学中教授外国哲学的教授,统统被调集到北大,改造思想。北大的哲学系师资,顿时显得极为雄厚。宗白华教授从南京来到北京,从此就再也没有回返他从小生长、学习和从事教育的江南。
最初,宗先生住在燕园南阁,伴着孤灯一盏,潜心研读他喜爱的康德。几年过去,热热闹闹的美学主客观立场大争论开始了。对这场牵动许多美学家的立场的争论,宗白华教授并不那么热心。木过,他也多少采用了一些客观论的说法。看得出来,他觉得客观论并没有什么不好。
让人感兴味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宗白华开始称颂不那么客观的庄子在山野里散步,并表明了自己的散步态度:散步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可以偶尔拾得鲜花、燕石,作为散步的回念。
给宗白华的思想挂上客观论或主观论的牌子,会显得极为可笑。对他来讲,这些都是身外之名,与生命无涉。生命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有此一说吗?”
宗白华真的开始散步了?为什么他偏偏在这个要求“统一思想”的时代提出“散步”哲学?“散步”与学术有什么关系?
宗先生家的书房里,挂着各种画,其中有两幅静物。一次,我同宗先生聊起静物。一谈到艺术,他总是滔滔不绝,但也相当简练。他说:“静物不过是把情感注入很平常的小东西上;其实,中国早有这种传统和潮流,宋人小品,一只小虫、小鸡,趣味无穷,这发端于陶渊明把自己溶入自然的精神,不是写人、写事,而是写表面看来平淡无奇的自然物,在小品、小物、小虫上寄托情深。西人以往重历史和人物,近代才重静物;中国早先重个人,后来就重历史,至今如此,而且,中国历史上不重视文化史,只重政治史,二十四史都是政治斗争史。”
“五四”一代的学者,许多都在自己的后半生或晚年转向对汉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美学史、文学史)的研究,这里大概多半有某种“移情”心态。虽然他们早年大都受过西方学术的训练,但毕竟是中国人。即便是毕生主要研究西方美学的朱光潜先生,实际上依然是“现代儒生”。
宗白华先生晚年对中国美学思想的系统研究,明显寄托了无限情深。《三叶集》中的宗白华曾表示要“仍旧保持着我那向来的唯美主义和黑暗的研究”,这让我想知道,唯美主义与对黑暗的研究会有何种方式的连结。但早在三十年代,他就已经彻底转向了唯美主义。中国式的生命哲学总是高超的……
三
宗先生晚年一直住在北大朗润园,那里湖光山色,景致清丽。不过,宗先生的居室在楼房的底层,光线不足,室内十分黯淡,书房常让我想到卡夫卡在致女友的信中曾赞美过的那间地下室。不同之处在于,宗先生的书房四周,挂着或摆着各种艺术品,使这间昏暗的小屋显出某种神秘的调子。我常思忖:这是否恰是唯美与黑暗的关系的象征呢?
宗先生觉得,通过诗或艺术,微渺的心才与茫茫的广大的人类,“打通了一道地下的深沉的神秘的暗道。”这是中国式的人格美,宗先生没有充分注意到,一千九百多年前的一位拿撒勒人,曾用生命和血启示过另一种微渺的心与茫茫人类的沟通方式。
宗老对中国式的人格精神美的


![[HP]瞧这一家子封面](http://www.xntxt2.com/cover/19/1991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