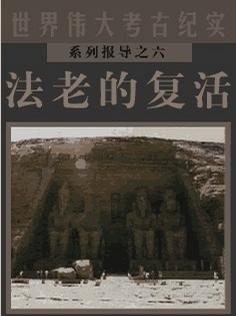复活的度母 作者:白玛娜珍-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琼芨和雷的私情很快传遍了全校。一时间,校园里的墙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大字报。雷的一些琼芨没读过的诗也被贴出来,作为反革命言论和不满情绪。一夜之间,雷成了强奸犯、反动右派分子。
这时,琼芨挺着一天比一天高的腹,低头躲闪着四面八方投来的哄笑和羞辱。夜晚,她孤单地躺在宿舍的床上,感到胎儿欢愉地在腹中翻动,一会儿滚到左边,把左腹顶得鼓鼓的,一会儿小脚又踢右腹。“好了嘛,别闹了,人家要睡了。”她悄悄摸着肚子,小声说。还是少女的她,母性的本能被肚子里的胎儿触动着,双乳肿胀,像充盈着乳汁,对雷的思恋,淡薄起来。
雷躲藏在他的角落终日惶惶不安。琼芨的身体,她裸露的模样,她在他的大床上走来走去或转半圈。他在床下望着她:被胎儿撑起的小腹,绽开了淡淡的纵向的纹路,像细风在湖面上的涟漪,手去抚摸时,像是透明的,珍贵的宫阙里如意珍宝般的圣子……他眩晕了,他的手在颤栗。这个来自神秘喜马拉雅的少女,他不敢以为那个圣子是他所为。
琼芨对他说:“我要带他回西藏。”她想孩子在直射的阳光下,她要在他身上涂抹掺了甘露的油,采高山香柏,为他熏染童身以及黄金雕琢的经文,飘荡在他纯净的眸子里。
“跟我去医院吧,”雷说,“你还只是个少女,这样会毁了你的一生。”
“不,我不去。”她害怕起来。害怕雷,怕这个布满坟茔的地方埋葬她唯一的亲人。当她从内心断绝,与母亲、继父、姐姐曲桑姆,孑然漂泊着,她感到今天在这世上,就要降临的,她的骨肉,血脉相承,她至亲的人儿……
雷,哭了。雷蹲在门后,手撑着脸,像头系白毛巾的那些个找不到水源,没有肥沃的土地的山民,泪水和鼻涕纵横,拍着地,绝望地哀号:“这下完了,全完了……”
琼芨惊诧地望着那个男人,想着他写的那些美丽的诗句。她跳下床,从他抽屉里翻出来,她给他看,要他看她爱慕过的诗人的句子。雷接过去,他看了几眼,突然将纸撕成碎片向空中掷去。琼芨怔住了,她伸出手想要去接住,缓缓落下的像白雪,雪花儿上的字迹像是不净的污渍……
4
雷走了。被下放到边远地区劳动改造。他的宿舍被查封,那张琼芨睡过的核桃木大床被拆散了送进了学校的伙房。没过几天,琼芨也被送进了医院。学校安排她坠胎。
这时,孩子在琼芨的腹中已长出了黑黑的眼睛、鼻子、耳朵和小嘴,还长了一头浓密的黑发,毛茸茸扎得琼芨常感到胃那儿痒痛痒痛的。再过几个月,孩子就要出生了。孩子开始用他的小拳头小脚不安地轻叩母亲。他感到了母亲的惊恐与绝望,母亲的哭泣和抽搐令他住着的小暖房像糌粑口袋一会儿勒紧了令他喘不过气,一会儿被揉搓一般,长长的脐带绕住了他的颈,他无助地哭喊着,奋力想出来……
然而,命运早已被注定。央珍和另外几个同学协助护士把琼芨压在床上,任凭她怎样挣扎,毒液已被一滴滴注入她的血脉,驰向她腹中那无辜的婴孩儿。凌晨三点多钟,琼芨感到自己像被屠宰的母牛,在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中,孩子终于被驱赶出来了。
护士们惊呆了,这是一个多么漂亮的男婴啊! 胖胖的,长着长长的睫毛,他浑身青紫,脐带紧紧勒住他的小脖颈,他还没死! 琼芨不顾一切地夺过来抱在怀里,但孩子张了张小嘴,吐出最后一口气,在她怀中渐渐僵冷……
小护士掉眼泪了,央珍也哭起来。琼芨紧抱着死婴,下身的污血像溪流一样流淌着,她昏了过去,迷乱的神思追寻着亡灵,想要与孩子再相遇……
第九章
1
我不由地哭泣。这人世间,还有什么比母亲失去亲子更痛苦啊! 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如果……我死了? ”我脱口说,“黛拉,你没必要害怕,不许流泪。”
黛拉惊异地望着我,又看看旺杰。
“总有一天,我会自己了断! ”说着,我又干了一杯酒。我们醉了。
“快凌晨四点了,茜玛,我们回去好吗? ”黛拉恳求道。她是胆怯了? 我的手腕上是刚愈合的伤,嫩嫩的呈粉色。
“再坐一会儿。”我说。街上华灯通明,拉萨这时已是一个疲惫不堪,没有夜,没有睡眠和梦的都市。年轻人聚在街两旁的酒吧里纵情畅饮,老人牵着狗,也在街上,整夜地转经。
“死于意外,老死、病死……”旺杰说着一掌拍到桌上,
“他妈的,死在哪里? 根本就没有死! ”
“不过是一种短暂的离开。”我故作平静地笑道。泪水噙满了我的双眼。
“但怎么可以?!”黛拉坐在我和哥哥的对面,一脸的迷惑。她穿得很薄,像是冷,双臂交护在胸前:“自杀,会使心从死亡里坠入地狱! ”
“哈哈哈! 心? 地狱?!”旺杰笑道,“老套! ”
“感受一下地狱的酷怎么啦? ”我睨了她一眼,“生生死死,反正没完没了。”
黛拉不吭气。我望着她,我想,比如这张木桌子,只是某棵树的躯体。这杯美酒,是葡萄离开藤蔓和土壤的复活之灵。而所有的一切,像飘泊在水里日月的光影,谁能说活着或已死,生命就像一场虚无的盛宴。
我不禁感到莫名的狂喜。我想呕吐。
这时,头发鬈曲,印度美男子一般的洛泽,一直踟躅在拉萨的街上,推开一扇又一扇门,进去又出来,在缭绕的烟雾和袭人的酒香里,他要找到我,美艳的茜玛——他听说那晚,她离开以后,躺在家里的床上,切割自己的手腕。流淌的鲜血像红色的花瓣,又像夕阳拖着的长长的尾巴。茜玛快死了,她还那么年轻,生命又要从头再来。那时,她不想再见这个令她升起幻想的男子。无端的幻念比生死轮回更令人绝望,茜玛要离开他。
夜半时分,洛泽终于找到了。在这个城市龌龊的角落,他跌趺撞撞地闯了进来。他是多么的英俊啊,他的身上,印度洋的暖风或许还有某个热带女人的气味……他看见了我,茜玛。他从来没有如此愤怒过,他以为,他所有的颠沛流离,是为了拉萨那虚构的圣洁……他粗野地抓起立在门边的一个垃圾桶,他接受过的西方文明的教化转眼化为乌有,只剩下暴力。垃圾桶从黛拉的左肩上飞过去了。纸屑和垃圾从半空飘了一些在我们的桌上,我嚼着口香糖。
“你想干什么?!”旺杰冲上去。他们要打起来了。我的情人和我的哥哥。而他们的血,流的血会是什么颜色? 像稠稠的奶汁或黑血如炭……我紧张起来,拉萨在他们自相残杀的血垢中,魔界的罗刹即将复活吗——我张皇地拿起一个空酒瓶,对准桌子的一角狠劲敲碎了,我宁愿用尖利的玻璃齿狠狠地自残,刺进我自己的血肉……
桌上的残迹被凝合在一起,红里透黑。洛泽惊诧地转过身,呆呆地望着我,慢慢坐下去,垂下了头。后来,他走了。他还要去往别处,瑞士、加拿大或北欧……
黛拉弄来一瓶云南白药。
“走吧,我们回家吧。”黛拉求旺杰。
“你要走你就走,”我一字一句地对黛拉说,“记住,你只是我嫂子,仅此而已。”
“我们一起来的,也该一起走。”黛拉小声说。但假如,假如她撇下我和哥哥……她坐着没动。我又说:“还坐着干吗? 没人留你。”哥哥沉默着。我和黛拉,他心里无法平衡的感情。我感到阵阵眩晕。周遭的一切都像是离开了原本的位置,无序而混乱。
“去医院看看去! ”哥哥说,“包扎一下! ”
我痛得发笑。我趴在桌上。
“看她脸色都变了。”我听见黛拉悄悄说,“洛泽为什么对她那样? ”
“茜玛不愿理他。”
“那茜玛为什么用酒瓶扎自己的手? ”
“走,疼得不行了! ”我站起来,浑身有些颤抖起来。黛拉上前扶住我,我感到我快要痛昏过去了。
我执意要去一个小诊所。
诊所很偏,在一处街角。青蓝的日光灯下,某个无照行医的汉人像是从地缝里钻出来的,身上有一股臭味。他说:“她肉里刺进了玻璃,要打麻药。”他的口音很奇怪。我咬咬牙,我朝他摇手,我不要用麻药,坚决不用。
“这不行,不行。”他把刚穿上的白大褂脱下来,“不打麻药不敢做不敢。”
“给你二百元? ”我说。
“好嘛好嘛,但痛得很,你能忍住吗? ”他有些不相信。
“茜玛,你就打麻药吧。”黛拉哀求我说。
“一点玻璃渣子,不用。”我笑道。
“茜玛,别逞能! ”旺杰怀疑地说,“为什么不要麻药? ”
“还站着千吗? 嫌钱少了吗?!”我朝江湖医生大喊。
他开始了。一脸惶恐,抖抖嗦嗦地拿起锋利的刀片划开我的中指,再用镊子从血肉模糊中挑出一粒粒玻璃渣。疼痛使我面目扭曲,神智恍惚。疼痛原来是这样,如此强烈,令我亢奋和疯狂。那么死,是否一如那生命的高潮,潜藏在欲望深处……
2
所以,洛泽,后来,在没有你的路上,当我走着,或又会遇见你和与你相似的人。
你举起长长的手臂,你有了新的主意:“下面这样,”你瞧瞧我,得意地笑道,“我们大家:国外的藏族说藏语时不许夹杂英语和印第语,你们,”你指指我,“不许加汉语,要不就罚谁喝酒! ”
“哦! 哦!ok!”大家齐声起哄道。
“开始! ”
好一阵,我们和你们都不吭声,害怕一开口漏嘴,我在心里暗暗连续着一段完整的藏话。
“您,您今天非常,很漂亮,白吉啦。”还是洛泽的朋友先开口了。他说藏语的尾音朝上扬得厉害,怯生生的。我的女友白吉吃吃笑起来,不知该回答什么好。
洛泽端起酒杯准备罚她了。
“谢谢。今天天气不错? ”哇! 这家伙! 外面天都黑了! 她分明是用藏语生搬硬套。
“罚一杯罚一杯! 哈哈哈……”洛泽和他的朋友们高兴坏了。
“他本来说得就不对。藏族男女之间不这么表达。比如我们现在喝酒玩,他该说‘我要敬您一杯酒,白吉啦’才合适嘛! 白吉你快开口呀! ”我急了。
“把刚才说的再重复一遍! ”洛泽对我说。
“为什么? ”
白吉捂住脸在笑。天哪! 我最后一句对白吉说的是汉语!
“都怪你! ”我连连笑骂她。
“罚酒罚酒! ”洛泽把酒倒满了。
“no no!”
“哇,他说了英语啦! ”我们大笑起来,我们拉平了!
游戏又重头来,但再玩下去大家都顶不住了,纯粹的藏语式的交流,显得脆弱虚假和强求。让这些见鬼去吧! 放响音乐,让我们狂欢纵饮,心贴着心,感受彼此的温度。多尽兴! 多快活! 我们必须快活。有一句谚语说得很好:自己不享乐,别人就要让你吃苦……而我们,好比竹筒里的蛇,还有别的出路吗? 所以,洛泽,当我醉了。又醉了,你扶着我,带我去吧。我不在乎,临时的憩所,而不想背负,空渺的家园。
你走过来,点燃烛火,你训练过的体格,你从那个国度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