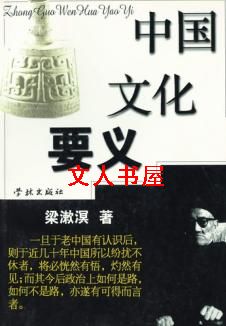两岸三地文化名人自述:穿越美与不美-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挖河的时候,我受了批评。挖河挖到十几公尺深的时候,泥土的颜色都变了,绿色的、黄色的,漂亮得不得了!但是挖到那么深的时候,泥土就很硬了,要打钎,打一个个的洞,灌水进去,过一个晚上,等裂缝松了,把泥土一大块一大块地撬出来。结果挖出了很多化石来,化石是完整的,那么粗那么长,不知道是什么从来没有见过的动物。我说这不得了,马上停工,这也许是史前动物呢。要报上去让专家来鉴定。从下报到上,通报到最高指挥部,结果我得了一个“阻延工程进展,散布不利谣言”的罪名,不过因为工程紧张,都没有顾上处理我。那些化石被挖出来一车车倒掉,我只好自己收集,拣最好的收集,收集了三十公斤的化石,放到自己的行李里面。工程还没有结束,我争取了一次到上海出差的机会,辛辛苦苦地把那批化石带到虎丘路那个博物馆,打算捐给博物馆。结果那里的副馆长连头都不回:“什么东西?也拿到我面前来看。”我把化石拿过去,“这种东西,我们这里有的是,走走走!”不容我解释,那个副馆长就把我轰了出来。但是直到现在,我走了那么多的博物馆,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好的化石,但是当时没有人知道那些化石的价值。那是陈胜吴广起义的地方,化石的历史肯定要比陈胜吴广起义的历史要长。
后来我把化石拿到中药铺,结果中药铺的好喜欢:没见过那么好的龙骨!结果我就把那些化石当作龙骨卖掉了,卖了70多万人民币(旧币)。当时我的工资也不过一个月三十多万人民币。把河挖好之后,我又被调到另外一个工地,也是在皖北。后来又被调到苏北去。
3
在内蒙古,因为大雪阻路,煤运不进去,天寒地冻,很多人都冻死了。我拆了一个摇摇欲坠的木桥当柴火,我想河水已经冻到底了,要化冻至少也要到六月,那时我砍一些树再搭好就是了。我以为我在挽救同志生命,结果被冠上了“破坏交通”的罪名,“破坏交通”是现行反革命,很大的罪。我被关在一间周围没有人烟的小房子里,门也是透风的,里面只有一个炕。每天晚上,狼就围着小房子,哇哇地叫,狼叫声真是可怕。这小房子以前不知道是做什么的,我垒了炉灶,当然没有煤,要自己收集干草,不然零下三十度的严寒,是要被冻死的。他们每两个星期给我送一次吃的,第一次给我送来了一块很大的“花岗石”,我问:“这是什么?”送东西的人答:“豆腐。”豆腐要拿斧头砍着吃,幸好我那时候年轻。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倪匡:被一阵风改变的人生(3)
我是骑马离开我所在的单位的,当时我的单位要组织一个法庭审判我,所以我要逃走。一个朋友给我偷了一匹马,朋友告诉我:骑着马一直往北走。我说,往北不是蒙古游牧部落吗?朋友说:就是要去游牧部落呀,他们一定会收留你的。到了那里,你学蒙古话,过两年,改个蒙古名字,你就变成蒙古人了,娶个蒙古姑娘更好。那时候你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出来,不会再有人管你。我就骑着马一直往北走,当时是五月中旬,抬起头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北斗星。从九点钟走到十一点钟,忽然天阴了,下了一场大雪,东南西北再也无法分辨,只好随着马乱走。大概走了几十里路,天快亮的时候,走到了一个小火车站,正好有一辆火车开来,我也不知道火车是朝南还是朝北,就上去了。没有目的地,只想赶快离开就好。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个小火车站是什么地方。
上了火车,没有地方可去。一想,大哥在鞍山,不如到鞍山好了。到了鞍山,大哥问我带没带档案,我说没有,都被我烧掉了。当时我想我一个人没有地方生活了,档案还有什么用呢,一大包档案就被我放到火炉里烧掉了。原先我还真不知道我有那么多的记录:什么地主思想啦,什么小资产阶级思想永不改变啦,什么目无组织啦。真是吓死人!大哥又问我有没有介绍信,我说介绍信还不好说,我自己写一个就好了。就这样,报了一个临时户口,我在鞍钢作了两个月的小工。每个月的工资也不低,有四十多块人民币。那时候旧币已经改成新币,是第一套新人民币。
身边有了一点钱,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就想到上海看看再说。因为父母在1950年就到了香港,所以在那时就已经想到了最终目的是要到香港来。1957年6月,我到了上海,那里鸣放正是最火热的时候,也是环境宽松的时候。 7月份,反右就开始了。当时上海莫名其妙地聚集了各地的年轻人,大家在一起商量怎么办,忽然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我有办法把你们带到香港去,相信我的就参加,费用只能用港币支付。”那时候哪有港币呀,就有人问他到香港之后再给行不行,也不知道他怎么判断的,反正有的行,有的不行。我属于可以的那一类,然后我们约定时间在北火车站集合。
上了火车,一路到了广东,到广东之后,又到了一个不知道是哪里的临海的小地方。那人把我们七八个人弄上一艘很窄的运菜的船,我现在都不知道我们七八个人是怎么挤进去的。我们白天上船,到了天黑的时候才把大家放出来透透气,远远地看到海面上有灯光,又马上挤进去。再下船的时候,已经到了香港。
带我们到香港的那个人跟我讲:你不会讲广东话,独自不要开口,一句话都不要讲。他给了我一包黑猫牌香烟,告诉我有人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就拿烟假装抽烟,别人看到我抽黑猫香烟就不会怀疑。然后他问我我家在哪里,他把我送过去。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一天下着大雨,我们一起躲在楼底下避雨,等雨小一点就冒雨去了我的父母家,妈妈一开门看到我,吓了一大跳。从上海到香港,只收了一百五十元港币,还帮我拿了香港的身份证。这是我这辈子花得最值的一百五十港币。
4
到家之后,家中地方很小,妈妈马上带我去买了一张行军床,晚上打开睡觉,白天收拾起来。然后我就到处去找工作,做过很多杂工,最累的就是风镐,当时香港普遍的工资是一天三块钱港币,但是风镐可以达到一个小时两块钱。我身体好的时候,一天可以工作四小时,时间再长了就吃不消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倪匡:被一阵风改变的人生(4)
当时从各地来香港的年轻人非常多,我们当时联系到的就过千了,这种联络一直维持了二十年之久,这些人后来有的成了台湾大学的校长,有的成了著名的教授,有的成了很出名的出版商,大家各自忙,也就很少联系了。我喜欢看书,那时我跟他们说香港报纸上的那些小说我也会写,他们都不相信。结果我花了一个下午,写了一篇一万字的小说,投稿到《工商日报》。我是七月份到的香港,九月份写的那篇小说,十月份就发表出来了。前年我回来的时候,香港的记者真是本事大,竟然把那个小说找了出来。我自己看看:哇,这样规规矩矩的文章竟然也能写得出来。当时文章登出来,通知我去拿稿费,我以为只有十块八块的,结果给了我九十块钱。报馆的人跟我讲:“你的文章有一万字,但是我们删改了一些,剩下九千字,一千字十块钱,满意不满意?”我当然满意极了,问他们这样的文章还要不要,他们说需要的,让我继续写。我这才觉得原来写东西也可以做为谋生的手段。写一篇那样的文章,太容易了!
后来我就到处去投稿,从我第一次投稿到现在为止,从没有被人家退过稿。1959年,《文汇报》上面讨论一个小说,因为《文汇报》是一个左派报纸,他们拼命批评一个小说,我就为那个小说打抱不平,结果我的文章也被登了出来,我连稿费就不敢去拿。
写到后来,我经常给有家叫《真报》的报馆写稿,《真报》的社长找到我,他说:“你不如来我们报馆帮忙好了。”我说:“好啊,我反正没有事情做。”那时候的报馆很简单,总共五六个人,一个社长,一个采访部主任,旁边就是字房。我问社长:“我做什么?”他说:“什么都干,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好了。”比如说采访部主任要一杯咖啡,我就跑下去给他买;字房里说副刊少三百字的影评,我马上就要写三百字的影评,尽管电影连看都没看过;甚至社长出去应酬,要六百字的社论,我也要马上写六百字的社论。报馆一个月给我一百一十块钱,可以维持生活了。当时我半个月发一次薪水,五十五块钱。那时候字房的工人生活很苦,每个月要靠借高利贷生活。我看不过眼,就跟字房工人说:“你们真是要借的话,向我借好了,我不要你们的利息,甚至也可以不要你们还。”高利贷很厉害的,借一百块钱,每天要还五块钱还一个月;还有一种是九赊十三归,就是你借一百块钱,他们只给你九十块钱,但是到了月底还账的时候要还一百三十块。我离开香港十几年,前年回来,走在大街上有人见了我就跟我拥抱,一报名字才记得他是当时报馆字房的工人。
当时台湾有个叫司马翎的很出名的作家,在《真报》上连载武侠小说,写着写着,稿子不来了。我就跟社长说:“这种小说,老实讲我写出来比他好。”社长不相信,我就说:“先续下去再说,因为他的稿子可能会来的。”续了两个星期,不仅没有人看出来,而且读者的反应好得不得了。后来司马翎来了,大发脾气:“谁敢续我的小说?”我说:“谁敢啊我敢。”司马翎和我同年,那年他二十来岁,他看了我续的内容,笑着跟我说:“续得很不错。”我说:“岂止很不错,简直是写得比你好!”司马翎气得要死。
倪匡:被一阵风改变的人生(5)
后来他不写了,社长说干脆你开一篇新的好了。我就开始写,三块钱一千字,一天两千字。简直太好了!你想想那是多么容易的事,半个小时都不用就可以写两千字!
这篇小说发出来之后,一个月内有四家报馆找到我,要我给他们写武侠小说。金庸差不多就是在这一年的年底找到我,让我给《明报》写。他给我十块钱一千字,每天写两千一百字。到了月底,我拿到六百三十块钱的稿费,我第一次拿到一张五百块面额的钞票。我和老婆拿着那张大钞笑了半天,商量着怎么办。我老婆要把它存起来,可是我却想把它花掉。当时在香港,我和我老婆两个人去饭店,五块钱可以要三个菜一个汤,白饭可以随便吃;去看电影,一张票一块半,我们两个人只要三块钱。一般人一个月如果拿到四五百的话,就是很高的工资了。那是在1960年,金庸的报纸是1959年创刊的。
《真报》是一个极右派的报纸,极端反共,《明报》则表示中立。有一次金庸在《明报》上说《真报》“只顾反共,不顾事实”。我写文章和金庸论战,说“我们既顾事实,又顾反共。”那时候《明报》创刊已经接近两周年了。有人开玩笑说:“你这样和金庸对着干,小心他不让你写稿呀。”我想那有什么关系,反正有大把的报纸让我写稿。《明报》两周年的时候,我去参加,查太太在宴会上大声问:“倪匡来了没有?他这样骂我们,还敢来吗?”我笑嘻嘻地说:“早就来了,就在你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