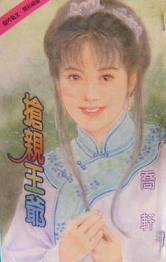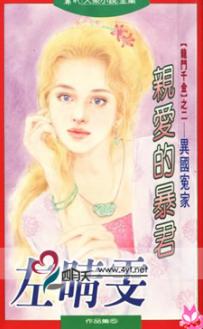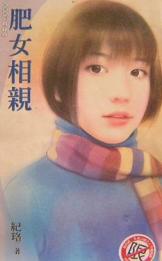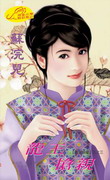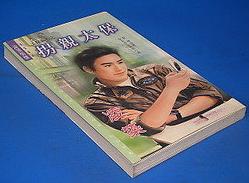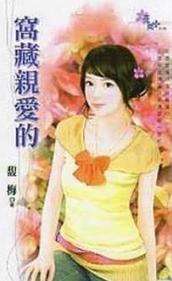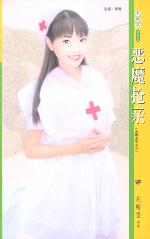老乡亲-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张大千擅长牛头筵
谈到吃牛头筵,宋子文任财政部时,偕税务署长谢祺巡视湘鄂赣
区海关统税情形,过经岳阳,当地统税所长李藻荪与彼等有旧,特请当
地名庖人刘旺福做了一席牛头筵宴客,并请当地驻军刘经扶军长陪
客,菜仅八簋二汤,均系出自牛头,鼎俎庖宰,肥酞调畅毫不腻人。宋
谢两人胃口均佳,恣飨竟日,羽觞尽醉,此后宋氏在沪每一谈及,仍念
念不忘也。
大干先生初次莅平,最好吃春华楼、济南春两家,多次邀我同席,
目的在邀我提调点菜。渠尝夸擅长牛头筵,俟选得上等材料,将亲自
动手,让我尝尝比岳阳刘庖手段如何,其后一别多年未晤。前数年渠
自海外回台,暂住云和大厦,某夕在台视看徐露演《二进宫》,又提起欠
我一顿牛头筵,此债非还不可。可是他迁居之后,一方面忙于布置新
居,又忙于绘事,牛头筵之约始终未实现,他已驾返道山矣。
北平书摊儿
在北平,读书人闲来无事最好的消遣是逛厂甸遛书摊。厂甸在和
平门外,元明时代叫海王村,清初工部所属的琉璃窑设在该处,所以改
名琉璃厂。从厂东到厂西门,街长二里,廛市林立,南北皆同。这些店
铺以古玩、字画、纸张、书籍、碑帖为正宗,从有清一代到民国抗战之
前,都是文人墨客访古寻碑、看书、买画的好去处。每年从农历正月初
一起,经市公所核准列市半个月:海王村里是儿童耍货,所谓琉璃喇
叭、糖葫芦、大沙雁,各种吃食如凉糕、蜂糕、炸糕、驴打滚、爱窝窝、豆
汁;灌肠小贩仿佛各有贩地,年年在原地设摊。居中是几家高搭板台
的茶座,居高临下得瞧得看,既喝茶,又歇腿;村里边边牙牙地区,就是
些像荒货,又像破烂古玩摊了。海王村外书摊大摆长龙,有些书店在
自己门前,设摊营业,有的是别处书商赶来凑热闹的,大致可分木版
书、洋装书两类,还有卖杂志、旧画报的。吴雷川先生在这种书报摊
上,买过八十八本全套的国学萃编;丰子恺收藏《点石斋画报》,就是遛
这种书摊补齐的。
好的宋元明清版本精镌的古籍,书店恐怕放在外面被风吹日晒,
纸张变脆变黄,多半把书名作者,写在纸条上,夹在别的书里。纸条垂
下来,给买书者看,如果中意,摊上招呼客人的伙计,就把客人引进店
里来了。
琉璃厂专卖讲究版本的书叫旧书铺,最有名,存书最多的有翰文
斋、来黄阁、二酉堂、经香阁、汲古山房几家。他们书的来源,多半是由
破落户的旧家整批买进来的,这一拨书里可能有海内孤本,也可能有
鼓儿词、劝善文,有的到手就能很快卖出去,有的压上三年五载也没有
人过问;年深日久,一家大书铺的存书,甚至于比一个图书馆还多还齐
全。旧书铺的服务,有些地方,比图书馆还周到,北平之所以被称为中
国文化中心,由北平旧书铺,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了。
旧书铺里,总有两间窗明几净的屋子,摆着几张书案长桌,凡是进
来看书的人,有柜上的徒弟或伙友伺候着,想看什么书,告诉他们,一
会儿就给您拿来;如果参考版本,他可以把这本书不同版本,凡是本铺
有的,全都一函一函地拿出来,任您查对;有的资深伙友,告诉他要找
什么资料,他佃还可以一页一页地给您翻查,如果有些书客人想看,而
本书铺恰巧没有,他们知道哪一家有,可以借来给您看。请想想,这种
方便,不管是哪家图书馆,不论公私都办不到吧!
看书时,抽烟柜上有旱烟、水烟,喝茶有小叶香片、祁门红茶;如果
客人想吃什么点心,客人掏钱,小徒弟可以跑腿代买,假如您跟柜上有
过交往,由柜上招待,也是常有的事。不但此也,您跟书店相熟之后,
酷暑严寒您懒得出门,可以写个便条派人给书铺送去,柜上很快就找
出送到府上;放上十天半个月,您买下固然好,不买也没关系,还给他
就是了,这就是北平书铺可爱之处。像南京夫子庙左近也有不少书
店,您要看了半天不买,他们绕着弯俏皮您几句损人的话,能把您鼻子
气歪啦!
清朝光绪年间所谓清流派如张之洞、洪钧、王仁堪、潘祖荫、文廷
式、盛昱、黄体芳、梁鼎芳、于式枚都是琉璃厂书铺的常客,既可多看自
己手边没有的书,又可以以文会友;时常有许多朋友不期而遇,凑在一
块儿研究学问,或是聊聊天。张香涛就是主张多往书铺看书的,他有
两部专讲目录学的书,初稿就是在二酉堂写出来的。翰文斋的掌柜韩
克庵,大家都叫他老韩,他对于目录学、金石学,精心汲古,搜隐阐微,
能令舒铁云、王懿荣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民国初年先母舅李锡侯在琉璃厂西门,把先外祖鹤年公累世收藏
的古籍金石整理陈售,开了一家汲古山房。陈师曾、樊云门、傅藏园、
沈尹默、瑞景苏、柯劭态,都是汲古山房常客。当时我想收集名贤书画
扇面一百把,半年之间不但收集齐全,而且部配好各式各样扇骨子,由
此可见汲古山房当年人文荟萃、朋从之盛了。
初来台湾时,台北福州街厦门街之间,还有几家书摊铺可逛,现在
如果发现那儿有一套或几本线装书,简直有如沙中淘金,掘到宝藏了。
来到台湾,令人念念不忘的,就是旧书摊了。
北平的人力车
提起北平的人力车,话可长啦,最早北平人叫它“东洋车”,天津人
叫它“胶皮”,上海人叫它“黄包车”,后来北平人把东字取消,干脆就叫
“洋车”了。
人力车问世之初,没有打气轮胎,而是硬胶带卡在车圈上的,所以
天津人一直叫它胶皮。早年先叔在世的时候,在清史馆供职,从舍下
到设在天安门左首的太庙,一直都是平坦的大马路,家里虽然有敞篷
和玻璃篷马车各一部,可是馆长赵次珊、总纂李新吾都是先祖光绪九
年癸未科同年,每天都是坐马车来馆,如果他自己也坐马车到值,怕人
家说少不更事,迹近浮夸,所以包了一辆人力车上衙门。
当时人力车都是死胶皮,拉车的又年长了几岁,反而在馆里博得
老牛破车的雅誉。先叔觉得以人力车代步,比起安步当车又高了一
筹,何况清史馆是个冷衙门,早点晚点到值也没什么关系呢!
过了没几年,打气轮胎的人力车大行其道,大家都觉得人力车又
经济又方便,拉车的又轻快省劲,于是马车渐渐被淘汰,由自用人力车
取而代之啦。自用人力车可到制造厂订制,车身不用说,是漆得锃光
瓦亮,车轮前辂,凿花电镀,车把后辖,起线包铜,轮圈钢轴擦得是一尘
不染,四只车灯两长两短,要黄包车上所有饰件,一律黄铜煅烧,喜欢
银白色的一律电镀,更显得干净洁亮。车簸箕安上双脚铃,车夫在前
车把上一边是手铃,一边是四音喇叭。不用说自用车如此讲究,就是
年轻小伙子拉散车也有这样刀尺的。有的人把自用车夫夏天穿上浅
竹布镶黑白大云头号坎,冬天蓝布大红云头号衣,大褂棉袄一甩,让人
一望而去是自用车,免得巡警找麻烦时摸不清底细。
夏天车上挂一块素色布挡,既避风沙,又免日晒,到了冬天,在零度
以下气温,西北风刮过真像小刀子割耳削脸地疼,于是人力车都套上深
蓝或深黑什衲的棉篷子起来。拉车的甩下大棉袄,往脚下一围,车帘子
扣得严丝合缝,寒意全蠲。当年地质学者李仲揆(四光),在北平因为工
作过分劳瘁一度失眠,冬季他就天天出门听夜戏,敖戏之后,坐有棉篷
子的人力车回家。车一晃荡,就引起他的睡意,一觉酣然,他的失眠症
居然不药而愈。还有一位摩登诗人林庚白,他在北平住在浸水河,他每
天应酬甚多,微醺之后,诗兴起来,每得佳句,酒醒即忘。他的包月车,
连篷上装有一只电石灯,随时记录,他说他诗词佳句,十之八九,是得自
车上。北平舍下大门正对一座磨砖大影壁墙,因对面是马圈尽量推展,
所以门前显得特别宽敞,加上两旁重阴匝地,修柯戛云,半人高石灰树
圈子,是藏茶具的好地方,左右上马石,是杀一盘车马炮的棋架子。舍
下人口众多,人来客往,成了无形的车口儿啦。
先君的乳母,我们尊称嬷嬷奶,为人慈慧温良,胸怀夷坦,西城贫
苦大众都叫她杨善人,凡是拉车的想拴个车(买辆新车叫拴个车)、沿
街叫卖的小贩亏了本,如果真有急用,找到她,只要她老人家手头松
翻,无不尽力帮忙。卖黄鱼、糖三角儿是她的干儿子,卖炸糕、打小鼓
儿的也叫她干妈,门口那帮拉散车的十之八九都管她叫好听的。杨老
太太出大门,一迈门坎,大家都抢过来拉,杨老太太坐车从不讲价,有
时身上不方便并不给钱,可是这般苦哈哈儿们,谁有了难处,杨老太太
总是倾囊相助,给他们解决问题。这帮拉车的非常讲义气,杨嬷奶在
北平病故,真有不少不认识的人来给她穿孝袍子送葬,足证他们的干
妈干姥姥没白疼他们。
我学校毕业,第一次担任公职,是在经界局补了一个主事,位卑职
小,如果天天坐着自用马车上下班,觉得挺别扭,于是也弄了一辆人力
车代步,拉车的人选可麻烦啦。门口拉散车的有“麻陈”、“小回子”、
“贾老虎”、“小辫儿”,几个人都是拉车里一等一的好手,快而且稳,一
些拉车的在街上拉着座儿看见是他们哥几个,就没有人敢跟他们赛车
的。
有一天我在珠市日开明戏院,听完梅兰芳的《贞娥刺虎》散戏出
来,一上车就有两辆各有四只电石灯自用车,把我的车夹在中间较起
劲儿来给。我拉车的叫小回子,牛高马大,两腿快似追风,长劲十足,
能够从西直门一口气跑到颐和园,而且从不服输。现在既然有人跟他
较劲,他自然求之不得,一过珠市口,我才看清车上两位靓装粲丽的美
妇,敢情是花国四大金刚的“忆君”、“惜君”姊妹,我想她们一定走胭脂
胡同回莳花馆。谁知这两辆车一直跟着进和平门,走到长安街天街人
静,小回子一使劲,可就把他们抛到后头了,一直到西单北大街舍饭
寺,他们去花园饭店才分手。过没几天大律师王劲闻在莳花馆请客,
忆君告诉我说,她们两个车夫耿大耿二是南城双杰,我的车夫小回子
是西城一霸,不打不相识,他们反而拜把子成了把兄弟了。想不到赛
车还赛出这么多事故由儿出来呢!
民国十六年我到上海,住在舍亲李府,他们拨了一部汽车给我代
步,我要求他家人力车借给我用。谁知上海自用车跟街车最大不同,
一个是方车厢,一个是圆车厢,自用车跑起来颤车把,在北方只有花姑
娘的自用车是这样抖法.,想不到上海自用车跑起来全是这副德行,我
实在吃不消,又改坐汽车。我有事去苏北,经过镇江,一出火车站就坐
上人力车,谁知经过京畿岭下一个很长的陡坡,拉车的偷懒,他一扬车
把,两脚腾空,顺流而下。幸亏车后有一个铁镞子把车挡住,否剐非闹
个人仰车翻不可。所以后来在镇江凡是经过京畿岭,我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