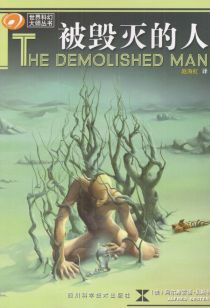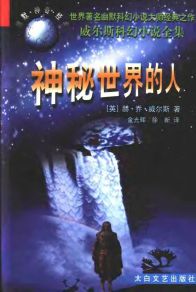承担天职的人们-第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对方摆脱了尴尬,迅速拿出老板的姿态,说:“你还没住下吧?我来安排。”
他把孙毅飞领到楼梯下的一间客房,说:“你住这里吧!其他的房间都是共用,太乱!这里虽然小点,但是一个人住,我叫人打扫一下,给你换套被辱。”
他说的房间,实际上只是楼梯下被利用的一个空间,除了一张床外,几乎再也没有多余地方,床上也只铺了张凉席,但一个人住,已经比这几天住的环境好得多,孙毅飞感到非常满意,他再三地道谢。
“你就别客气了!谁让我们曾经是战友呢?”对方笑着说。
“战友”,一个极为平常的称呼,在远离自己部队的地方,孤身一人时,再一次听到这个热乎乎的呼喊,孙毅飞越来越感受到,这种曾经像亲兄弟般一起战斗过的经历,在大家重新聚合的时候,是那样让人心潮激荡,思绪万千。
这里的蚊子,可算是可恶之极,尤其是人蹲在厕所的时候,这些凶恶杀手,在人们最难以防范的时间,向人最敏感,最为隐秘的区域疯狂进攻。黑色的,带着白色花纹的蚊子,隔着衣服都能吸食到人的鲜血,连蚊香都难驱逐它们。
夜晚,战友特意在孙毅飞住的小客房里,摆上四柱蚊香。虽说夜里蚊子没有侵扰孙毅飞,可大量熏蚊子的烟,却没能让孙毅飞好好休息。
语言是这里外调的最大障碍,乡村多数女性,几乎都不会说普通话,每当问到她们时,都是莞尔一笑,接着摇摇头,说出一句大概是听不懂的方言后离去。在几乎没有公路的沿海农村,孙毅飞用双脚,在空旷田野里赶路,上午也许是顶着烈日,下午可能又要行进在蒙蒙细雨中,他一步一步走过南方水乡一块块石板铺出的小路。
十几天的奔波,孙毅飞终于来到这次外调的最后一站,一个离福建省不远,坐落在海边的公社。海边上,孙毅飞和公社武装干事一起吃午饭,饭是公社武装部安排的,不要孙毅飞掏腰包。武装干事从公社办公室,拿来两把小椅子,一张小桌子,支在海边沙滩上,他又慷慨地从附近渔船上买来一些海鲜,连洗都没洗,放在地上的盆里,直接用开水烫一下食用。
孙毅飞在武装干事殷勤劝说下,试着吃了一个贝类海鲜,立刻,舌头上下,牙缝里,牙床上,布满泥沙,每嚼一下,“咯吱、咯吱”沙子硌牙的难受感觉,都使孙毅飞头皮发麻,浑身起鸡皮疙瘩,加上半生不熟和浓浓鱼腥味,使吃到嘴里的东西难以下咽。可碍于人家的好意,孙毅飞又无法吐出来,只好强忍咽下去后,赶紧喝几口水,借机冲洗满嘴沙子。孙毅飞用怀疑和难受的眼光,看着武装干事津津有味吃着。
武装干事并不在乎孙毅飞的不习惯,一个接一个吃得很香,他身边的地上,已经扔了一堆贝壳。他边吃边说:“这是好东西,只能这样吃,不然不新鲜了。”
孙毅飞索性不吃了,问:“我看你们这里好像都在单干,大队一级的政府机构,怎么都没有人办公?”
武装干事不停嘴的吃着,说:“整个地区都是这样,据说,我们这里光万元户有六十多户,还有几个上百万的,都在想办法挣钱,谁还管公家的事?”
万元户!并不难理解的数字表达词汇,一个全新的概念,虽然在这个星球上并不稀奇,可在中国内地很多地方的农村,还在以每日百分之几元来计算家庭收入的时候,却出现在中国远离中心城市的农村,足以使孙毅飞惊讶的同时,打开想象的空间。生活本来的丰富多彩,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对于每月只有十几元津贴的孙毅飞,不要说拥有百万,万元已经是个天文数字和不可想象的概念,即使对一个年收入一千多元的团级干部,万元也要挣将近十年,太简单的算数题了!他惊讶地问:“这么大的收入差别?你们没想法?”
“有想法有什么用?他能有你为什么不能有?他能挣到钱你为什么不能?大家都在比嘛!”武装干事,似乎很认可向往这种追求。
“那你们这里不是已经变了?”孙毅飞继续问。
武装干事说:“变?穷则思变嘛!我们这里平均每人不到半亩地,不想办法连饭都吃不饱,谁愿意过穷日子?”
孙毅飞好奇地问:“那他们靠什么挣这么多钱?”
武装干事边津津有味地吃着海鲜,边说:“做买卖呗!无商不富嘛!”
阵阵海风拂面,夹杂着淡淡的腥味,武装干事的引经据典,让孙毅飞大大开了眼界。
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孙毅飞忽然觉得,过去的思维模式,真像是井底之蛙,思维宽度,瞬间被拓展开来,忽然对过去一些认识,有了重新思考。
环境,磨练了孙毅飞的意志;社会,成为他最好的老师;经历,像生长激素一样催生他的成熟;天性中的倔强,使他不愿意屈服;命运中的八字和后天的努力,最终促成孙毅飞肩负起干部的责任。 。。
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
连部里,刚刚洗澡回来得邢志武,坐在床边,嘴上叼着烟,满脸仇恨地看着脸盆里的脏衣服。李中海也洗澡回来了,看着邢志武的样子,笑着说:“怎么啦?连长,又发憷洗衣服啦?那还不好办,给嫂子寄回去,洗干净了,再寄回来嘛!”
“哎!”邢志武叹了口气,说:“你说,咱们这哪像大老爷们?再学会生孩子,还要老婆干什么?”
“哈哈…”李中海笑起来,说:“那好啊!等嫂子来的时候,我告诉她,说咱们连长想学生孩子,看看嫂子啥意见?”
邢志武赶紧说:“你可别和她胡说八道,惹她生气!她也够不容易的!带着孩子,还要伺候老人,地里的活还要干,做个军人的老婆,够委屈她啦!”
李中海说:“是啊!别人都以为嫁给军官有多荣耀?其中的酸甜苦辣,也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也只能瘦驴拉硬屎硬撑着吧!”
李中海走过去,把邢志武的脏衣服到进自己的脸盆,说:“得了!你也别动手了,该忙什么忙什么去,我来洗吧!反正洗一件也是洗,洗两件还是个洗,我来过把瘾!别嫌我洗得不干净就行。”
邢志武说:“那怎么行?咱俩一块洗,凑个热闹,洗起来也不烦。”说完,从李忠海脸盆里,拿回自己的脏衣服。
李中海也不阻止,说:“好啊!正好我有事要和你商量呢,咱们边洗边说。”
晚上,李中海告诉孙毅飞,连长同意他带先遣队了,孙毅飞看着李中海,半信半疑的问:“连长这么快就改主意了?你怎么说服他的?”
李中海笑笑,说:“你还不了解连长,他是个自尊心很强,把面子看得很重的人,说话向来说一不二,在连里的威信和地位,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在干部会上,强调他的身体不好,否定他的意见,他当然接受不了。现在,在已经形成决议的事实面前,他主动让出先遣队的位置,这样既不会在大家面前失面子,又显得充分考虑尊重大家的意见,他还能有啥不同意的?何况,先遣队能有多大问题?顶多是困难多点,大部队到达前准备不好,以后还可以补救,去的又都是挑选出来的骨干,还能有逃兵不成?”
孙毅飞两眼凝神地看着李中海,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先遣队已经做好转场出发的准备,半个月后,出发的命令下达了。为了给先遣队饯行,临行前一天的晚饭,连队特地加了两个菜,难得一见的排骨炖土豆和烧茄子,加上多年一贯制的大白菜和萝卜,凑起四菜一汤。
别看菜里的排骨不多,却把邢志武肚里的酒虫,勾了出来。他一边看着菜盆里的排骨咂巴嘴,一边大大咧咧地朝孙毅飞喊道:“指导员!是不是把你库存的好东西,拿出来共产一下?”
孙毅飞笑着对邢志武说:“我说连长,先遣队的油水你还不放过?我们去的可是四无地带,攒这点儿好东西不容易!”
邢志武眼睛盯着菜盆,用手在盆里挑了一块排骨放进嘴里,大块的排骨,把枯瘦脸颊的一侧支撑起来,立刻,舌头也显得不利索,他话音含糊不清地说:“舍不得就舍不得吧,干嘛说得那么惨?这点东西你还用攒?对你来说还不是小菜一碟!”
听邢志武是话里有话,孙毅飞不假思索地说:“连长,这么说就远了吧?你我都在连队里,都是仨饱一倒的普通军人,享受的都是一样的供给制,你这可不是共产啊,倒有点像明夺暗抢啦!”
邢志武自知理亏,但他很快又给自己找了个理由,说:“你提升指导员都这么长时间了,早说要请客,到现在还没请,临走前还不补上?再说,我把先遣队让给你,你也应该谢谢我啊!”
孙毅飞也觉得自己的话,说得有些过,就坡下驴地说:“你要是这么说,还差不多,这是应该的!”
邢志武为自己找到理由感到得意,又加上几句想找回面子的话,说:“你来一连还不到两年,要不是你运气好,说不定指导员的位置上,就是我们老一连的人了,所以你更应该请客。”
邢志武说的是李中海。
那还是李中海第一个孩子降生的时候。探亲回家的李中海,面对自己第一个孩子的出生,满心欢喜,他抱着女儿,不停的在屋子里转着哄着,不时用手指摸摸孩子尚未睁眼的小脸,用嘴亲亲孩子还满是折皱的小脑门。
爱人看着他喜欢的样子,伤感地说:“你还能看几天?过几天你一走,又要丢下我一个人照顾孩子。”
李中海逗着女儿,头也不抬地说:“不是还有妈帮你吗?”
李中海不说还好,话刚出口,爱人便委屈地流起眼泪。李中海听见妻子的抽泣声,停下来回转动的脚步,疑惑不解地问:“你这是怎么啦?刚才还好好的,怎么哭上了?”
他爱人说:“妈早说了,要是男孩她给带,要是女孩让咱们自己带。”
李中海听到妻子这样的回答,轻松地说:“我当什么事,妈真是这样说的?哪能这么封建?我找妈去!”
妈的话,真的伤害了李中海的自尊心:“女娃命贱!好带,用不着我做什么。你是咱村里出的唯一军官,没个男娃,村里人说闲话。你媳妇要是有本事,就给你再生个男娃,别让村里人说咱绝户。”
绝户!农村里骂人没有比这更难听的。面对农村的封建意识,李中海还能说什么?他暗暗下决心,一定要生个男孩。部队有严格的计划生育规定,李中海回到部队不久,便悄悄把爱人接到部队,在驻地附近找了个民房住下来。
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爱人怀孕八个月了,经过各种民间土方验证,都说是男孩,李中海觉得要扬眉吐气了,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在笑。没有不透风的墙,团干部部门向李中海发出通牒,要么要孩子,要么纪律处分,降职留用。
作为基层干部的李中海,别无选择。降职意味自己的军旅生涯,又要回到原来的起点,甚至是终点,他只好违心带着爱人去医院做手术。
爱人肚子里的孩子,将用催产方式做掉。药物注射后的这段时间,李中海不敢面对爱人的眼睛,爱人痛不欲生中说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