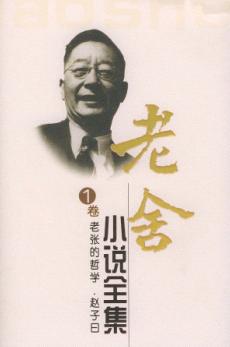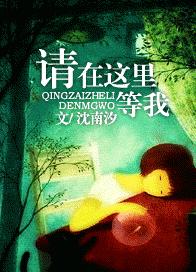请在车上等我-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八节
夏芙蓉住的地方是合租的小区住宅,且是七层的阁楼,估计里面的温度跟白天车里的相比舒适不了多少。他把车子停在楼梯口,她从一边下车。
夏芙蓉问,你还上来坐坐吗?
他知道租房子的条件之艰苦。往往是三四个人合住,一个人一个房间。所谓的家具最多只有一张窄窄的桌子和一把瘸腿椅子,除此之外就是睡床。加上单身生活往往不讲究,比较凌乱,插脚的地方都难找。不知道她的生活习惯怎么样,反正当年他就是这样的。
他说,不去了,我得回家,明天一早要去外地参加一个汽车新闻发布会,必须早点休息。
她没有再邀请,伸出了手,等着他来握。他的手在方向盘上,以为她还有什么事,见她笑着,眼中满是恳请的神色。他伸出了手。两个人握住了手。她的手软软的,有点湿润。多好的一双手啊!她拉着他的手,一边往后退,慢慢地把他的胳膊拽直了。一双手就这样依依不舍的样子分开了。她像个羞涩的少女,颔首紧走几步,扭着身子上楼去了。
他早该从她的眼中能够看出点什么来。
就餐的时候,王连城趁着喝了几杯的酒兴告诉她,如果她感兴趣可以到汽车专刊来试试身手,这边缺人。虽然报社常有临近毕业的大学生来实习,但大都留不下。如今的大学生不够务实,不想从最基本的事情做起。要知道,当年自己就是任人驱使先做小杂役的。他想,夏芙蓉将来或许能和自己共事。夏芙蓉的学历并不高,中专生,从陕西千里迢迢过来打工的,只是对他说过自己比较喜欢读点书,爱好一丁点文学而已。
“我才不管什么狗屁学历,我这边就是缺既懂汽车又懂文学的人才。”王连城醉意朦胧地说,“二十世纪什么最贵?人才!像我这样汽车专业科班出身又投身新闻采编事业的人太少了,小城市尤其如此,好在你对这两方面都有些感觉。汽车专刊的琐事比较多,秦筠主要精力在业务,忙不过来,你来之后可以帮我做一些编务和活动策划方面的工作。”
他说话的口气很像一个具有实权的领导。
他目前也是一个人住,不过与夏芙蓉不同的是,自己还有一套房子,刚刚按揭买的。其实他并不想这么早就买房子,单身在外面租房就挺好。以前报社给员工提供集体宿舍,水电暖等费用不用个人交,只是每个月象征性地收取五十块钱算是房租。问题是在半年前刚谈了一个对象,是柳文龙给介绍的,在一所重点高中当化学老师,两个人谈来谈去,感觉还行,就订了婚。说起来也许难以置信,自己大学毕业四五年了,另一半的问题早就应该解决,可是他并没有在爱情泛滥的大学期间谈情说爱,连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女朋友姓林,小林的家人提出,他们必须先拥有自己的房子才可以登记结婚,而且别指望女方出一分钱。王连城老家并不在Z市,他是家里唯一的男丁,上面有两个姐姐,父母巴望着他早点结婚生子,好在六十岁之前能抱上孙子。作为农民出身的他,房子问题是王连城有生以来遇到的第一头疼的大事,他不得不贷款。但是哪怕贷一分钱,父母都觉得不应该,好像亏欠了全天下人的。两位老人诚惶诚恐,愁得晚上睡不着觉,说:“儿啊,好好干!咱还欠国家的钱呢!”王连城却觉得,自己谁也不欠,全天下人都欠自己的。房子是新的,但没有装修,又要养车,还要交房贷,报社那点微薄的工资显然是杯水车薪,不足为外人道,让他捉襟见肘。
都忘了吧!天天想这些头疼的事情,人还不得死?
他驾驶着车子,半开着车窗,夜风吹进来,很舒适。要不是路上有不少车子来来往往,他都快要沉醉了。他必须开着车窗,好让头脑清醒一些,夏芙蓉和酒一样都会有麻醉作用。
第九节
他往楼上走,楼下正在装修中的住户的防盗门窥视窗里透出白色的光。他总觉得这些装修的人家里面住的都是居心不良之人,不定什么时候就要做一些坏事出来。好在他们已经停下了烦人的工作。他一路躲着脚,震动的足音让楼梯内的声控灯渐次地亮了,从一楼升到五楼。这段路是那么漫长,可是又很实在,只有在这种寂寞的时候,他才觉得自己是自己。
他不喜欢楼梯,因为楼梯让他感到恐惧。楼梯内绝少碰到人。而且这栋楼还没有楼层标识,他一边往上爬,还要一边数楼梯。他怕一直往上走,走啊走,会走过了头,走不到头,如同上了天梯,走进了异度空间。下楼梯亦如是,他怕下了地狱。
自己怎么会有如此荒诞的感觉?
目前他尚是孤孤单单一个人住。实际上孤独并不可耻,孤单才是可耻的。小林的家人知道他买了房子,虽然鼓励他们尽快结婚,但并不主张女儿在结婚前过来同居。这是什么时代了,还这么保守。而且这是年轻人自己决定的事情,不知道小林的父母为什么把宝贝闺女看得那么紧,小林怎么会那么死脑筋,难道真要为人师表吗?
真是古板的理科老师,没有文科生的浪漫。
他到浴室里冲了一个凉水澡,擦干净后躺在客厅的一把木质躺椅上,用遥控器打开电视——他几乎每晚都不关电源。
天非常热,乖张的夜色热涨后变成了令人窒息的浑水。
风扇在屁颠屁颠地转动着,现在他还没有闲钱装空调。家里十分简单,没什么像样的家具,更无制造浪漫情调的小摆设,就跟租房子的时候差不多。客厅里最显眼的就是电视和沙发,还有这把动起来“咯吱咯吱”响的躺椅,摇头晃脑的又有些垂头丧气的电风扇。而毛料的沙发是吸收储存热量的载体,不能再坐。三个卧室,只有一个卧室里摆着一张象征单身汉身份的单人床。厨房里除水管和燃气管道之外别无长物,灶具周围没有家一样感觉的锅碗瓢盆。他一般不在家里吃饭,除非是从外面买点回来,也常常是几个狐朋狗友聚在一起找没人管的清静,喝点革命的小酒。
他正在努力攒钱,装修和家具购置需要一笔不菲的开销。父母已经无能为力了,上了年纪的他们很难再提供大额的经济援助。他曾向小林提起这事儿,意思很明显,希望她家也帮衬帮衬,但是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应。估计是她的父母不同意,但她好像又不好意思对他说父母不同意。父母对她管得很严,她还要时时维护父母的权威,甘于被看管。小林肯定也觉得自己父母有些不近人情,所以淋浴器是她帮他买的。她每月发了工资都要上交,要不是每月悄悄地耗下一点奖金做私房钱,王连城只能洗凉水澡了。真是难以理解,小林的父母都是退休老教师,应该有那个境界啊!每个月两三千块钱的退休金,难道还想带进棺材,存到阴间的银行里?
电视正在上演古装片,他提不起一点兴致。伸手从沙发上随意捡起一本杂志,是财经类的刊物,还是崭新的,没有开封皮。三两把没好气地撕掉塑封,捧到眼前看了不多久,就感到困意袭来,昏昏欲睡。
在浑浑噩噩中他听到楼下有汽车鸣笛,并停了下来,接着是单元楼的防盗门“咣”地一声闭上了。他想,几乎整个楼洞走廊的灯都该亮起来了吧。真是该死。他敢肯定又是那两个女人。一老一少,老的四十多岁,少的二十多岁的样子。从进入楼梯开始,高跟鞋击打水泥地面的声音就响彻楼道上下。婊子。他喃喃地吐出两个字作为诅咒。他想,大概午夜了吧,打开手机一看,果然已经凌晨一点多了,没想到自己的一个迷糊就耗去了这么长时间。这两个女人总是晚出晚归,不跟常人一个作息时间。他在楼下乘凉的时候听闲来无事的老头儿老太太嚼舌头,说她们是“小姐”,在附近最豪华的夜总会坐台。老女人操着南方口音,小的讲东北话,打扮得花枝招展且妩媚妖艳。当然,半老徐娘的那位就算不上了,倒像个驴屎蛋子外面光的老鸨。王连城白天好几次与她们在楼梯上擦肩而过,两具肥壮的肉体上散发出呛人鼻息的气味,他没法分辨,但可以想象是哪几种混合物的味道。其中有股腐烂的霉味儿,肉的腐烂。正因为此,他从来没有正眼看过她们的脸,只知道她们化的妆很浓,眼影非绿即红,口唇如血盆。不过,她们开的车不错,是进口的日本车高档车。或许是因为车主的职业受到了怀疑,竟遭到了人们的不公正待遇,不给她们好脸色看,还要在她们开的车背后“呸呸噗噗”的唾弃痰水。
她们有自知之明,仿佛也在尽量地蹑手蹑脚地走路,他可以想象其动作会像猫狗一样,但仍然发出刺耳的鞋跟敲击和摩擦台阶的动静。声音从自己门前走过,又转折升上去,接着是悉悉索索的钥匙插门锁孔的声音,“咣当”一声掼门的巨响。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她们进入室内脱鞋之前的失蹄乱踏,仿佛X光线穿过房顶,从天花板上透射下来,像冰雹一样没头没脑垂直砸下来。他为自己的遭遇感到不幸,同时对出租房屋的主人发出了最恶毒的诅咒。据说,本楼其他住户以居住安全为由,已经向小区物业管理公司提出了抗议,强烈要求加强对外来人口租赁房屋的管理,如有必要还将向派出所反映。
他突然想起了夏芙蓉,她也租了别人的房子。尽管他没把她往坏处想,但很想知道她现在在做什么,是不是睡了。他拿起手机,写了一条短信:你睡了吗?但一直犹豫着,直到手机屏幕变黑恢复到省电模式,最终没有发出。
第十节
天亮的时候他是被一个噩梦惊醒的。确切地说,是一个让人困惑的梦。他常常做类似蒙太奇和荒诞风格的梦。比如置身于田野和村庄之间,永远找不到回家的路途,比如在梦里能飞檐走壁,到了被人追杀的关键时刻却一切特异功能皆告失效,比如你的亲人总是与自己形同陌路,甚至在阴阳两界。
这个梦也差不多令他感到绝望。
那是在由自己带队的自驾出游的路上,他和夏芙蓉(为什么不是秦筠呢)共乘一辆车,就是自己的富康,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近十辆由经销商负责集结起来的车主的汽车,他们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走着走着,渐渐地驶进了一片浓雾中,能见度极低,几乎看不到路边的护栏,甚至连地面也有些潮湿模糊了,高速公路的管理规定可不允许在极度恶劣的天气里行车,早就应该封闭了吧,他想,应该通知大家减速慢行或者安全停车,作为带队人,他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也有这个必要,他想去拿对讲机,然而一伸手却抓了一个空,刚才正常使用的对讲机不翼而飞,再往旁边一看,坐在副驾驶座上谈笑风生的夏芙蓉也消失了,回头看后面,没有任何车辆跟随行驶的踪迹,一点声音也没有,他成了孤家寡人,他开车走上了一条狭窄的出口,这是一条斜路,又像乡村的一条岔道,路上湿漉漉的,像潮水洗过的沙滩,这时候周围的浓雾稀薄了许多,仿佛走了好久,转了一个弯,竟然驶下了一个缓坡,眼前是一片极目难尽的嫩绿的茶树丛,远处有雾霭隐现,车子终于抛锚了,发动了几次都是徒劳,一点动静也没有,真要命,此时他还在胡思乱想,竟然想起了为了挂晒玉米从梧桐树上摔下来致死的身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