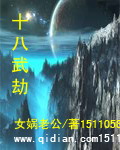残影断魂劫-第53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样为我付出。至于你对我的好,我很是感激,可惜无以为报。希望你明白,我不喜欢任何人来逼迫我,或许,我算不得脾气如何强硬,但我也绝不会向强权妥协。不论他用什么来威胁我,哪怕是生命。”
扎萨克图昂然站起,道:“安琳,我不要你的回报,只要是我想要的东西,就一定要拿到手。那姓孟的,不过是个没权没势的穷小子,就算他能熬到出任华山掌门之日,又能多加个几钱几两?他养不起你,他也配不上你,明白么?而我——”双手向身旁一摊,满有种将整个天下囊括怀中的豪情,道:“本座是祭影神教的教尊,任何人都得屈服在我的统治之下,包括华山,包括江湖上的大小门派,也包括当今龙椅上的皇帝老儿!放眼整座江湖,还有哪一处不是我教的土地,是我未曾派人驻守?安琳,嫁给我,做我的教主夫人,你会从此获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位。你是个一生下来,就应该享福的女孩,从我在那山洞中第一眼看到你,如同花瓣上一滴新生露水般的你,那样柔弱,却又那样坚强,从那一刻起,我就决定了要保护你一生一世,给你一切的幸福。你不仅是我的救命恩人,更是我这辈子认定的女孩。安琳,我只爱你一个,再也没有其他人可以插足。”
楚安琳又是感动,又是无奈,低声道:“这样的你,对我而言很陌生。看着你追逐权欲的狂热,甚至令我觉得可怕。你要的是天下,不是我,你只希望我能做你身边的一个华丽点缀,做你借以锦上添花的工具!如果说,我曾经对你有过感情,那么我爱的,也是在山洞中初次相逢的你,那个言谈间风流倜傥,同我讲论天南地北的人。”扎萨克图沉声道:“可惜他已经死了,回不来了,被他的伯父亲手所杀。”楚安琳道:“是的,他回不来,我又何尝回得去?”每个人都在不断向前行进,过去再如何美好,却又怎能在追忆中复苏?
扎萨克图顿了一顿,忽然像是突然醒悟一般,道:“对了,安琳,我知道了,你一定是不愿见我杀人,是不是?那么我答应你,只要能够彻底安邦定国,此后我祭影教,定然不伤百姓一条性命,不损中原一根草木!这不也同样是你的愿望么?为了你,我一定会改,一切都改,行么?”
楚安琳见他痴心一片,虽觉不忍,却也不得不狠下心肠,道:“你为何就偏要这么傻,在我身上浪费感情?难道你不明白,无论你再如何努力,我对你,最多都只能当作最好的朋友,却永远不会是爱意。因为我爱着孟郎,纵然与他在华山默默无闻,我乐意;随他漂泊江湖,我乐意;随他打鱼砍柴,我乐意;甚至随他在街头讨饭,遭受天寒地冻,我也乐意。当你全心爱着一个人的时候,你虽想跟在他的身边,却绝不会束缚他,而是盼他得到幸福,甚至牺牲自己,来成全他!如果你真心爱我,就请你让我去寻找值得停泊的港湾,请你祝福我。”
第三十七章(39)
扎萨克图气急败坏,极力平定心神,才未向楚安琳大吼大叫,道:“那么,请你告诉我,究竟要我怎样做,才能使你快乐?”楚安琳声音低微,却又极是坚定的道:“只要你放我走,让我回到孟郎身边,对我,就是最大的成全。同时这一生,我都不会忘记你这个朋友。”
扎萨克图恼火已极,如困兽般在室内连兜几个圈子,拳头几次提起,而又落下。楚安琳几乎以为他要扑过来掐死自己,但她性子里自有一份倔强,仍然高昂着头,视线不肯回缩。终于扎萨克图长叹一声,道:“也罢!在你心甘情愿之前,我不会勉强你,也不来碰你,你就在这房中好生休息。但我也绝不会让你回去见孟安英,没有哪个男人,能做到如此大度,这已是我所能容忍的底线,你最好别再妄图触犯我。”说完狠狠一甩袍袖,急奔出屋。楚安琳望着他垂头丧气的背影,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只斗败的公鸡。
两人本应就此相安无事,但历来贪心总有不足。扎萨克图失势后,心胸尤其狭小,只觉全天下人对他均有亏欠,这笔债须得一一偿还。因此凡是他想要的,无论是人是物,都将不惜一切手段强取豪夺。楚安琳虽然在他身边,态度却始终不冷不热,也令他尤其恼火。听多了下属谈论“若想得到一个女人,便要先拿下她的身体,远比骗得她的心重要。”思潮暗涌。最终借着一次酒后乱性,闯进楚安琳房中,强行占有了她。事后倒真有几分后悔,谁料楚安琳不哭不闹,也没来向他责问一句,仍依每日照常起居。扎萨克图做贼心虚,不敢主动探听,只好在暗地里加派人手盯梢,以免她自寻短见。
又过了一段时日,楚安琳情绪终于转归镇定,整日尽在书房中翻阅典藏,将扎萨克图千辛万苦收集的秘笈逐一看遍。偶有闲暇,则与他谈论武学大成之道,集数家之所长,弥方寸之所短。扎萨克图虽不解其意,却分明觉出她态度好转不少,对自己的抵触也不再如往常般明显。而楚安琳学识渊博,见解独到,在其练功一途颇有助益,扎萨克图已觉经她提点,诸般困惑迎刃而解,喜不自胜。同时暗中惋惜,早知这法子如此有效,为何不提早施行。每当他论及武道,楚安琳也随着他性子,侃侃而谈,堪称良师益友。但他若想更进一步,谈些初为人父之喜,或是不知咱们将来的宝宝是男是女,该给他做些小衣服等等,楚安琳则立即板起脸,冷如冰霜。扎萨克图碰过几次钉子,渐渐学得乖了。暗想两人能有如今这份友情,已属不易。放眼来日方长,自己一片深情,还愁感动不了她?
与此同时,孟安英亦是锲而不舍,以各种途径打探楚安琳下落。然而落到魔教手中的人,竟也如魔教本身一般受人忌讳。苦寻多日,旁人连这话题也不愿多谈。正当此时,原庄主出现在他面前。提及两人初遇,那还是不打不相识。正值原庄主在各地连犯大案,追踪的捕快也是个个束手无策。地方官员摊上这桩案子,不知受过上司几度责骂。不得已备下重礼,前来华山求援。一番商谈后,掌门人派出几位得力弟子出山相助。一行人闯入一座荒宅,孟安英奋勇当先,跨过满地七零八落的尸体,忍着刺鼻的血腥味,在各间房中穿进穿出。忽然一道深绿色暗影急冲而出,孟安英应对极快,立即向着他去路追出,两人仅落得个前后脚相差。那凶手正是原庄主,展开家传轻功,状若足不点地的飞奔。而不论他如何提速,横转斜拐,孟安英总能紧跟在他身后,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始终甩之不脱。原庄主本当他是个寻常练家子,如此一来,倒是不敢再小瞧了对手。又诱他奔出几步,忽然回身出掌。孟安英全不慌张,依着平素习练的功夫,沉稳应对。苦战良久,竟是双方势均力敌,谁也斗不过谁。原庄主哈哈一笑,身子倒纵,道:“这位兄弟,身手不错啊。不知是出自哪位高人门下?可惜我现有要事,恐怕没时间多陪你玩了。”
常言道得好‘伸手不打笑脸人’。孟安英见他这副神情,手中紧握的长剑逐渐垂了下去,却仍未敢全然收入剑鞘,道:“看兄台模样,也是个知书达理之人,却为何要做下这等伤天害理之事?那一家子,同你又有什么怨仇?”
原庄主冷冷的道:“谁妄想阻止我,都只有死。想我对阿茵掏心挖肺,最终又换来了什么?那些身居高位者,根本就什么都不明白,只以眼前所见为论断,都来难为我。我偏偏不服!”此时其余弟子也随后赶上,刚好听见他这一句话。楚安琳试探着道:“听你所言,似乎有何苦衷?或许我们可以帮你。”原庄主双眼一瞪,道:“胡说!人死不能复生,没有任何人帮得了我!”楚安琳道:“你也知道是人死不能复生,徒造杀孽何益?不仅无法挽回你所珍视的一切,更要使旁人一齐陷入这苦痛深渊。倘使人人所受置气,均要以转嫁旁人来讨回,怪不得武林中纷争不断,永远无法获得太平。你们眼里似乎不存在的所谓公理、正义,需要所有人同来维护。自身已是触犯者,更有什么资格怨责世道不公?”
原庄主眉头拧起,仔细打量了楚安琳半晌,道:“小姑娘,我不知你果然是冰雪聪明,还是歪打正着,竟能猜出,我是失去了极为重要的东西,才来向世人报复?”楚安琳淡淡道:“那不必猜,或许该说是一种体会。从你眼中涌动的不平,却又隐含着一种刻骨的遗憾,那不是残忍嗜血的眼神,而更像一头受了伤,默默流血,无人怜惜的豹子。我想,你并非冷血无情,而是觉得天下亏欠了你,是一笔难以偿还的债。因此索性放弃了合理的索赔,转为颠覆正道,来做你心头所爱的祭奠。我说的对么?”孟安英与原庄主尚有一段长途追踪,此时与他当面交谈,也不过是觉此人气质超众,不像个天生的恶魔。但对于他杀戮根源,则全然摸不着头脑。不想楚安琳几句分析,竟而说得头头是道,宛如亲眼所见,看来正触及了原庄主心头痛处。孟安英心神一凛,历来受伤的野兽绝死反扑,才是最凶恶的杀招。见他眼神极是怪异,盯着楚安琳的目光恨不得将她生吞下去。暗中握紧剑柄,脚步悄悄挪动,挡在楚安琳身前,以防原庄主几时心志失常,突起进攻。
不料过得片刻,原庄主眼神忽转柔和,眸中卸去了一层深深戒备。叹道:“除了她,从没有哪一个人,能够真正看穿我的内心。如果你当真愿听,我就破例给你说说。倒不妨请你品评品评,我的报复,究竟算不算无事生非?”
华山朝阳台,一阵冷风嗖嗖卷过。说到此处,孟安英向原庄主投去一眼,道:“原兄弟,你那段陈年往事,是否介意我公诸于众?”原庄主苦笑着摇了摇头,道:“时隔二十多年,人生几易寒暑,曾经的一切,我早已看得淡了。真相总要人来面对,还能逃避到几时?你尽管直说便是。但愿能使江圣君有所领悟,不要走上我的老路。”江冽尘冷哼一声,道:“有劳挂怀,但即使过程相似,结果也是不同的。看在你的面上,本座就洗耳恭听。”
原庄主的故事很简单,据他当初所言,出身在一个多年前鼎盛一时,而后因奸人所败,逐渐走向没落,最终隐居方外,不问世事的神秘家族。原庄主年纪轻轻,就是个文武全才,对隐居的苦闷生活深感厌倦,有心要在江湖上崭露头角,出人头地。首次参加科举,却因行文格式不类传统八股,言辞又太显激进,未受考官青睐,最终连一位落第秀才也没能捞到。原庄主大感不平,暗道:“原来中原人就这等不识货,怪不得四城难以长存。”功名未能考取,他便转换途径,做得个劫富济贫的侠盗。而平常在市井之间,却是极不显眼,纵然对面相识,也教旁人认不出来,他便是**上颇有几分名气的人物。
这天,原庄主又打听到一家富豪府邸,据称府中老爷全靠贪赃枉法,才积得家财万贯,能在这座本不大富裕的小城中,筑起一座偌大宅院。四座山庄布置也是处处金碧辉煌,原庄主则另有种争先心思,与穷人推翻显贵相比,更多则是不愿见旁人比自家富裕。因此偷起富人财物,从来不曾手软。运起绝顶轻功,从高墙外一跃而入,竟连地面半根草也未惊起拂动。匆匆急掠,足不沾地的跃入房内。室中前一刻还是漆黑一片,等他脚跟落稳,竟突然间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