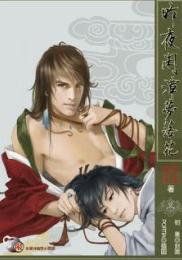��������-��4��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ϲ�����ŷ��̫�������磬������ȴ�����ʯͷ�ǡ�
�ҵ���������������������λ�ø��࣬��������أ��������ʿ�������ʳ���������������ǴӲ��Ϸ���������ʣ��ƺ�������������Ĵʻ㡣
�Ҵ�û���κ�����������յ����֣��Ҳ�����ô������֪�������ᵽʯͷ��������ô��ֻҪ��֪���������֣���û�а취�ٻ�����
Ҫ֪������Ҫ��סһ���������ҵ��ȣ��Ǻ����ѵġ�
���ǣ��һ��ǵ����ε�������
�������������һ��Ѫ����һ��ʼ����ֻ�������Ϊ�Dz�����һ�����ݡ�
�������ϣ��ұ������������������ѣ����⿴ȥ��ȴ���ֺܶ�������������������ʯͷ�ǡ�
ʯͷ�������ǵĹ����ͨ���Dz������߽��ġ�
���������⡣
��Ⱥ�ᄍ�����ഩ�ź��£�ͷ�Ϲ��ź�ɫ�鲼���ˡ�
��������ʲô�ˣ�����С��ѯ�����ߡ�
���Ǹ����ң���Щ���ǹ��ܲ���Ĺ��塣
��֣����ܾ۾��ڱ��������������ϣ���ô���Ȼ���������ء�
��Ⱥ�У��ҷ���һ��ʮ�ָߴ�Ĺ����ˣ����úڲ���ס����ֻ����һ˫�۾�������ü���ú�ɫ��ʯ������һ�����Ѷ��ϵĺ��ߣ��������е�����������ĵ������������ںڵ��۾�����ҵķ���ȴ����ת�������˲�䣬�ҷ��������ڻ����һ����ϻ�ӡ�
������ʲô������С���ʵ���
����æ�������������������ܳ���֮������ܡ���
���ƶ��Ƕ��ĵ��ͷ��
Ӯ���ڸ�ʲô�����ҷ�����Խ��Խ���Ծ����ƺ���������ʲô���¡�
���ܳ��ϼ���Ī������Ķ��������ɴ��ͷת�˹�ȥ�����ĸ߰�����ʮ�ֲ��ã����������ӣ������߹�ȥ��˭֪����û���������㱻һ���˽�ס��
��������ѩ�ij������ںڵ�ͷ���̳�һ���ٸ߸ߵ�����ͷ������һ�������İ�ɫʯͷ����ס��
��������·��ʮ����ӯ������ƮƮ�����¡�
������ǰ����Ǹ�Ů�ˣ�ȴ�������Ǵ���ͬ�����·������߰�������ͷ�������ҵ�����ʱ���������۾���û��գһ�¡�
����æ�������ס�ҡ�
��������Ӧ�貿��Ĺ��壬��ס�����ģ���m������ͬһƬ����֮�ϡ���
���m����
���ߵ��ͷ��
����˵�����m��һ���������ų��Ĺ��ˣ�����**�����������ò�Ҷ�ڵ�����˵�Ǐm������˵ĺ����������������һƬ�����ϵ�Ӧ��ֳ����������䣬һ�������ﶼ�����ԣ�����Ϊ�ɷ������һ��������ȫ��Ů�ԣ�����Ϊ���˹��������ͨ�飬ȴ���ų���ĺ�ֵ����
Ӧ���˵ĸ����dz�������̸���Ҳ���Դﵽ�˰��ꡣ
��Ŀ����Զȥ��Ӧ�賤�ϣ���Ů��Ӧ�ò����ϣ����ҵ�ȷ���²�������͡�
�ܶ���˵��Ӧ���˳�������Ϊ�����DZ�������������ĵط�����������˵��λ�������IJ���ɽ��ͨ������Ψһ��ڡ����ﵽ���������������ʳ����˱�ɳ������ϡ�
��ȷ��Ӧ���˲���˥�ϣ�����ֱ��������
����������ĽӦ�貿�䣬���ǵ�����Ϊʲô��ô��ѡ��ȥ�˰˻�֮����Ϊ��ʥ��������
Ȼ������ȴ�IJ���ΪȻ��
�����ߵ���Զ��ҲҪ���ض������ӻع��ϻģ���Ϊ�����������ҡ������ҡɽ�µ�С����Ũ�����ڵ��������������ʥѪͳפ�ص�ʥ�ء�
������������°ͣ���Щ������Ŀ��һ�еļ��ƣ����Ҿ���ʮ�ֵ�θ�ڣ����Ա��������뿪��ʯͷ�ǡ�
ֻҪ�ڰ�����ȥ�Ϳ����ˣ��������������ϵ������С���ʱ���һ�ֻ��Ϊ����һ�����ݡ��ҵ�ĸ���ٻ��˻ĵ�����ۼ������Ľ��£���ô����ֻ�dz�����ô��
��һ�Σ��ҷ�Խ��ҡɽ��ȴ��Ϊ�˵�ɽ�������ˮ����������
����ˮ����ҡɽ������������ɽȪ��۶��ɵ�һ���ӣ���ˮ����ȴ���겻�ϣ���ʱ�ᱩ�dzɿ��µ����ѣ���ʱ�����������ĵ����ӣ�Ȼ�����Դ���������У�����˵���Ǻ�ˮ�ͱ��ˡ�
ɽ���������������Ǹ����Ȫˮ���ɻ�۾���һ���ٲ�ע��һ����̶�ͱ���ζ���������ֿ���ɬ���������õ�����֮ˮ��
�ҷ���ɽ���������Ǹ���̶��;�У���ľԽ��Խ�Ͱ��������ɫ��ʧ������������ʯ�����Ʒ绯��һ�㣬����ȴ�Ƿϡ�
�ٲ��Ӻ�Զ���Ĵ���ˮ������Ϯ����ȴ�ڽӽ��������˲�仯��һ���������������ѳſ���һ����Դ�������Լ����ܵ�ˮ���˺���
̶��ʕ����ˮ�����γ���һ��Ʈ��ĺ�����
�������һ�������������ѷ죬̶ˮ�����������͵ĵط���ȥ�����Ÿߵʹ����ʯͷ��������ңԶ�ĵط���۳�һ����ӣ�ע��������
Ȼ����֪����������ĵط�������������̶�С�
ˮ��ζ��Ҳ�Ǵ����↑ʼ�仯�ġ�
�Ҹ�����ȥ��̶ˮ���������Ĺ⣬�������Ͽյĺ��������������������ӳ������������
�Ҷ���������̶ˮ����û�취��Ŀ�⿴�ĸ�Զ����ˮ��������ճҺһ�㣬�������ȥ��մ��մ����ˮ�档
һ�ɱ����̹ǵ������ʱϯ��ȫ����
��ˮ��������
�ҵ����˿��������������������õ�����������Դ������ʱ���ҵ�����ӳ���һ�ֻ����Ĺ�â��
���������֪��������˵�Ϯ������ЩƮ�첻�������գ���ȫ��ȥ��
��ʱ���պ�̫�����Ʋ�������������ɫ������������̶�ϣ��ǵ���ɫ��̶ˮ����ʱӿ��������������������IJ��⡣
���������������Ե���̾�š�
�����ֺ�����������ƺ��ܰ�������ȥ�������ʸС�
��վ����������˫Ŀ��˫��һ���������һ��Ȼ���ϡ�
����Ҫ��ʲô����
һ����ǣ�ˮ��Ѹ�پ�������˻�����ɫˮ���ϳ��ֱ���ɫ���˻��������ѵ�һ���ľ�������Щ�ס��
�˻�������ӿ�����մ�̶�����һ��ˮ������ˮ�������Գ�һ�ΰ������壬���ţ��ҿ������շ�ŭ������
���������ڱ���ɫ���˻��������ģ�ֻ�����������ɼ���
����Ҫ��ʲô������ŭĿ���ӡ�
�����ҵ�һ�μ����ȴ����ı������������������������������������ŵ�����ɫ�ʡ�
�����Ȼ��ֻ�ȡ������������������
������ҵĻ���ʹ����������ȥ��ȴֻ��Ƭ�̣�Ȼ����Ȼһ��������ɫ��ˮ��һ���ij���������ϯ����������Ŀ�ɿڴ�����Щ�˻��γ�һ����ӯƮ�ݵ�ѩ��ɫɴ�¡����ţ���һԾ������̶ˮ�︡�������������������ҵ���ǰ��
������������̶ˮ�ĺ��������澧Ө�ģ���Ȼ��ˮ��Ľ�ɳ������ô�����ˣ�����ˮ�У��������ǽ�ɳ��
��ΪʲôҪ�����ʱ������ң�쾡����������������Ϣ�����ҵ���Χ���ơ���ʱ���Ҳ���ʶ�������Ľ�û���ˡ���������ֻ��һ��Ʈ���Ӱ�ӣ�����һ������ֲ����ҵ���ΧƮ����ȥ�������ķ�˿������������ҵIJ����
�����ʱ����ô�ˣ�����˵����
˭֪���������㶵Ķ�����һ�ᣬȻ������Ц�ˡ�
����������֮���ÿ���µ���Բʱ�����Ṧ����������������ʱ�������ܳ�һ��Ů�����ͻ����Ӱ��깦������
�Һ��������ţ�������������Ĵ�������������ҡɽ������ʱ��Щ��ͬ�����Ĵ��ݼ�ͬ��������˸�Ľ�ɳ�������������Ӷ��Ե÷dz���ĿѤ�á�����Ƥ��ͬɫ���촽�ϣ������Ÿ���Ľ�ɳ���ҽ���ס���������촽�������������������룬�������ԡ���
���������㶣�Ȼ���Ȼ�˵�̶�ġ�
������ʲôζ���������ľٶ����Ҿ�����֡�
��ʲô��û�С���
�����ԣ����ŵ��ˣ�һ���ر������ζ����������һ�������Ц�տ����ң�Ȼ��һͷ����ˮ�У�����һƬˮ����
�������ҽ��������������֤ʵ������Ļ���
ԭ�����������һֻ�ȣ��ҵ�ȷ����ˡ�
����Щ��ڣ����ǣ�ת���뿪��
�������ڣ��壩�Ѿ����²��������ϴ����������顢��������֡�ͼƬ�����۵ȣ���������������������FANS�������ϴ���ά�����ռ������磬��������Ϊ���뱾վ�����أ��Ķ�����С˵�뷵�ر���������ҳ
��������ڣ�����
�ص�ʯͷ�ǣ��ұ���ǰ�ľ����ˡ�
��վ�ڸ߸ߵļ�̨�ϡ�Ӯ�������棬�������������ԡ���������ۼ������Ը�������ij��Ϻ��塣���Ǹ����������࣬Ŀ���ȴӿ�������˲����Ĺ�â��
Īվ�������Ǻ�Զ���ſڣ���һ�ֲ�м����������̨�ϵ��Ρ�
��������ʲô�����Ҵյ�Ī�����ԣ�С���ʵ���
Ī��Ц�ţ�ȴ�Ծɶ����ε�һ��һ����
��Ѫ������
��Ѫ�������Ҳ��������������Ϊʲô����
��Ϊ����ֻ�ȡ����������ĵ���
�Ҷ�ʱһ����չ�۳���̨��ȥ��
������ѩ�����ӣ�������أ����������ݵ��ֱۡ���ʱ��Ӧ��ij���һ���֣���Ⱥ��һ�����Ű��µ�Ů�����˳���������������ʯ�ף�������̨�ϡ�������ɫ�ʹ��͵�Ŀ�����һ��������ж��Dz����ܵ���ij�ֹ����Ŀ��ơ�
ȴ����ʱ������ȥ���·�������**��վ�����
�����Ǹ�ʲô�������е㾪�ȣ�ת��ȥ��Ī��
Ī���۾����ʱӿ��һ˿�����Ц�⡣
����������֪���Լ�����ʲô�������ĺ��ӡ���
�Ҷ�ʱ���ס�Ӧ�貿���еĸ��˹��Ǵ�Ů��õIJ��أ������ﲻ�����������Ů������Զ�����ܼ������˵ġ��������а���Ȼ֮���ϰ�ߣ�ÿ�궼Ҫ���������Ʒ�����ר����ѡһЩ��ò�õ�Ů�������������¹ƣ�ʹ����û��˼�룬ֻ�������˵�Ҫ��Է�˯�������˼����ʱ����Ϊ������
����Щ�ɶ������ô������ª�״������ء�������Щ���ߣ�һ�����˳���Ⱥ�г�ȥ��
��ʱ�����ǿ�ʼ�������춯��
�����ȣ��Dz����Ż��ˣ������ǿ�ʼɧ�����ع�ͷ����
��ĬĬ��ע������Ⱥ������ӿ���Ż���һ��ķ߿���
����Ҫ���֣���Ӯ��Ȼ��������
���������û��һ˿���飬����ӹ���ɵ�����˵������쾣�������ķ�ŭ����
����������Ĺ�����Ȼ��һ�μ������ǵ���Ů����Ƭ�̵ij��ɺ�æ��أ��տ��Ĵ�����һ����Ƶĺ�����
Ӯ��Ŀ��ᶨ�����䡣�Ҿ�ǿ���������ӡ�
������ʱ���ξ�����������ļ�����������е�һ�ѵ���ѩ���ĵ��У�ֻ���������Ƶij��ȣ�ȴ�����ޱȡ�Ȼ���ҵ�����������һ������Ѫ����
��Ů���������Ͽ���
����������������������ɭɭ�ǡ���������û���κα��飬�Ծ�����Ŀ��ն�����һ�ַdz������Ĵ���վ���š�
Īҡ��ҡͷ��
��������Ǹ������ˡ���
���ţ���ȡ��һ�����룬�ŵ������ֱߡ�����ʱ���������ˡ�������������������ָ�������Ѫ��ջ���һ�������䡣�������������������ʦ�ض��������������������üͷ��
���������ܳɹ�������֪���������֡����������ȴ��������ڰ�ο�Լ�һ�㡣
Ī��ȻŤͷ�����ң�������졣
����֪����ֻ�ȵ����֣���
��̧�ۿ�����ȴʲô��û˵����������Ů����ֻҪ�Ҳ�Ը�⣬˭��û��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