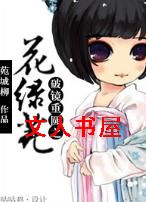髑髅之花-第8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母亲握着男孩嫩生生的小手,交到相识五天的盲眼女人手上。孩子的手掌柔腻温暖,轻扣之下传来纤细脉搏的跳动,如同一支安静地跃起火焰的蜡烛。
“那么,”芬妮说,“现在起,他就是你的儿子。”
还没有人——
“真高兴能认识你。”少顷,她用细不可闻的语声续道。
便在这刹那间,爱丝璀德看见芬妮的心向她敞开了。没有任何形象和言语能够描摹,只有一种或许名为“光”的、鼓荡着视野的物质奔涌出来,被它裹在其中的是一个微笑。也许那并非笑容,只是向上挑着的一弧伤痕,浅浅地,濡出血滴。一弦流着泪的淡红月亮。
她伸出手。
但所拉住的唯有虚空。
每个站在第一排绝望地等待那决定自己命运的马鞭选定祭品的人都看见了,那个毫不起眼的女人从队列里冲出来,扑向血斑虎,直到三杆长矛左右贯穿她的身躯。尽管如此,她还是摇晃了好一阵子,在葵花首领雪白的座骑上留下一抹瞧起来已不算怵目惊心的殷色。血斑虎揪起她的头发,令她看着自己,仿佛要从她垂死的眼中找出勇气的来源。“真是愚蠢啊,女人。”
女人咯咯地笑了。血沫迅速从她喉间向外涌着。“……这不是正好吗,”她艰难地说,“你如愿以偿了。”
血斑虎的手臂向上提了提。
“你们一直在找的刺客……”她的手自他臂上垂落,五道深黯的印迹,“……就是我。”
血斑虎怔住。
一旁怔住的还有所有人,所有靠的近而听见那句话的人,所有未听见却目睹首领一反常态的人,所有茫然等待着自己未知命运的人。
还有声音、风、尚未凝止的血流和鸦群。
“愚蠢!愚不可及!”马背上的男人猛然大笑,“你想救谁?一个弱不禁风连跑起来都像头绵羊的女人,会是人群中杀害两位导师的刺客吗?今天这里要是没个结果,所有人都得死!听见了吗?给我杀!给我把剩下的一个个杀光——”
“——妈妈!”
一个稚幼的童声接在了他的狂笑上,仿佛狰狞虬曲的死木忽地绽出了极小的嫩芽。还未及马腿高的男孩步步蹒跚,向血泊中的尸体走去。白衣黑发的女子跑出来,轻扭过他的脸,将她整个人拥入怀中。
长矛和利剑对准了她。她站在那儿,没有动,却也没有退缩。
“这小鬼在叫唤谁?是蠢女人的儿子吗?”男人振动缰绳,马蹄踩在尸体的脊背上。
爱丝璀德的表情平如镜面。
“他是我的儿子。”她回答,“他名叫潘格兰涅,是我的儿子。”
——潘格兰涅,鲜红的安石榴花。这是你向被判罪的圣徒求取的名字。这是你曾引以为傲,而今羞于启齿的名字。可它真的很美,不是吗?这是一个书写诗歌的人取的名字,这是我深爱过的人取的名字。他从被命名那天起就流有能与我相通的血液,曾凝目于我的灵魂亦曾温柔地注视他。他会活下去,远离暴行,远离灾难,他是妓…女的儿子,魔女的儿子,一个仍想极力保护她所失去之物的母亲的儿子。
他是我的儿子。
“你站在这里又是干什么?想跟刚才那蠢货一样下场吗?”
矛尖贴上喉咙。灼灼欲焚的热度。
'我期求这一刻已很久了'
“您不是……”
'我酝酿着说出这句话已很久了'
盲女深黝的眼眸微笑着弯了起来。
'我等待踏出这一步已很久了'
“您不是,”她曼声宛转,“说知晓刺客来历者,上前一步吗?”
——爱丝璀德,你是能触摸黑暗之人,如同阴影隶属寂夜,凡物心中只要是秘密和裂痕,都隶属于你的双眼。你将踏着人心的缝隙起舞,与他们的影子共语,从黑暗中汲取水泉,拥吻它予你的温暖;你是真相的女儿,魔鬼的妻子,呼吸间即可焚化一个灵魂,反掌间即可颠覆一个意志。你能用真实毁灭傀儡的面具,用灰烬的土壤填平深渊裂谷。请你铭记黑暗,这力量唯你所有,独一无二,不可战胜。
——你是吞噬月影的九音鸟,是人们遗漏在空气里的吐息,是风向莽林开翕的唇及其暗秘耳语。
——你是至察之眼爱丝璀德。
——你是“告密者”爱丝璀德。
“只要答允我的条件,”一字字地,她吐出终于在脑中完整成形的语句,“我可以告诉您我所知的一切……包括刺客的真实身份!”
作者有话要说: 潘格兰涅(Pomegranate),这个名字的由来见前编第17章,贝鲁恒出征段。
这几天沉迷DreamSelf(我忏悔),给文中几个角色捏了小人儿,当做迟到的中秋贺礼吧…w… 欢迎自由地发表意见!
☆、Ⅵ 捋锋(3)
她告过三次密。
最早的一次若要溯源,是在一个无星无月却喧如白昼的夜里。新圣廷建立了,新教皇登上宗座,新的圣徒被加封额印,不过那与她没有太多关系。唯一的影响是热血激昂的人们冲进妓院,要好好惩治这些将旧圣廷弄得污秽不堪的元凶。所有妓…女都被赶到陈列老教皇普拉锡尼首级的广场上,人们(尤其是女人)脱光她们的衣服,扯光她们的头发,拿火烫、剪刀戳、柳条抽打,肆意羞辱。她只记得自己还没到大半夜,就已连站也站不起来。但这不算最惨。最惨的是一个年龄稍长、平素就很照顾她的妓…女,绰号“金雀花”的,因为替盲眼的她挡了一下,让一大桶冶金用的强酸泼了一头一身。泼酸的妇人乘机冲上前,用切肉刀砍掉了她的双手。
“金雀花”被抬了回去。几天后,眼瞎、口哑、面目全毁、无力自理的她,被发现在自己的房间内吞了一整盒缝衣针。她死的时候,夜阑人静,悄无声息。
自戕是教典上的大罪。她被焚尸扬灰在乱葬岗,永世不得安息。
又过了几个月,新圣廷开始大规模清洗旧时代的残余分子。将“金雀花”毁容断手的那个妇人就在绞死的第一批名单内。证据确凿,她曾帮好色成性的主教坑骗农村少女,以换取她经营的店铺在哥珊城内的免税权。
爱丝璀德并不介意周围的人是用怎样的目光指戳自己。她拿到了很小一笔钱,同时也大病一场。不久,审判局负责受理告密的调查官员突遭横祸,落水而死。
爱丝璀德,黑暗赐福于你,然而你须遵守与黑暗的誓约。他人心中的暗影,不得公诸于阳光之下,否则不但听见秘密的人要为诅咒纠缠,你也会慢慢失去黑暗的信任与眷顾。你会重新成为普通人,弱小无力,路程险恶,永远等不到生命的奇迹。
她离开了哥珊。那是圣曼特裘即位后的第二年。她洞悉世人,然而对自己的过去一无所知。
她在各地流浪,用记忆里的草药学知识给人看病。摆弄草药的女人在旧圣廷被称为魔女,虽然新教皇说那都是欺世之谈,但民众的观念要立时从地到天也并非那么容易。她来到与以前家所在的地方非常相似的、名叫旺达的西陲小镇,一贫如洗,无人敢近。只有一家同样贫困潦倒、居住在城郊旧草棚的母子收留她同住。尽管她明白母亲更大的目的是期望她治好那八岁男孩的肺痨,但她仍然感激他们的善意。
孩子的病用尽法子也不见好转。但小镇的领主不知听哪个急着投资的商人说,这对母子住的旧草棚附近有钻石矿。部队在一个阴惨惨的凌晨踹开了漏风的木门,将她们三个撵了出去。哀求无用,母子俩唯一的财产——那间破屋,在大雨中被浓烟蚕食成了一堆灰烬。
孩子淋了雨,病得更重了。爱丝璀德清楚他剩下的时日。他有一个从来未曾、也永远不会向母亲提起的愿望:想摸一摸那把一直放在镇上最好的玩具店柜台上的,淬过火,涂过银漆,锃锃亮亮的骑士小剑。
那把小剑要十个辉银币。
但她们连十个铜角儿也凑不齐。
矿场开挖许久,钻石却迟迟不见冒头。领主大为光火,刚好这时接到那商人走私贵金属的密报。线人拿到赏钱,商人顺理成章地掉了脑袋,万贯家财也填进了领主的金库。而聆听黑暗秘密的领主终究没能逃脱噩运,他在镇民叫骂声中被一剑钉在了城墙上,夺走他性命的哈茂·格伦维尔,归来的流浪骑士,宣称自己才是旺达合法的保护人。
皆大欢喜。
但她一点也不觉得高兴。
锃锃亮亮的小剑插在男孩的墓堆上。
目睹她指证商人的镇民称她为“告密者”。传言和她的恶名像瘟疫一样散播开来。人们说她拥有魔鬼的双眼,能看穿黑夜中的一切灵魂。她与野兽…交…合以换取魔力。她用各种毒草调配春…药,蛊惑人向她献出身心。她在月明之夜变身女妖,吸人血,吮人骨髓。她于虚空中窥视每一个人,仿如阴影矗立身后,无所不在。
若不是那个自称她前夫兄长的哈茂子爵,她无法在镇上生存那么长时间。没人知道她为第二次告密付出了什么代价。断断续续差不多一年,她的黑暗视力都不能运用自如。
她一度以为自己是真的瞎了。彻彻底底地瞎了。
无所依傍。无所撑持。
教皇国上下开始兴起批斗贵族之风的那一年,哈茂到她的居所来找她。我要走了,这个平日嘻嘻哈哈不修边幅的男人异常凝重地说。国家已陷入到一个巨大得无从想象的漩涡之中,终有一天,它会毁掉我们所有的人性。我对这个地方有感情,不想看到仍爱我的人为考虑是否要反对我而面临两难境地。
——你想要我做什么?
——如果出卖我能救别人的命,那么,请你出卖我。
——荒唐。她说。真是荒唐。
她恍惚回到了许多年前,“金雀花”悄然死去的那个晚上。她守在不成人形的女人床前,用早已干涸无泪的眼睛凝视对方的心。伤势感染恶化,时间所剩无几。给我一盒针。女人沉默地说。
不,爱丝璀德说。自裁是罪孽,这罪请让我来分担。
罪孽又怎样呢……女人失去容貌的脸似乎微笑了。至少我还有自己选择的权力。至少我还有决定去地狱、而非天国的权力。
……哈茂,你觉得我的力量真可以救人吗?我的愿望如此微小,我不祈求良善的人都能幸福安乐,但求他们都能有尊严地活着。可我做不到,就算是逞一己之快的复仇也多么像自欺欺人。我至多,至多只能看着他们有尊严地死去。
无比荒唐。
如果我可以——我可以做什么,我仅仅只求他们都能活下去。
先是活着,然后才是尊严。
哈茂走了。几年后,他死在神断之中。带着他的尊严。
她的告密终究埋葬在了深心里。但即使什么有用的信息也没得到,梅瑞狄斯主教依然难逃诅咒,很快,被哥珊那场屠戮牧师的风暴卷得尸骨无存。
她遇见了那两个曾以不同轨迹穿错过她生命的男人。一个是她的过去。一个是她的将来。
她疲惫而惯性地活着。以自己固有的姿态活着。趋利避害,圆滑无争。
很多时候她感觉自己只是一个笔画寥寥的小人,被切割成数十上百的截面描在书角,风一吹,才翻动起来,沿着预设的无形轨迹舞蹈,而更多时间则是死气沉沉地呆在纸上。无数僵直交错的断线。
先是活着,然后才是尊严。
那场白白献出祭品的告密或许要一直延续到后来,当她在小木屋里叫破投毒妇人的秘密,从黑暗里瞬间涌起的巨大漩涡席卷了她。第一次,她开始恐惧它的后果,被时间封存的记忆像鹭鸟飞脱囚笼那样重返自由,但它们永不能飞得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