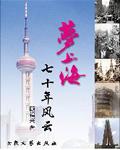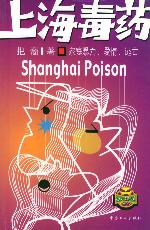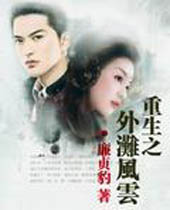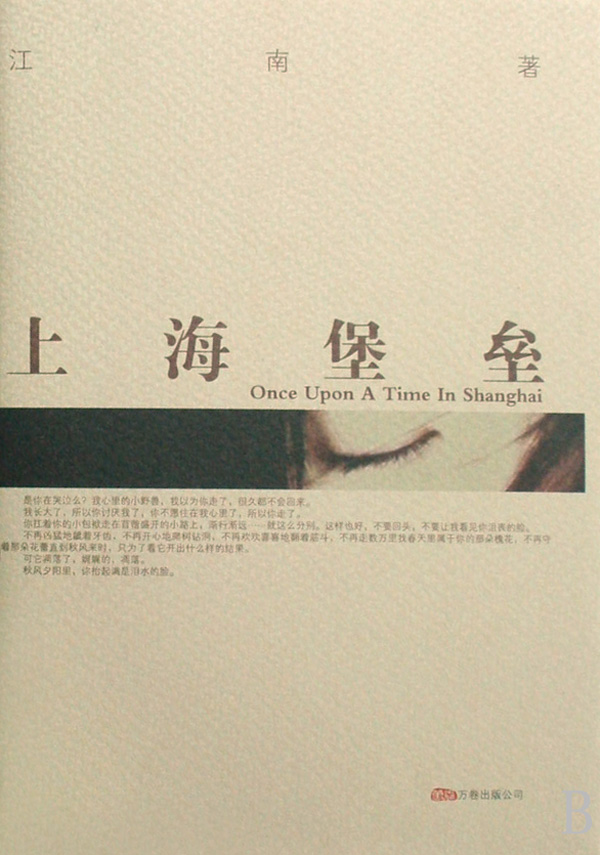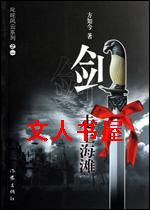上海滩风月女明星-第3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母亲没有再回答,默默地似乎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久久盘旋在孩子心头的疑问,赶走了她的睡意。沉默了一阵子以后,凤根把小凳子靠近母亲的身边,抬头又提出了问题:
“为什么我们不能上厂里做工?”
“我们是女人嘛。”母亲叹了口气说。
“女人就不能做事吗?”在她的幼小天真的心灵里,女子低人一等的观念还没有形成。
“社会是不允许的。”母亲抚摸了一下她的头发和脸,说:“睡吧,别瞎想了。船到桥头自然直,听命吧。”
夜更深了,寒风从不严实的门窗里钻了进来,把靠在母亲腿边迷迷糊糊睡过去的凤根冻醒了。她感到身上多了件旧毛衣,睁开眼睛望望仍在不停地缝衣、身子微微颤抖的母亲,禁不住说:
“妈,你太冷啦!怎么把绒线衫都给了我?”
母亲慈爱地说:
“你穿着吧。小孩子冻不起的。要不上床睡吧。”
“妈,我不冷,也不困,陪你做活吧。你还只穿件单褂呢!”
实际上,才6岁的凤根真是又冷又困,她终于在母亲的抚爱和督促下,爬上了又硬又冷的床铺。
在童年的梦里,她尝到的是人生的苦果。
穷人家的孩子是早熟的。凤根随着母亲,给有钱人家当小丫头,小小的年纪就学着打杂、洗衣、给老爷擦皮鞋、替太太抱小少爷。唯有相依为命的母亲心疼她,夏天,看到她累得满头大汗,面色通红;冬日,瞧见她双手起了冻疮,肿得很高,瞅着主人家出门的时候,让她放下手上的活计,悄悄去休息一会儿。
这时候,她总是很快溜到附近的一所小学,从校门的缝隙里偷望男女孩子们上课的景象。有时,凑巧孩子们放学了,她就躲得远远的看他们嬉闹、打架。他们都穿得很整齐,背着崭新的小书包,有的孩子的父母,还在校门口等候迎接他们。
这,给凤根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象。这,也使一个难以管束的想法在她头脑里转了又转。隔了好一阵子,她看到母亲忙完了活心绪较好时,终于忍不住说出了自己最大的愿望:
“妈,让我上学吧。”
妈妈听到她的要求,像被针扎了一样皱了一下眉心,半天没有说话。而当她拉着母亲的手,一再恳求:“妈,让我上学吧。”母亲的心动了,轻轻叹了口气:“难哪。”
母亲是这样一个老实,听命,苦苦挣扎的妇女。她没有马上答应女儿的要求,因为,她明白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学费、杂费、书本费、衣着这一连串的费用,对当女佣的她来说是很难应付的。再说,女儿上了学,还能在主人家吃住下去吗?她找不到答案。
母亲的心在那次风根的恳求后,确确实实留下了无法摆脱的印记。凤根是她世上唯一的亲人和寄托啊,何况,凤根自小体弱多病,丈夫刚去世之际,自己曾将她寄养在一个干姐妹家中,一场大病整整两个月,几乎葬送了一条小生命。
母亲尽管没有文化,但身居上海这样繁华的大都市,也约略知道读书才能有出头之日。从此,母亲默默地攒钱,也在主人家卖命地干活,博取老爷、太太的欢心。
冬去春来,约摸在两年之后一个晚上,母亲悄悄地对女儿说:
“凤根,你也不小了。妈明早送你去上学吧,这可不易啊。”
说着说着,母亲眼眶红了起来,声音也变得颤抖了。
凤根望着更加苍老的母亲,聆听着这字字千斤重的话语,一阵温暖,一阵心酸;一阵凄苦,又一阵幸福。夜依然是凉冰冰的,而她的心底却由于有了希望而感到热辣辣的。连她的梦也出现了一丝希望之光。
凤根8岁才上学念书,改学名为玉英。起初,进的是私塾,第二年,才转入崇德女子学校。
上学,对这个寡母孤女来说,实在是难上加难的事,费用的重担自不用说,而且,母女俩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她俩得苦苦求情于心肠较好的人家,让母女俩有一个栖身之处。
不久,一户姓张的人家收留了母女俩。这户姓张的是广东香山人,和凤根父亲是同乡。张公馆坐落在乍浦路,张老爷在清末是做官的,辛亥革命后丢了官,转而经商,全家从广东迁到了上海。
张老爷经商很有些手段,发了大财,整日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张老爷有妻妾九人,生下的子女计十七人之多。张太太管不住丈夫纳妾,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不致发生动摇,她绝不允许丈夫把这些女人弄回家来,也绝不承认老爷在外面生的孩子是张家的后代。
进了张家大院,何阿英带着凤根在后院佣人住房住下,她处处留心,很快就熟悉了新的环境。张府的大院共有三进,每进房子之间,都有着很大的天井相隔,前两进房子是上房,下人是不能随便进入的,只有后院才是下人们住的。
这位张太太共有四个公子,即长子慧冲,二子晴浦,三子惠民和小儿子达民。这兄弟四人日后和当时的上海影坛都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也都有过一些名气,其中尤以张慧冲和张达民名气最大。
张慧冲生于1898年,那年19岁,正在上海的航海专科学校读书,时刻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漂洋过海,发一笔洋财,后来他果然成就了一番事业。
他从航专毕业后,即东渡日本,抵日不久就对航海失去了兴趣,而迷上了东洋魔术,加上他自己勤奋钻研,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套东方魔术玩得堪称炉火纯青。
20年代初归国,很快又迷上了电影,加盟中国最早的电影摄制机构之一的商务印书馆影片部,当上了一名电影演员。主演了《莲花落》、《好兄弟》等片,他那英俊的外貌、洒脱的造型,颇受影迷喜欢。
1923年春,有个叫尼古拉的德国人来到上海进行魔术表演,为招徕观众,他自封为“德国魔术大师”,大言不惭地吹嘘自己天下无敌。张慧冲很不服气,待观看了这个德国人的表演后,他更是胸有成竹,他马上和尼古拉唱起了对台戏,也准备了一套魔术登台表演。
他表演的这套魔术不仅包含了尼古拉的所有节目,而且还多了一个他独创的巨型魔术“水遁”。此事一下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报纸则称之为“国际魔术大竞赛”,盛赞张慧冲“比尼古拉多一手”。
尼古拉还算识相,见比试不过,遂偃旗息鼓,溜之大吉。此后,张慧冲又在电影界和魔术界大显身手,曾大红大紫过。此乃后话,暂且不提。
张达民的“成名”却不是因为有何业绩,而是因为他后来与阮玲玉(即凤根)的特殊关系。张达民生于1904年,长凤根6岁。凤根8岁入张府时,张达民还是个14岁的孩子。
张太太对这个小儿子格外宠爱,凡事皆依着他,使他成为典型的公子少爷。张太太是个麻将迷,所有的时间几乎都沉迷在牌桌上,张达民从小跟着母亲,牌艺也是十分精通,且赌瘾极大,由此埋下了日后赌尽数十万家产的祸根。
凤根上了学后改名为阮玉英。玉英随母亲进入张府后,更加劳累了。放学后,她还得像小丫头一样干活,比往常更卖命地干活。要不,母女俩马上连一个可以这风避雨的住处都会没有了。
年幼多病的玉英,并没有被这种艰难的境遇压倒,随着年岁的增长,随着知识的开化,也变得自信了,坚强了。
清晨,当她忙完主人家的杂活,迎着初升的太阳向学校走去时,她的心里反复响起了一个声音:“我要做个自立的女子!”
黄昏,当她离开学校急匆匆地赶回主人家时,母亲的面貌和话语出现在她眼前耳边:“听命吧!”“不,我定要做个自主的女子!”她的内心时时在和母亲作着争辩。
这种发自内心的精神力量,使她自小有无穷无尽的求知欲。她比许多富家的孩子学得认真,进步得快。年幼的孩子,谁不贪睡呢,而她,常常忙到主人们睡了才能学习,常常要熬到深夜;天色微明就得起床,偷偷温习了功课又要干活。她不觉得苦,也不怕累,一心要念书识字,成为“自立的女子”。
上海,是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富商阔人的天下,又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大都市。玉英渐渐长大了,学校里的功课对她已经不那么费力了,她开始借来许多小说之类的书来读。
小说是五花八门,杂七杂八的,而她从中一次次体验了各种人、各种生活的甜酸苦辣。她嗜书如命,终生不变。这,也不知不觉地在她身上培育了艺术的细胞,对她走上电影演员的道路有莫大的影响。
一晃三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玉英已是四年级的学生。她品学兼优,对于国文和音乐尤为爱好。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借到了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邓肯自传》,刚读了几页就被书中的描写吸引住了,于是手不释卷地一口气读完了全书。
美国舞蹈家邓肯为舞蹈事业终身奋斗的事迹和精神深深地打动了玉英,在她的眼前,仿佛出现了邓肯像森林女神一样薄纱轻衫赤足起舞的形象;而邓肯向往自由,不畏权贵,坚持信念,勇于创新的坚强意志,更赢得了玉英由衷的敬佩。
掩卷深思,玉英沉入了对艺术追求的遐想之中。《邓肯自传》无疑又为她开启了一扇探视艺术殿堂的窗户,激起了她心中对表演艺术的憧憬。
1922年初的一个周末,玉英的同学好友谭瑞珍、梁碧如兴奋地告诉玉英,她们已搞到三张《海誓》的电影票,准备一起到夏令配克看电影。
以今天的眼光观之,《海誓》无疑是一部极其平庸的电影,但它却令玉英和她的两位伙伴既觉新鲜又受感动。要知道,《海誓》可是中国最早的三部长故事片之一,不仅有完整的故事,而且制作也比较认真,尤为称道的是该片的女主角殷明珠。
如果说《海誓》曾使得小学高年级的学生阮玉英对中国电影产生了兴趣,并有了一种朦胧的向往,那么,1924年底上映的一部中国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明星电影公司摄制的长故事片《孤儿救祖记》,则使已成为初中生的阮玉英对电影有了更为深厚的感情。女主角王汉伦的杰出表演使玉英萌发了演电影的最初愿望。
应该说,殷明珠和王汉伦的成功,为阮玉英、胡蝶等这些比她们年轻了几岁的后来者,冲破世俗偏见,顺利地走上银幕,开辟了一条道路。
1925年,阮玉英已是崇德女校初中部二年级的学生了。自从升入初中后,玉英便搬出张家,开始住校了。阮玉英到张家的次数逐渐减少了,但闲暇时,她还是偷偷溜到后院去看望母亲。她的偶而露面,引起了张家四少爷张达民的注意。
张达民这年已22岁了,作为一个富家子弟,在交际场所和生意场上也可谓见多识广了。但当他第一次留心注目已是中学生的阮玉英时,仍为她身上所特有的超凡脱俗的气质和带有一丝哀怨的漂亮面容所震惊不已。他怎么也没料到当年瘦瘦小小的黄毛丫头,现今居然出落得如此楚楚动人,不由得怦然心动。
于是,他想办法接近阮玉英,当他得知玉英喜欢到昆山公园散步时,心中不由一喜。
秋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