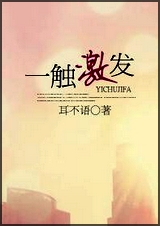一触即发-第7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圣灵能使人知罪、悔改、重生……”杨羽桦喃喃地说,他的眼神呆板、迟钝。
“您知罪了吗?爸爸。”慕次的话很冷。
杨羽桦沉默了一会,说:“你恨我是吧?孩子。”
“是的。我恨您。恨、痛苦、怨,都堵在我胸口,您明白吗?我甚至不知道该叫你叔叔好呢?还是叫爸爸?”慕次说。
“你都叫了二十几年的爸爸了,还是叫我爸爸吧。”杨羽桦说。
“爸爸,我自始至终都不明白,你为什么会做出那些种种丧尽天良的事?我亲生爸爸,他是你大哥,我亲生母亲,她是你嫂子,你怎么能为了自己所谓的荣华富贵,你杀嫂诛侄、害兄焚宅、变节求禄、通敌卖国?”
“孩子,我自始至终都是爱你的。”杨羽桦答非所问地说。“你知道吗?孩子,那可怖的夜晚,一直萦绕在我心底,挥之不去。噩梦,噩梦如影随形,我每天夜里都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想也许时间能够冲淡一切,包括罪恶感。我不断地拒绝回忆,我对你就像……就像亲生孩子一样怜惜,儿子,我想,只要你健康的活着,我们杨家就算有了后,总可以减少我的一分罪过,我想救赎自己的灵魂,我想洗刷自己身上的血腥。”
“你的罪,不仅无法洗刷,也没有可能救赎。”慕次冷静地说。
“我曾经想过杀死你。可是,我每一次都放弃了,包括对你哥哥的追杀。”
“你炸毁了他的诊室。”
“那是那个贱人干的。”
“可是你执行了她的命令。”
“是的。其实,这是我们的最大的败笔!”
“为什么?”
“因为,他太强悍。我们自己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强悍的敌人。”
“你们没有估计到,我哥哥的能量。”
“是的,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一个下贱的家奴出身的人,会如此果决、睿智,并且具有强大的攻击力和杀伤力。”
“您后悔了?”
“是的。”杨羽桦说。“所以,我想到了死。死亡,是最好的镇痛剂。”
“您想自杀,却选择了在一个无辜女人身上绑炸弹,人怎么可以无耻到这步田地?”
“当双方人马厮杀殆尽的时候,没有人会在乎谁是否无辜。孩子。”
“您承认自己有罪,却不肯悔改?”
“我无路可逃,孩子。”
“你可以选择去自首,去承担罪责,去向全社会揭露二十年前杨氏家族毁家焚宅的事实真相,让日本人侵略的野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纵是以身受死,你的灵魂还可以安息,那些屈死的亡灵才能安眠于九泉之下。”
“不可能。”杨羽桦脸色灰白。“不可能,阿次。'真相'是我永远无法面对的。孩子,你要救我,救我,孩子。二十年来,我对你不薄啊,孩子。你忍心眼睁睁看我去走绝路吗?”
“不可能。”杨慕次说得很坚决。“不可能,爸爸,您需要面对,面对您所犯下的罪行,您要给、给我被害的父亲、自戕的母亲、被炸死的姐姐、被烧死的亡灵一个公道。”
“我养育了你二十多年,我们二十多年的父子啊,阿次……”
“爸爸!”阿次正色地一字一句地说:“如果我亲生爸爸、亲生妈妈还活着,他们也会养育我,栽培我,爱我,珍惜我。是你剥夺了他们爱我的权利和义务,是你残忍地分开了我们的亲情天恩。如果他们在,我相信,他们会做得比你好。”
慕次决绝的表态,让杨羽桦感到万念俱灰。
“孩子,你知道,人总归是惧怕死亡的。就在半个小时前,我鼓足了勇气,去迎接死神的臂膀,却被你给破坏了……其实,自从玉真死后,我一直郁郁寡欢,你母亲很美,我说的是你的亲生母亲,她是世上少有的美人,缨子无论怎么样的刀刻精描,毕竟是'赝品'。你说,我死以后,能否再次见到她?”
杨羽桦的意思很明显,他准备自杀。
“孩子,你帮帮我。”杨羽桦说。
“怎么帮?”
“你开枪打死我。”
“你会向我开枪吗?”慕次反问。
“不会。”
“这也是我的答案。”慕次说。
“或者,你把枪给我。”杨羽桦的态度十分真诚。
慕次看着杨羽桦的眼睛,一秒、两秒、三秒,他把身上的手枪拿了出来,背转身递了过去。
时间仿佛静止,慕次以耳代目,他仔细地听着杨羽桦不均匀的呼吸声。
三秒、两秒、一秒!
“慕次。”杨羽桦说。“对不起。”
杨羽桦果然变卦了。
杨慕次回头望去,乌黑的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胸膛,慕次很失望。
“我哥哥就在外面。”慕次说。“枪响之后,您想过自己的下场吗?”
“我没想杀你,儿子,不过,你给了我重生的机会。杨慕初是不会让你死在我的枪口下的,我有你做筹码,也许,我还能有一条活路。”
“杨慕初连自己的女人都会拿来做诱饵,他会在乎一个认贼作父二十年的人吗?”
“会的。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他会救你的。”
“二十年前,你不是为了一件衣服,亲手剁了手足吗?”
杨羽桦的手开始哆嗦。
“你手上根本没有任何筹码,你听我一句忠告,或者,跟我去自首,或者,自行了断。除此之外,别无它途。我保证,看在您二十年来抚养'恩情',无论您选哪一条路,我都尊重你,你死后,我给你戴孝扶棺。”
“这两条路都是死路!”
“人一生下来,就在死路上走。不要走得太难看。”
“不,我现在不想死了!”
“那也由不得你了!”慕次不退反进,突袭似的右手一把握住了杨羽桦拿枪的手。杨羽桦大惊失色,大汗淋漓地扣动了扳机。
枪里根本没有子弹。
杨羽桦的脸色仓皇至极。
杨幕次的左手掌松开了,五颗子弹从他手心里滑落。
“我们的父子情份尽了。”
“阿次,你听我说……”
阿次转身就走,没有任何意识地往前走,与此同时,一群人与他擦肩冲过,身后传来杨羽桦深嘶力竭的哀嚎声:“阿次,照顾你妹妹……”“求求你,阿……”排枪响过。阿次浑身战栗,阳光底,整个庭院显得幽静美谧。满身披着夕阳碎影的阿初迎面走来,几米外,阿次也能感觉到阿初身上的杀气。
阿次走到阿初面前,身子一软,仆地倒下去,阿初抱住他。
阿次浑身滚烫,面无血色。
“放过我妹妹。”这是阿初最不想听的一句话,也是阿次昏迷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天花板上悬吊的莲花灯,灯色柔和,满室的梅花香气混杂了中药的气息,充溢着家庭病房的温馨氛围。
慕次睁开了眼睛,他感觉自己的身体酥酥软软的,应该是高烧才退,他抬头看了看四周摆设,知道自己又回到了阿初在长乐路的住所,他支撑着向床头斜靠,往床头柜上瞄了一眼,上面居然放置着一座水晶冰山。
慕次紧张地掀开被子坐起来。
这座水晶冰山是慕次十五岁那年,妹妹杨思桐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这座水晶冰山一直放在自己的卧室里,怎么会突然在阿初的家里出现?
紧接着,他看见了床头柜上整齐地摆放着一叠报纸,他伸手取来阅读。报纸的种类很多,有:《申报》、《上海新闻报》、《申报月刊》、《东方杂志》、《奇闻报》、《新闻月报》等等……
慕次知道,阿初是用另一种方式来告诉自己,这两天来上海滩上所发生的大事件。赫然醒目的大标题,一个又一个夸张的惊叹号,纷纷闯入慕次的眼帘。
“上海滩金融界大亨杨羽柏杀妻真相揭密”、“杨氏银行易主,疑为'宫廷政变'”、“杨羽柏开枪拒捕被当场击毙”、“杨羽柏、杨羽桦兄弟照”、“二十年前杨家老宅焚毁之谜”、“日本间谍百川丛惠子在监狱内自戕”、“杨家新主人探秘”、“杨氏千金杨思桐行踪成谜”……
慕次的神经绷起来,急忙忙穿上鞋子,站起来往外走,他的身体轻飘飘的,脚步也飘忽不定。他推开门的一刹那,听见楼下客厅里传来阵阵欢畅的笑声。
客厅里灯火辉煌,阿初正陪着汤少、跃春、韩禹三人闲话,四个人俱是春风满面,大约刚用过晚餐,饭后纵意而谈,全没题目,只不过绕来绕去,都落在阿初的头上,一个个妙语连珠,不断诱发“有色”谈资,笑语声四彻。
慕次站在楼梯上,忽然看见一个素花旗袍的倩影,隐身在楼柱侧,不用说,他也知道是雅淑,雅淑身上特有的淡淡香气熏染在楼道上,楼道的面目也幽馨不凡了。
“阿初如今扫荡阴霾,重掌乾坤,通杀股市、银楼、工商制造,前途未可限量。”汤少说。
“岂止商场得意,阿初情场也得了意了。”跃春说。
“此话怎讲?”韩禹问。
“阿初决定娶妻了。”跃春说。
“谁?”汤少明知故问。
“哎呀,这件事说来话长了。”跃春说:“那位有姿有色的格格跟汤少也有过瓜葛。”
“和雅淑。”韩禹答。
“阿初,你是一贯崇尚儒家传统的,按儒家地说法,娶妻娶德,娶妾娶色,阿初你究竟是娶德呢?还是娶色?”汤少问题刁钻。
“照你地说法,有德的女子都没有姿色了?”阿初抗议。“断章取义嘛。”
“汤少,不要被他中途改了题目。你只问他,'朋友妻,不可欺'?”夏跃春提醒。
“对呀,平常一副封建卫道士嘴脸,换做自己就另当别论。”汤少说。
“活天冤枉。汤少可曾明媒正娶?”阿初不依。
“我家下过聘金,她家收过彩礼。”汤少笑。
“你横刀夺爱,不合传统。”跃春说。
“儒家传统,用于自勉。”阿初不得已虚晃一枪。
“大家都听到了,他自勉不自律啊。”跃春一味地凑趣起哄。“你们还没有深察其心,原来从前都是违心话。现在,对付这种口是心非的人,只有一种办法,我们把雅淑小姐请下楼来,要他当面表白,下跪求婚。”
“你文明戏看过头了你?”阿初笑着推搡跃春。
“我们锄强扶弱,责无旁贷。”汤少支持跃春的建议。
“对呀,若要汤少不追究,少不得请雅淑小姐下来,讲讲你们的自由恋爱史。”韩禹在一旁帮。
“你们简直'党同伐异'嘛。”阿初故意怪叫起来。“小心我报复!”
“哇!你还敢报复?你如今是强弩之末,还敢嚣张?”跃春说。
“跃春,今天就你兴风作浪。”阿初说。
“这是你说的?小心我讲出点故事来……”
“有故事听?”汤少来了兴致。
“故事多呢,有异国风情、雨夜夜奔、玉镯遗情、舞场邂逅……”
“夏院长,夏院长,夏公子,夏老爷。”阿初一迭声地叫,笑着站起来作揖。
“我们不管,总要雅淑小姐下来救你。”跃春笑。
“雅淑面薄,夏老爷您包涵。”阿初说。
“我看阿初将来一定是个惧内的。”汤少怪笑。
“他倒不是惧内,只不过,爱深情重,百炼钢也要化做绕指柔。”跃春说。
慕次听到此处,默默朝雅淑望去。
只见雅淑嘴角咬着丝帕一角,两只手拽着丝帕两角,淡淡浅笑,无限幸福之意流溢于眉间眼角,一缕春魂,绕着丝帕低回婉转,满腹深情眷恋。
“你婚期订了没有?”韩禹问。
“下个月初六。”阿初作答。
“阿初,在你结婚前,我想让你有个最后的选择。”韩禹说。
“什么意思?”阿初问。
“阿丛惠从法国来信了。”韩禹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
阿初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