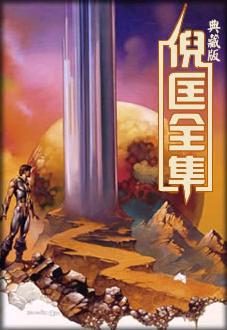媚君蛊-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不是会读心术吗?你且读一读便知道了罢。”阮子悭低头脱着鞋子,语音淡然无波澜。
什么?老子读不懂你又怎地了?火冒三丈的小银噌一下就跃到了阮子悭面前,两者相隔不过几步远,“你那晚都将我家姑娘抱上床了,还想抵赖?不过,你最好不要想我家姑娘,因为我不同意!哼!”
“别想把我家姑娘抢走!”高昂着头游移上房梁的小银极是霸气地甩下一句话后,便消失地无影无踪。
阮子悭也只是轻笑着摇了摇头,若是这小银也是个人的话,看来也算是情敌了。
三月末,医馆愈发忙碌起来,而荆韩交战的消息也不断从前方传进缃白镇,几天一小战,一月一大战,这可苦了荆韩交界的民众,战火之中自是拖儿带女的四散逃离而去,这缃白镇自然也会涌进些难民。
每日诊脉从不停歇的阮子悭虽说依旧一副寡淡模样,可见到这民不聊生的景象,眉眼间的忧虑不免也多增了几分,乱世之中,谁也别想过平静的日子。
就在两军伤亡惨重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时,阮子悭的房中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条散着粼光的绿色大蟒蛇,在房梁上游移的速度极其缓慢姿态也极其优雅。
“公子,荆地将士怕是撑不住了,您……”
大绿缓缓地吐着芯子,似是很犹豫却也很着急。
另一屋中的小银蓦地有一种地盘被侵犯的强烈感觉,遂循了气味甩着尾巴就进了阮子悭的房间。
目光霎时交接,大眼瞪着小眼,碗口粗的蟒蛇对着指头细的银蛇,周遭气息瞬间停滞。临阵脱逃不是小银的本性,许久才捏着胆子嘶嚷道:“阮,阮子悭,别以为你找来帮手,老子就会怕你!”
“忒地无礼的小子!你打哪儿来的?”看似年岁已久的大绿摆出了老者该有的气势,脱口而出的话语也有着训诫百蛇的威严。
“老子活了六十几年,还怕你不成?”心底发虚的小银很是悔恨自己生了这么一副细小的皮囊,否则它现在至少能当上一方蛇王呼风唤雨,此刻一想到蛇王二字,小银立马挺直了身子飘着声音鄙夷道,“看你才像是初出茅庐的小子吧!”
“什么?”向来被人尊敬惯的大绿一听这等藐视之语,火红的信子吐了老长,“我活了六十几年倒没见过你这等无礼的小子!想来也是河边石缝里蹦出来的野小子!”
“胡说!”气势骤增的小银被大绿的话语刺激的彻底燃起了斗志,昂首吐信就是一番挑衅,“你有本事给老子下来!”
大绿倏地滑下房梁本想再说教番,孰料小银探着头就猛扑了上来,尘土飞扬下,加起来有一百二十多岁的两条蛇彻底扭打在了一起。
翻看医书的阮子悭也没有管闲事的心,对眼前的混战一概无视。挂了彩的小银心下仍旧不服输,拖着大绿就往外一阵撕扯,气喘吁吁的大绿在得到阮子悭的默许后,无奈只得出去继续纠缠。
目送着两条蛇扭打着离去后,阮子悭才将心思转到了荆地将士身上,看来有些事情终究是避不掉的。
在药舍捣药的向雎一下午没见小银,总觉得不对劲,可又不能对别人说,只得抽了空闲去寻阮子悭,喝着茶的男人只淡淡道:“它出去玩了,不用担心。”
同一时刻在田野外被扁的哭爹喊娘的小银早已将阮子悭痛骂了几千遍。
随着夜幕降临,医馆又来了一拨不速之客。
重重的敲门声惊醒了医馆的所有人,当前堂的灯盏亮起时,打着哈欠的竹青开了门闩,可还未待他将一个哈欠打完,来人已跨步进门将十锭金子倒在了桌子上,亮闪闪的金黄色刺得每个人眼疼。
“听闻阮大夫医术不错,希望您能诊治一下我家公子的病。”披着蓑衣的彪形大汉对阮子悭倒也敬重,语气上也皆是商榷,“诊金方面我们不会亏待阮大夫,这十锭金只是定金而已。”
“我家公子不医官宦,您请回吧。”早已清醒的竹青瞥着门外的马车,言语之上再冷淡不过。
在这乱世之秋,官宦之家还是避过最好,阮子悭是这么吩咐过,但此刻打量了这些不明来路之人,阮子悭心下已了然了几分,因那蓑衣下的行装他是认得的,只怕这些人是在战场了负了伤才连夜赶到了这里。
“把你家公子抬进来罢。”略一沉思的阮子悭对着竹青挥了挥手,而后便示意明海与向雎张罗药材。
当四名着蓑衣的彪形大汉将一裹着黑狐大氅的男子抬进屋时,青石板上已淅淅沥沥滴了一行触目惊心的血迹。
两名大汉将男子小心翼翼地置于躺椅上时,许是牵动了伤口,一阵低嘎的声音自那人的喉间传出,听来让人禁不住一阵哆嗦。
俯身上前的阮子悭捏着狐毛缓缓拉开了大氅,恍然被暴露于灯光下,气息微弱的男子或许不是很情愿,极是痛苦地蹙了蹙眉,而后凭借意识睁开了眼睛。
四目相接之际,脸色惨白的男子竟瞪圆了眼睛发出一声含混不清的呜咽,而后便晕了过去。
而手臂停滞在半空的阮子悭同样惊异地发出一声隐于喉间的低呼,寡淡的面容之上霎时现出万千神色,向来淡然的心境一下子轰然倒塌,只剩残片碎屑。
十年了,兜兜转转还是见面了。
作者有话要说:小银:老子是蛇中之王,老子才是楠竹!把那小绿给老子写死!写死!
大绿:小逼崽子看把你能耐的!
小银:#@*&#*&
☆、偷听
阮子悭那略一呆滞的细微动作尽数落入了向雎眼中,可他紧绷的惨白脸颊却避过了所有人,在背光的暗影里,是那么的无奈,却又那么的痛苦。
“公子,您确定要医治吗?”竹青见阮子悭迟迟不动,以为他家公子又有些犹豫,岂料回过神的阮子悭只是示意来人将晕过去的男子往后院抬去。
明海提了灯笼往前方引着,向雎背着沉重的药箱尾随在众人身后,细细的眉毛皱成了两条小蚯蚓,这不速之客竟莫名的让她生出一股厌烦的感觉。
众人从前堂快速穿过回廊后,为了节省时间,阮子悭直接命人将男子抬进了距回廊最近的向雎房间,此时刻救人最要紧,也没那么多礼节讲究。
四位蓑衣男子安置好一切后,便对着阮子悭一拱手而后埋首踱出,静静地护在了门外,明海有些惊诧地咋了咋舌,看来这位公子应该是位将军,这种训练有素的手下可不是一般人能带出来的。
应了阮子悭的吩咐,老陈急急去饭堂备了热水,竹青则细细地挑了烛芯而后又将火盆拨旺了些,每个人心下焦急却也没有忙乱。
黑狐大氅被褪下时,向雎赶忙上前将被子覆在了那人身上,只近距离的那么一瞥眼,向雎的小心脏便咯噔一下跳到了嗓子眼,床上之人的面孔有些熟悉,似是在哪里见过,可又有些记不起是在哪里。
怀了心思的向雎注视着那人衣服袖口处细密的金银丝线,而后视线又不自觉地游移到那煞白如雪的脸颊之上,细密的睫毛遮盖着眼睑下的阴影,紧抿的薄唇自成一条线,看去静谧如熟睡之人,可细看去那眉宇间却散发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阴鸷之气。
“去兑盆温水罢。”俯身在床侧的阮子悭抚了抚走神的向雎,然后便将她轻轻推离了开去,被迫转身的向雎下意识的回头时,阮子悭已掀开被褥剪开了那人的衣袍,此时她才猛然注意到那人的胸前插着一支被斩去箭身的毒箭,而暗黑的血液也早已结痂。
那粗粗的箭头光是看着就让人不寒而栗,何况还是深插在人肉当中,顿觉一阵恶心的向雎埋了头就急急转身离去,竹青怕她一人提不动热水,便也尾随而去。
阮子悭细细观察着那已被止血的伤口,若有所思地瞥了眼门外的四个蓑衣人,心下了然了几分,想来军医只是止了毒素蔓延,剩下的也不敢贸然动手,所以才连夜转移到了这里。
难道自己的行踪早已暴露?思绪翻转的阮子悭也顾不得多想,命明海开了药箱便要剜肉拔箭头,纵使明海跟随阮子悭多年,但这一血腥的场面他还是有些经受不住,从旁递布巾时,不免止了鼻息避过头去。
竹青提了热水掩好门帘后,向雎才急急将水盆端放在了床前的木凳上,正专注做着处理的软子悭将布巾连同箭头扔进了盆里,接下来是一团团染了血的布巾,暗黑之色在水中肆意的蔓延,宛若无间地狱的浮灵即将挣脱而出。
一阵阵恶心感袭上心头的向雎捶着胸口倒退了几步,堪堪撞在了正欲上前的竹青身上,他本想帮着阮子悭包扎,孰料他家公子尽数包揽了一切,并未让他上前帮忙,这在他追随阮子悭以来还是第一次。
“去我房里休息罢。”暂且忙完的阮子悭揉了揉向雎毛茸茸的脑袋,言下之意是这间房已经被征用了。
向雎虽觉不大好,但她此刻很想逃离这间屋子,便应声点了点头。当她回到阮子悭房间时,侧耳听见竹青等人也相继离去,她便想着阮子悭应该也会回来休息,如此小的念头一闪过,向雎的小脸颊又红热起来。
“若是公子回屋休息,那总不能与公子同睡一床上。”喃喃自语的向雎轻撇着唇角四处瞅了瞅,亮亮的眼神最后定格在书案旁的大木椅上,或许在那上面窝一晚上也不错,总不至于给公子添麻烦。
心下还是有些害羞的向雎站在门口又等了会儿,她见阮子悭迟迟不归,而自己又实在困得不行,干脆裹紧衣袍直接窝在了木椅上。
春日她是总有些嗜睡,在心心念念着阮子悭时,小丫头已枕着手臂迷迷糊糊睡了过去。由于前半夜倒腾着忙了许久,她自是一觉睡到了天明,这本是一件很舒畅的事情,可在睁眼醒来的瞬间,小丫头惊恐了。
因为她躺在了阮子悭的床上,身上还盖着阮子悭的被子,周遭一切都充斥着那个男人的气息。乱了心神的向雎卷着衣袍就往地下奔去,纵使水渍湿了罗袜她也犹自不知,在奔出十几步后,向雎才忽然想起鞋子还在木榻上。
当她猫着腰小心翼翼返回床榻边时,才发现空落落的床上只有被褥,眼落之处压根就没有那个令她脸红心跳的男人,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自己夜游了?
百思不得其解的向雎整理好床铺后又讷讷地发了会儿呆,直至房外响起一阵嘈杂的脚步声时她才陡然回了神儿,莫不是昨晚那位公子出了什么事?
当向雎从阮子悭房间走出时,后院的走廊上已空无一人,连昨晚她房前的那四位蓑衣人也没了踪影,向雎下意识去推自己的房门时,却霍然听见里面传出一陌生男子的声音。
“能在这里遇见你,说明你是人不是鬼咯!”略带戏谑的声音传出后便是一阵低咳的喘息声,想来应是昨夜那位中箭的男子,心下如此想的向雎有些不悦地皱了皱眉,都被伤成了那样,怎么一开口就是刻薄。
“躲了十年,你还要躲吗?”又是一声压抑着苦痛的质问,声线慵懒清冷。
躲了十年?小心脏怦怦乱跳的向雎又往门前侧了侧身,看来公子果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若不是十年前发生的事,现在受这一毒箭的只怕是你了罢。”无奈到让人心酸的声音直直飘进了向雎的双耳里,堪堪将她的心绪搅的一团糟乱,她现在很断定这受了伤的男子肯定与以前的阮子悭认识,或许阮子悭被蛊毒所害的来龙去脉他也知道。
“你认错人了。”阮子悭淡淡回应着,简短不含任何温度。
向雎光是想就能想到阮子悭抿唇负手而立的疏离模样。
“别人我可能会认错,但你,绝对不可能!”从齿间挤出的一句话仿似蕴含了怒气,一阵静默后,便是止了气焰的喃喃自语,“现在关于你就是个禁忌,因为所有人都欠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