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此时,各地赶来参加会议的将佐以及南京政府方面的文武官员们,都开始络绎不绝地入场。在会场内,南部正和几个许久不见的同僚互相打着招呼,却见两个中国人走了过来。其中一个年轻人似曾相识,用流利的日语替他身边的那个中年男子介绍说,这是江苏省政府李士群主席。
南部一愣,随即省起,这就是在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特工头目:李士群。此人和梅机关的影佐贞昭中将关系极其密切,是个不可小视的人物。那年轻人自我介绍,说是姓周,海陵人氏,正是他第七旅团驻扎之地。南部想起了,那天在旅团部召见的周繁盛原来是他的弟弟。他就是汪精卫的手下亲信,周繁昌。
三个人客气地握手。李士群脸上浮现着暧昧的笑意,说:“听说旅团长南来的旅途上,受了小小的惊吓,不要太过放在心上。江南风物犹盛,大可趁这个机会放松、放松。”
南部心中暗暗吃惊,想不到这个特工头目的情报如此之快,不过一夜,此事竟已被他得悉了。他佯作轻松地表示,自己是军人,随时都可以为天皇献身。昨日遇险,只是桩小事,不足挂齿。繁昌一脸的敬意,恭维了他几句,邀约他散会后去晓月楼饭庄,小酌几杯。
接下来的会议,由派遣军参谋长柳川中将主持。畋骏六大将和汪精卫分别讲了几句,便转入正题。此次清乡,不同于前一阶段的规模和范围。为了彻底解决苏浙境内以新四军为主要对手的武装力量,使其成为大东亚圣战真正的战略基地,派遣军决心集中皇军3个师团,皇协军12个师共计30万人的总兵力,在苏浙地区开始清乡。
第一阶段,自明年春节至春天,解决军事进攻问题;当年春天至冬天,解决围困肃清问题;冬末力求将敌人的有生力量全数剿灭。至此,苏浙境内,不允许有大规模的敌方武装存在。南京政府方面,汪精卫自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长,江苏省清乡负责人李士群,浙江省清乡负责人高冠吾。
第三章(6)
南部旅团得到的使命,是由海陵向北500里范围,与友邻部队一起,将活动于这个地带的新四军一个军区,正规部队加上地方武装3万余人挤压围困,聚而歼之。此次清乡,分五个区域同步进行。江南以镇江、苏州、无锡为重点。江北以海陵、通州为重点。南部被委为海陵地区清乡司令,另拨孙良诚、李长江等皇协军部队听候指挥。同时,皇军情报机关、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工机关,全力协同对付新四军及军统、中统地下情报机构,确保掐断敌方的情报来源。而且,情报战必须先于军事行动展开。
会议散后,已是黄昏时分。
南部襄吉离开会场时,李士群、周繁昌守候在门外,身边停着辆黑色锃亮的福特轿车,盛情邀请。李士群微笑着拉开车门,做出恭候的姿态。南部有点不好意思,料不到他们会这样殷勤,便谦让着颔首致意,跟着繁昌上车而去。车子在苏州城内曲折繁复地街巷穿行了一段后,在观前街一家饭庄前停下了。
饭庄招牌上醒目三个颜体字:晓月楼。
饭庄门口,早已布置好了警戒暗哨。一些便衣的中国人手插在深兜内,明显看出了驳壳枪的痕迹来。
李士群下车后,使个眼色。这些人立刻四散开去,散布入热闹的人群中。
与外面繁华的夜市相对比,饭庄里明显冷清了许多。虽然楼底有两三桌人吃饭,但大多神情拘谨,显然是另有要务。楼上包间内,已然坐了两个日本军官,一个30多岁,一个年近50,都是大佐军衔。李士群忙过来加以介绍,年轻的是晴川大佐,梅机关的得力干将。年长者是宫本大佐,苏州宪兵司令。他们和李士群的关系极为融洽。
南部心中迅速掂量了这两个人的分量,不敢以军阶高一级而有所藐视,连忙寒暄问好致意。李士群笑声不绝,吩咐酒保倒酒上菜。几个人坐下后,李士群举杯先敬宾客,乘机又隆重地向三个日本高级军官介绍了周繁昌,说他不仅仅是汪主席的从龙之臣,还是咱们省府保安处的少将处长,特工总部苏北情报专员。不久,将要去海陵负责协助皇军侦破国共两方的地下情报组织,为清乡圣战作贡献。
繁昌举起杯子,恭敬地向南部致意。南部笑了几声,说:“令弟周繁盛先生,我曾和他有一面之交。他跟我一样,也曾在南去的河道中险遭不测。看来,我与你们海陵周家还是很有缘分的。”
繁昌点头,道:“鄙人也是刚刚知道二弟脱险的消息。我不日将北归海陵,届时,定当尽地主之谊,请将军喝咱们那里的枯陈美酒。”
晴川大佐微笑道:“周先生此次行程,也将同时担负我们梅机关的秘密任务,是具有双重身份的情报专员。还望南部将军多加关照。”
南部连连点头,端起杯子,邀敬座上两位同胞,互相问起家乡来。攀谈之下,彼此原来老家都相距不远,不由喜出望外,遂尽着性子连饮了几杯,李士群和周繁昌望着他们开怀痛饮的模样,笑而不语。这几个日本人虽然好饮,却不善饮,酒量浅显。这十年陈酿的美酒,非掺水的日本清酒可比,下了肚子化作一团烈火,令他们不由自主地失态了,捏着酒杯东倒西歪,放声唱起歌来。
歌声从窗口传到楼下街道上,令行人侧目,心中咒骂不已。
这一场酒,李士群做东,任由南部他们饮乐。酒酣之时,律川大佐又去弄来两个日本艺妓,就着这晓月楼上望月而舞,且舞且唱。三弦乐器幽幽拨动,更撩起他们的思乡之愁,不由撑着肚子更进杯酒,泣不成声,直至半夜方才兴尽,被几个随从搀扶着下楼,塞进汽车后各奔东西。
李士群和周繁昌望着这冬夜苏州旧城上空一弦月牙,不禁叹息一声,说:“寒山寺钟声不起,咱们无从领略江枫渔火对愁眠的意境了。”
繁昌四顾这幽暗的夜色,轻声说:“多谢李部长的成全。兄弟初次涉足情报部门,万事还望多加提携。”
李士群笑道:“咱们是什么关系?我们相见恨晚呢。汪主席对你青睐有加,引为心腹。李某岂能放过你这样的人才?再者,苏北之事,还要仰仗你多加出力。将来,那边的地盘,尽皆交由你统率。我自当倾力相助。”
第三章(7)
繁昌抱拳一揖,郑重道:“不敢有负重托,定然全力而为。”
(五)
海陵城内,虽然平静,但是离城30里却是截然相反的情形。
腊月初八,正是庙里开门放粥救济灾民的时候。远近百姓纷纷赶进城来,去几家大庙讨粥喝。正当城内热闹非凡之际,城南三十里铺,先行轰地一声响,守备小队的碉堡被炸药送上了半空。犹如晴天霹雳,声震四方,连光孝寺前抢粥喝的人群都有所觉,纷纷停手聆听。
不料,这边爆炸声未落,那边枪声又起。城西缪家沟驻防的南部旅团第十二大队突然遭到数量不明的新四军部队的进攻,环镇皆有枪响。临近公路的据点被迫击炮击中,死伤狼藉。仿佛是早有预谋似地,北面沙沟镇方向,突然有新四军一次强攻,排山倒海而来,由于事先没有任何预兆,守卫的皇协军二十七团稀里哗啦立时败退出镇。
只有东面是第七旅团主力屯扎,动静全无。
本田中佐临时衔命出城救应北面沙沟方向,率领一个大队及皇协军一个团兼程赶路。但是,在半途竟然被公路两侧山坡、河谷里不明之敌伏击。他猝不及防,座下战马被打死,覆压在他的身上,一阵剧痛后昏死过去。
待得醒来,本田已躺在海陵城内的康复中。军医告诉他,他的左臂折断了,需要上夹板养息至少两个月。本田着急不已,只肯上夹板却不愿休息。军医无奈,只得遵命替他接对骨位,上了夹板绷带。
本田中佐吊着左臂,以一副伤残形象出席了应急军事会议。替代南部主持军事指挥的是参谋长山本大佐,他焦头烂额地在地图前好一阵子研究,决定将海陵周边驻守的部队派遣到第一线去。同时,东边主力也抽调部分兵力转而向北。南边水道,鉴于上次南部旅团长遇险的教训,特配合口岸海军基地派出小吨位的炮艇沿大河巡航到白马河一带。海陵至白马河河段,则由本部组织巡逻队来回巡查,并在三岔河口加设了一个岗楼据点,配备一个小队驻防,保护这条通江航道畅行无阻。
海陵周家,腊月初八这一天,全数都去了光孝寺吃粥。许怡陪同母亲也过来凑热闹,正好和繁盛等人相遇于后殿斋房厅内。方丈住持捻须而笑,连连唤小僧盛头等的份粥上来,请诸人品尝。就在枪炮起那一刻,大家正开心地吃粥。商议捐钱给穷人加添粥量。被此一惊,不由个个都放下粥碗来,惊骇相顾。老方丈禅修了得,听力非常,侧耳略闻,迟疑道:“四面八方都是枪声,难道是新四军四面攻城不成?”
繁盛笑道:“这可不像。日本人重兵屯集,哪有鸡蛋刻意撞石头的道理。怕是疑兵之计吧?”
繁茂也说绝无可能,肯定是新四军在故布疑阵玩把戏,不知道日本人又要吃什么亏了。许怡犹豫着,说哥哥新近来信,提醒日本人即将要对整个苏、浙两省的新四军动手了,嘱咐千万不要轻易出城,以防卷入战火。
方丈念声阿弥陀佛,叹口气说:“生灵涂炭,老衲不忍卒见。这光孝禅寺,怕又要涌入许多乡下避难的无辜良民了。”
周太太适当此时,却无众人之忧,合十在胸,暗暗祈祷道:“佛祖在上,千万别让繁昌回来。海陵已是一片是非之地,令人望而却步也是件好事。”
腊月初八这天的意外变局,令繁茂每天到处游荡、无所事事的日子结束了。原本驻扎在县立中学的日本部队,奉命出城,前往周边乡镇敏感地带驻守。学校内,帐篷尽拆,遗留下一地的屎尿,狼藉不堪。校长发出紧急通知,让家住在城内的教员和学生赶来学校,参加打扫,清除污垢后准备复课开学。
接到通知后,繁茂心情不错。次日起了一个大早,他去厨房内先寻了两碗热粥下肚子,然后便行色匆匆地往外走。不料途经前宅时,正好碰上大嫂玉茹。玉茹看情形是夜里睡眠不好,眼窝里隐隐泛青,有点儿疲惫无奈的样子朝大门走去,似乎也要上街出门。
第三章(8)
繁茂见了她的背影在前,本想避让。
可是,玉茹听到了他的脚步声来,头也不回,说:“你也起这么早,想去街上看热闹吗?”
繁茂见她停步,似乎在等自己,只得上前。
这叔嫂俩自从上次闹酒醉后,还没有真正地谈上一次话。此刻清早面对,各怀心思。有懊恼有沮丧,也有回味和尴尬。玉茹望着繁茂那张年轻俊秀的脸庞,强笑道:“富春的三丁包子、蒸笼虾饺、水晶油糕都不错,咱们先买先吃,汤汁浓抖抖爽口,鲜美无比。怎么样?”
繁茂摇摇头,说:“我要赶去学校,日本人离开了,操场、教室都要清理,好复课开学了。”
“哦。”玉茹略显失望地说:“你是要忙于生计了,我可不便拦你。走吧,咱们至少还能同一段路。”
(六)
繁茂和玉茹在1941年末冬季的某个早晨,踏着薄薄的轻霜出了宅门,沿着麻石铺就的小街慢慢走着。街头行人稀少,寒鸦高踞枝头,哀鸣声声。浅淡的一丝阳光横掠过枯萎的树丛,留下了一道宛若刀痕的印记。这衰败的冬景,令这对行走于其内的男女心头郁闷,无话可说。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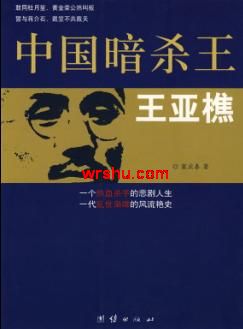
![[张卓] 暗杀封面](http://www.xntxt2.com/cover/noimg.jpg)

![(暗杀教室同人)[暗杀教室]论玩坏完全防御模式杀老师的各种方法封面](http://www.xntxt2.com/cover/85/8502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