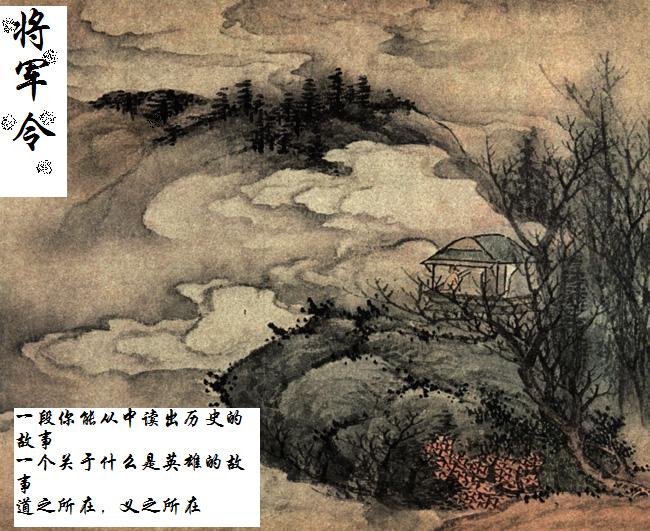尚书令-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气得聂玉棠整整
三个月没和李朝钺说话。
那这口气最后是怎么消得?
具体还要回到那一年的七月半,聂玉棠让秦水香穿好了戏服,上好了妆,手里提着一摞纸钱,骑马带着他做环城一日游,边唱边撒。
唱什么?
——《窦娥冤》
撒什么?
——撒纸钱。
一路从城内向城外,直到郊外的坟地,半空中飘着的都是白花花的纸钱。最后停在了蔡晓楼的墓碑前洒了一杯清酒,道:“老天知道你冤枉。”
至此,朝廷里的人算是彻底领教了他的疯,疯起来就连天皇老子的面子也不给。
郭孝如为此屡屡上折子说尚书令弄权,聂玉棠听后冷笑道:“废话!权?我只要一天还在这位子上,我手中只要一天还有权,就是要玩儿给别人看的。”
细细想来,这两人交恶,大抵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虽说如今时过境迁,这桩事已没多少人能记得,但秦水香记得,他捂着心口的位置对云逸之道:“大人为我做的这些,点点滴滴,我都记在心头。我是一个伶人,说的话没多少人会信,可就算全天下人都说聂大人的不是,将他说的多糟糕都好,他都是我的救命恩人。”
云逸之点点头,抬眼看秦水香,发现他眼角湿漉漉的,显然还在为蔡晓楼伤心,云逸之有点内疚,自己方才对他态度不算好,这会儿就呆呆的拈起袖子替秦水香擦了擦眼泪。
秦水香破涕为笑,说道:“我们伶人不过是个玩物,只有大人将我当作人,所以我常来府上陪着大人,其他的…水香没奢求过什么。”至于坐聂玉棠腿上那个吻,秦水香解释道:“云大人您也晓得,聂大人性子淘,就爱捉弄别人。”
云逸之想到聂玉棠专门在屋顶上挖了洞还铺一层稻草引诱他掉入陷阱,便叹了口气道:“是啊,贼坏的。”
秦水香笑着说:“我与大人识得多年了,他的性子呀,就和他的字一样,看着觉得眼花缭乱的,其实表里不一,真性情是鲜少在人前流露的。不过我看的出,他很着紧云大人。”
云逸之摸了摸鼻子,心道,那人确实坏,又贼又坏,可正因为这样,就如同怒放的海棠,红的热烈,红的鲜艳,不似桃花欲语还休的轻佻,反而显得不做作,坏的可爱。
聂玉棠不知是何原因,这时候总算提着药箱姗姗来
迟,秦水香赶忙接过替云逸之上药,聂玉棠就负责在一边教育偷窥的云大人,俯□,两手撑着膝盖,直勾勾的盯着云逸之道:“以后要过来记得走正门,要不然爬墙也行,别再当什么梁上君子了,老爷我经不住吓,可记住了?”
云逸之可怜巴巴的点了点头。
聂玉棠再没说什么,自顾自喝酒,等云逸之的腿被秦水香包的像一只火腿,才道:“我让小饭团送你回去。”
云逸之低低‘哦’了一声。
突然聂玉棠眯起了眼,一手摸着下巴一边绕着云逸之走了一圈,不知琢磨着什么,神秘兮兮的。而后老规矩伸手点了点云逸之的鼻子问道:“云小哥,我没记错的话,再几日你是不是就要过生辰了?”
云逸之抓了抓脑袋,想了片刻,点头道:“嗯。”
“嘻。”聂玉棠咧嘴一笑,单手勾住秦水香的肩膀。“反正我们闲来无事,就替你做寿吧!”
“啊?”云逸之望着他。
“嗯。”聂玉棠眨巴眨巴眼睛,十分肯定的点头。
“哦!”云逸之坦然地接受了这个安排,“好,既然如此,那下官先谢过大人了。”说完,对聂玉棠一揖,转身走了。
清风朗朗,明月高悬,秦水香指着云逸之离去的背影对聂玉棠说:“大人,我可能高估了他的伤势,你瞧他走的多轻快,一蹦一跳的。”
“有吗?”聂玉棠抬头望天,装傻。
“有啊,他看上去似乎心情很好。”
“不觉的。”聂玉棠道。
秦水香啧啧摇头:“造孽啊造孽,大人,你的风流债又多了一笔。”
“啊呀小香…”聂玉棠打断他,“安平郡王这回瞧上了我一个朋友…”
“咦?真的么?”秦水香果然是个好糊弄的。
“真啊,不过那大个子武功了得,郡王要是敢摸一下,保准上演一出《武松打虎》,哎呀呀,锵锵锵锵…”聂玉棠边说边玩起来,就差在屋里翻两个跟斗。
秦水香咯咯直笑,笑完了正色道:“大人,你的心情好像也很好…”
“……”
作者有话要说:尚书令当的好憋屈。。。这会儿各位大概能琢磨出云逸之让小聂题字的真正用意了,嘻嘻。
☆、玉棠记(上)
五月初九,云逸之寿辰,府中唱堂会。
京华城里的人四处奔走相告。轰动一时。
百官几乎是用上朝的架势如流水一般涌向云府,而李朝钺也带着贴身的两个小太监偷偷出了宫门,亲自来替他贺寿。
单单是礼物,就收了足足有两大间厢房那么多。而坊间听闻云府做寿,挑大梁的竟然还是秦水香,就令整件事看起来愈加扑朔迷离,内幕重重。只因秦水香有规矩,绝不出去唱堂会,却专门为云逸之破了先例。外人对于他们之间关系的揣测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直接导致了不管是真戏迷还是伪戏迷,通通都趴在云府的墙角,骑在云府的墙头上,要一睹绝世名伶的风采。为此,管家提着扫帚都不知赶了多少回…
云逸之本人的心情却不像旁人那样兴奋,反而倒像是避暑山庄蜿蜒的龙墙,起起伏伏。开始聂玉棠说要替他操办生日宴时,他确实乐了好些天,可谁知操办的过程里头由头至尾就没有瞧见聂玉棠的人影,连一绺头发都未见着,不免叫人怀疑其真实性和可靠性。而到宴席开始,李朝钺都入座了,还是独缺一个聂玉棠,云逸之这才算是领教了聂玉棠空口说白话的本领,心情顿时跌到谷底,面上也是难掩失落,一边默默腹诽着,说要替自己庆贺的人是他,缺席的人也是他,真是没心没肺,吊儿郎当!
他没有留意一件事儿,那就是,如果聂玉棠没有插手的话,他府中那么多丫鬟家丁到底哪儿来的?虽说云府是国师宅邸,但手下人都是李朝钺赐予的标配,云逸之活的懵懂,向来是无法分辨的,这其中的斤两只有聂玉棠这样的大俗人才能拿捏的出来。所以刚才那番自说自话若是叫尚书令听见了,必定点着云逸之的鼻子问:“嗯?说我没心没肺,你倒是自己说说,没心没肺的人其实是哪个?”这些个帮忙的家丁丫鬟那可都是聂府外借的啊!
当夜、色、降临,京华城笼罩在一片暗暗的暖火色里。有花,静悄悄的开。有风,轻凉凉的吹。什么都是缓慢的,内秀的。人声鼎沸的喧嚣散去后,云府那些推杯换盏间说的场面话,也都是悦耳的,舒心的,只是纠集在一块儿,熙熙攘攘,竟也汇成了一条河,在夜幕里分外有些被群山环绕的孤立之势,处处留着回声。这回声,是河水表面下的暗流汹涌,这回声,是群山之间漆黑的沟壑,深不见底,暗藏机锋。好在台上唱的文戏,是久不见的鹭鸶小调,从前上不了台面,此刻用来暖场,提上台咿咿呀呀哼唱两句,倒是分外亲切,也就冲淡了那些暗的,黑的,张扬的,尖锐的,只余下一些纯粹的饮酒作乐的心,暂时将那些九曲十八弯的垢腻心思收敛起来,留待明天
。这就是官场,一边乐着,一边算着,一边恣意放荡,一边又谨慎瑟缩,每个人都是好人,每个人也都能是坏人,大部分时候虚张声势撑得饱满,偶尔也会冒出一根刺来谨防被别人暗算。其实什么人什么事都是分两边,最后不过是一边战胜另一边。
聂玉棠就是这样一个又俗又雅的人。正是俗的透了,才能想得出各种奇招对付这些朝堂上的大老爷,鲍参翅肚,酒肉海鲜,上菜的顺序也都是他算计好的,趁着嘴被塞住了,才讲不出多余的废话八卦。饕足享受之后,更有糖果糕点见缝插针,一嘴的甜,说的也只能是好话。除此之外,丝竹配乐也是一俗,琵琶胡琴,花鼓唢呐,全然没有钟磬的大气端庄,可也生生的将裹着黄沙泥土的黑河水搅成了涓涓白溪水,全然瞧不出任何威胁危险。这等手段,这份心思,是既浑浊又分明,俗气之中透着诙谐狡黠,是属于聂玉棠独一无二的风雅韵致。云逸之要是再看不出门道来,那就是傻。他对着鲍参翅肚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晓得得花多少钱,而后眼角余光一瞄,逮住了小饭团,令他过来问话,盘算着要将银子还给聂玉棠。小饭团说:“我家老爷这个人,顶顶俗了。愿意在谁身上花钱,就是对人家真的好,所以云大人你要是计较着这些,我家老爷可是要生气的。”云逸之听后,浅笑不语,淡然受之。他想,这份心思,须妥帖收着。
大戏开锣的时候,群臣正是酒足饭饱,品着茶百家争鸣。话在兴头,乐在兴头,算是一个小波浪将要去到顶点,还未至顶点的时候。
有一点风,来无影去无踪。有一个人,踩着碎步,摇曳生花的上台来。还未闻其声,未窥其真容,就已觉得这是一个活脱脱的女人,比女人还女人。台下听戏的经意或者不经意那么一瞥,想,啊!这就是秦水香,举手投足,千娇百媚。果然名不虚传。跟着擦亮了眼睛满心期待。可台上的花旦不知卖的什么关子,袖子掩着脸,手上结着花儿,走走停停,犹抱琵琶半遮面。
舞台是依着一颗大榕树而建,虬枝盘桓在头顶,轻风路过,带起旁边不知名的野花,徐徐漂浮在半空。那花旦舒展了袖子,露出玉一般的手,张罗了一朵在掌心,随后腕节一转,两手交叠,右手趁势拈起了那朵花,换成左手来挡住脸面,整个动作一气呵成,滴水不漏,就是不肯叫人瞧见他的真面目,却开口唱了一句:“哎呀,那个卖花的怎么还没来呐?!”
当是时喝酒的觉得花香酒醇,喝汤的觉得汤鲜味正,喝茶的觉得馥郁回甘,却没有一种味道,叫做清,于是这一把嗓子音起的高,字正腔圆,霎那间令这些复杂的味道通通破了功,顿觉淡而
无味。唯有赞叹这把天籁之音,自九天银河而下,直捣凡世,教化众人。而所谓广寒清歌,嫦娥舞袖,应当如是光景。
一个个摆下酒盅,茶杯,鼓掌不断,齐声喝彩道:“好!”
而后一个大汉套上髯口,提着大刀,蹭蹭蹭从侧边踏到舞台上来,中气十足道:“小姐,你等的可是俺吗?!”
“扑哧——!”一群人笑开了。
秦观首当其冲,起哄道:“哎,程铁峰,别以为你把脸画花了,大伙儿就不认得你啦!”
程铁峰憨厚的笑笑,尤其是向着云逸之露出八颗雪白的大牙齿,顺便再从屁股后头捞出一根毛茸茸的狼尾巴,冲台下众人挥了挥,把所有人逗得眼泪都快笑出来了,这才回过头去继续调戏捂脸害羞的小花旦。
“小姐,你等的可是吾,我,俺么?”他一边重复,一边将海棠花递过去。
小花旦退了一步又一步,退无可退便打了个圆,幸运的从程铁峰的魔爪之下逃走,叫这色狼扑了个空,随后气急败坏,穷追不舍,期间小花旦一边逃一边还舞一舞袖子,风姿绰约胜过烟柳,欲拒还羞勾引煞人。把台下众人熬到伸长了脖子,一个个抓耳挠腮,痒的不行。——喂,你倒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