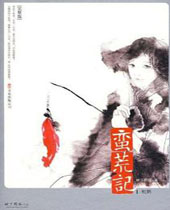未止记-第1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笑来,问道:“莫不是真成了肺痨么?”太医反倒愣住了,匆匆地把目光扭到一边,重新坐到药碾子后面去,说:“你这人倒有意思,好像早盼着了似的。”文顺叹了口气,道:“我师傅也略懂一点岐黄,早些年教过我几句,再者说,这么成年累月的咳下来,再怎么笨的心里也有数了。”
这时候中午已经过了,太监们都被支配去陵寝擦扫,到处都冷冷清清的没人,文顺在路上磨蹭了一会儿,才慢吞吞地往回走。远远看见自己住的院子,倏地转回身,随便找了个岔路往别处去了。稀薄的阳光从他身后扑过来,石土地上歪斜着拉出一条扭曲了的长影子,尽头被一棵粗柳树截断了。他深深地吸了口气,肺叶里立刻充满了冰凉的尘土的味道,撩得喉咙发痒,再吐出来的时候,那树根旁边便氤氲出一团浅浅的灰烟来。再不出两个月就该下雪了。文顺直着眼睛,怔怔地只顾往一个地方盯,却不知道在看什么,也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滋味,大概总有些凄凉和悲哀。真是得意的越发得意,落魄的就更加落魄,他现在得了这样治不好的病,恐怕也剩不下多少时候,可别人却正准备着生儿育女,日子要圆满起来了。他又忽然恨极了自己当初为什么非要吃这口饭不可。除了这么一副残缺不全的身子,到底还有什么是他的?
郑太监知道了这样的事情,非常气恼,忙不迭地打发文顺去了最偏僻的屋子。北院靠山最近,所以一直空着,只有两三间里堆了些平时用不到的器具摆设,直到文顺搬了进去,才算有了点人气。因为离着别人都远,大家也就渐渐想不起他来了。汤药是自己搭小炉灶煎着,饭食没法烧,难免三天两头吃了上顿没下顿。小倪子倒很殷勤,一天三次地送了来,过了一个来月,也不太露面了。文顺最怕他的病过给小倪子,不过似乎痨病也不
是全都会过给人的,小倪子不来,他反倒比人家来的时候还安心些。
因着长久抱病和养息不周的缘故,文顺很快地消瘦了下去。他本来身体就不甚结实,只是凭着习武的底子,才看上去稍微有些棱角。但是病了一段日子,就不能每天碰剑了,有时候练小半个时辰,回头就得躺一整天才缓得过来,慢慢地就连一炷香的时候都撑不住了。文顺十分担忧,另一方面又替自己叹息,没想到才这个年纪,却已然不中用,像个废人了。
有一阵他精神稍微好了些,可以经常下床走动,便常常到他以前住的院子里去。他多半是坐在院门口,离别人远远的,不说话,光是看着,听别人说最近米和菜又贵了,一吊铜钱过去能买一车的土豆,现在只能买半车。他们只有那一辆板车,以前拉过死人,后来去采买衣食的时候还是用它。偶尔也有人多告几天假,跑到西京去,回来就成了大家注目的中心。他们吃完了饭,往往在台阶上围成一圈坐着,哪怕天气是那么冷。大家都想知道,他们过着死灰槁木一般的人生,那外面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
有一天小倪子从西京回来,说皇上要去近郊的天禅寺进香。大家都觉得奇怪。永承登基这四年多,从没有过烧香拜佛的举动,更不要说特地跑到哪个寺里去。后来才打听明白,是因为惠妃的产期临近了,怕第一胎生得不稳,才热心地求神拜佛起来。惠妃虽然不太信这个,此番也颇当成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挺着肚子也要去拜的。日子就定在正月初八。
算起来这时候文顺已经被赶出宫一年了。他实在是不甘心就这么静悄悄地等死。最近他的病突然沉重起来,总是睡着的时候多,醒的时候少,但其实也并不算是真的睡,只是昏昏沉沉地阖着眼睛不愿意见光罢了。在昏迷中他总想起过去的事,心里总是有那么个声音,像是劝说似的令他相信,尽管永承只把他看作个可有可无的玩物,但他对永承是一直死心塌地地想念着的,这是一种毫无来由、也根本没有道理的、霸道的执着。等到清醒过来,想见永承的愿望就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强烈。
除夕夜他也是躺在床上过的。一向没人肯上他这儿,黎大奶奶却忽然来看他,还提了几样酒菜。文顺打算爬起来给她道个万福,被她按住了。文顺笑道:“您这一遭儿来的缘由我可猜着了。咱们都是平常不招人待见的,所以这种时候才爱往一起凑呢。”黎大奶奶愣住了,呆着脸瞧了他几眼,才跟着笑起来:“了不得,这话比刀片还利害。原是我不识趣,非要往不待见
我的地方凑。”文顺连忙跟她赔罪,把几碟卤牛肉、花生之类的东西在桌上摆开了。他们面对面坐着,先是没人说话,只各自闷头喝酒,过了半天,文顺伸着筷子去搛一粒花生,黎大奶奶正巧也用两只手指去拈,两人都停在半空里,一齐笑了,才慢慢地聊起来。黎大奶奶问到他家里的事,文顺一句也答不出,只含含糊糊地推说不记得了,见他脸上神情尴尬,便不再追问,又说了许多宽慰的话。文顺和她并没什么往来,有时她难得出来走动,也不过是点个头而已,现在忽地交浅言深,虽说有些仓促,心里到底是暖和的。酒壶不多时就见了底,黎大奶奶面颊上飞起两片红晕,看人时一双眼睛也眯得有两分妩媚。文顺静默着低下头,忽然想如果当年没有进宫,而是在外头找个活计撑下去,到今天也差不多能熬出头,过上这样的日子了,虽不见得发达,也能攒下几吊闲钱,说不定也会有个女人愿意在半夜里陪着他。说不定……这都是说不定的事,谁知道呢。
他决定回西京一次。因为初八就快到了,所以没时间让他犹豫。文顺算着日子,故意提早了两天走,虽说不会有人想到这一层,他还是不想让人知道,他是因为要去看銮驾才回京的。
他走的还是前年来的官道,沿途讨饭的越来越多,当中混着不少正当壮年的汉子,一个个面有菜色,身上的布袄灰扑扑的,袖口露出脏污的棉花来。离都城还有十几里路的时候忽然都不见了,沿途在赶工装饰帷帐,又有一些官兵稀稀散散地在附近巡视。看见那明黄色的绸布,他的心口忍不住倏地抽搐了一下。在路上的时候还不觉得,这样的颜色一跃而来,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是离永承越来越近了。
进城已经过了晚饭时候,文顺在城东一家客栈住下。路上多耽搁了一日,这天已经是初七了,他本来打算早点歇下,怕连续几天的折腾引得病更重起来,但躺了半天丝毫困意也没有。这屋子墙壁很薄,隔壁那间住的是对刚上京的夫妻,半夜里嘁嘁呿呿不停地说私房话,偶然有一句半句顺着风飘过来,撩起人的好奇来,仔细听时,声音却又低下去了。文顺叹了口气,重新起来点了蜡烛,把一整幅棉被都裹在身上,又将窗户推开了条缝,踢了个椅子过来,倚窗框坐着。他往外头怔怔地瞧了一会,忽然摇着头气咻咻地笑起来。说来实在是让人脸红,就因为能远远地看那么一眼,他竟会睡不着了。过了些时候,窗外渐渐鸦雀无声,街上远远地传来敲更鼓的声音,咚咚两声,顿了一顿又是咚咚两声,也许是因为天冷,那木槌击着竹板的声响都硬梆梆的
,带着一股刺人的凉意。巷子里忽然窸窸簌簌地有了人声,文顺往前倾了倾,瞧见窗下两个人影子跌跌撞撞地跑开了,借着红灯笼幌子的光,看身形像是两个孩子,一个肩上背着包袱,另一个边跑边往怀里揣东西。两个孩子跑远了,转角那边却忽然喧闹起来,听见高一声低一声的叫骂,又有男人叫嚷,说大过年的连贼也不消停。文顺把双腿蜷到椅子上,棉被又裹紧了些。这事情和他无关,但他心里总是隐隐约约地不踏实。年景是一年比一年差了,连西京尚且是这样,永承治下的土地便是这样,偷的尽管去偷,偷不着的就要饿死,可真要摆出来给上头看了,一切又都是盛世太平。
第二天一大早,出城的路就全被帷帐隔下了。两侧的摊贩是早两天就被驱散了不准再出来的,每隔两步就站着一个守卫,面无表情地在人脸上逡巡。凑热闹的挤在跸道两旁,想往前冲,又忌惮着侍卫腰里的长刀,人群便忽前忽后地晃,仿佛是一齐晕了船。文顺茫无目的地被人夹在当中,离那明黄的帷帐还有六七步的距离,忽然街尽头躁动起来,人群受了指令似的一齐伸长了脖子,生怕错过什么。大家都以为是銮驾来了,但前头只是先来了几队侍卫,铠甲下面都穿着大红的锦袍,手搭在剑柄上,趾高气扬地炫耀着走过去了。后头却再没见着什么人,人群里又失望地窃窃私语起来。
过了一炷香时候,忽然有两排宫人挑着宫灯和提炉,沿着帷帐边悄无声息地走近前,那身上的赭红服色文顺再熟悉不过,心口突然被揪紧了似的,扑通扑通狂跳。那队太监要走到他面前的时候,文顺下意识地低下头,捂着嘴咳嗽了两声。其实并不会有人认出他,但他还是止不住地紧张。这一队走过去,銮仪便慢慢地开始上来了,黄幢和大红旗子层层叠叠地遮住了天,身后忽然潮水似的往前拥,不知是谁发了号令,街角的人群忽然跪了下去,旁边的人也就跟着往下跪,四周黑压压地矮了一片。文顺茫然地屈□子,膝盖碰到地面的那一瞬,他忽然有种奇异的触感。耳旁开始有错杂不齐的声音高呼万岁,喊得都是些戏文里看来的、乱七八糟的吉祥话,听着好笑,却令他莫名其妙地觉得悲哀。他抬起头,沿街的楼上悬着各种颜色的木板和招牌,香烛铺,麻油铺,绸缎坊,卖香粉的,沈同德堂,鲁菜馆……密密麻麻的全都是人,不做生意,每个人都因为銮驾而自个儿砍了自个儿一截。
有个武官气喘吁吁地顺着幔帐跑过来,嘴里喝斥道:“低头!都把头低下!”文顺突然直挺起脖颈——他看见了那抬宽大的轿子,看见
了摇摇晃晃的黄穗儿,永承就在他面前了……他和他之间只隔着一层布。銮驾越来越近,先是明黄的御辇,紧随其后跟着惠妃的仪仗。他忽然什么都不怕了,他直起上身,怔怔地盯着那抬轿子,他原本很恐慌,怕永承会突然从那张轿帘后面露出脸来,然而现在他确信地知道,这件事永远也不会发生,居高临下的皇上绝不可能对这些褴褛的子民发生任何兴趣。早在他无数次像今天一样,作为一个卑微的个体,畏缩着跪在永承面前的时候,他就应该明白,他们之间横亘着如此不可能被逾越的深壑,早就不该幻想了。今天是永承为惠妃、惠妃的孩子,同时也是永承的孩子祈福的盛大的表演,而自己只是成千上万渺小的共演者之中的一员。文顺站起身,从人群中一步步退了出去。那浩荡车马和华衣美服沿着街离他越来越远,他第一次感到这样巨大的无助和迷惘。眼前只剩了狂欢的人潮,推、抢、搡,争先恐后地追着銮驾走,追着旁边的人走。他眼睛里有无数张脸,它们是好奇的,惊喜的,感激的,老泪纵横的……那些脸忽然又都变成了一个样,好像只是一张脸被复制了成千上万遍,在那张脸上,尽管从没能因为生活富庶而出现过满足的笑容,却因为远远地瞻仰了一次帝王而露出疯狂的喜悦,仿佛蒙受了巨大的恩赐。永承的轿子上有根线,和他心里的什么东西拴在一起,车轮吱呀吱呀地碾着石头地,一圈,再一圈,那线就愈发紧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