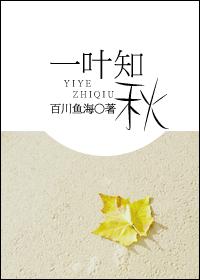һҶ��Ŀ-��2��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ý����������ô���Ľ�ס��¶�������˵�ģ����
�����ڱ�������һ�ۣ���ͷһ�������ұ�¶���ֺ������飬��͢���£���������ֺ��������ó���Щ����ʱ�ܺ��Լ����Ҳ�Dz����ģ�һ�������˵����鶼������ɱ����
�����ڱ����Ѻ������ֿ��˿����˵���ɫ����ͷ���棺�����£������Ŀ�������֮��Χ�ƣ������־���է��է�ȣ�����һʱ���ܲ�ס���ŷ�����������
����һ����է��է�ȣ��ʵ���������ѩ������ݣ���������ԡ�Ĺ�ϵ�������ֲ�м�����˵����壬��ô��ô����ȴ��֪�뜏�Ѿ���ѩ������˺ü���ʱ���ˡ�
��������Ҫ��ò��ܺã������ոյ��ֵģ����ʾ�����û����ô��������һ�����ʵ۵Ŀ������Ǻܺá�
�����ڱ������ŵ��������»�ֻ�Ƿ��գ��ȸ������ˣ����ܻ��Ƿ纮������������Ҫ����µ�ʱ�䡣��
������ô�ã��ʵ�������üͷ����������
�����ڱ����о����ʵ۵��������Ǻܺã����ʱ��˵���������鷳�����Ǵ˿�ƫƫ���ֲ��ò����ڣ�վ��Ϊ���忼�ǵĽǶȣ����ҽ�ߵ�����������£��뽫�����������Է����������̸����¡���
�����ʵۿ��˿�������ͷ��
��������һ�п�ʼ����ؽ��У���̫�ཫ�뜏�Ӵ���̧�ߵ�ʱ���뜏�����Ժ������ţ��ֽ����Ķ��˶���������һЩ���죬�ʵ�̧ͷƳ����һ�ۣ�ֻ�����������Ϻ��һ���ġ�
����������֮���ǰ������������ū���ź����ЪϢ�ɡ���
������ʱ��ɫ�Ѿ���Щ�����ˣ��ʵ۾����Լ�˯�߹��ˣ�Ҳ����Ъ�ˣ������������ˣ������ϻ�û����������ù�������
�����ܶ���ʵۻ����������뜏�ĵ�һҹ����ҹ�������ڵ�����˯�������պ�ĺܶ��ҹһ�����������о��ѣ�����˯���·��ǵ�һҹ�ͱ�������һ�㣬���ܵ�һҹ�ʵ�ֻ�ǵ����ز���˯���˶��ѣ����պ�İ�ҹ��������˼����ĥ������ͬ�����Ǵ�ij��Դͷ��������������Ϊ�뜏����ˡ�ټ����������ı������������ɼ����¶�����ҹ����������ֻ��һ����һ�ݱ�������ۡ���ʱ���ͻ����������뜏�ĵ�һҹ�����Ľ�Ӳ�����ķ����Լ�����������顣
����
���������
�����뜏�����Լ�ʱ�����ѵúܣ�����ϸ������������һ�������ֻ�Dz��ܶ���ʱ���ַ��룬�·����кڶ������������µ�������һ�����ű�ˮ����һ��������ˮ�Ϲ���
������������������ʱ����һ�����ϡ���֪�Ǽ�������ֻ�����Լ�����ָ���Զ��ˣ�����ĸо�Ҳ���������ˡ�ֻ������������ģ��Ų�������ֻ�ü������š�
�������紵�Ŵ�������žž��������һ�����һ��
�����뜏��һ���۾�����һ���۾���������������֪��������ʲô���ڰ�����ǹ���һ��������Ц�⡣
����������Ĺ���һ��һ���������ͬ�뜏����ɫ���Ұ�ȴ����һ����ϲ��ζ����
����
����С��һ�ߴ��ź�Ƿ��һ�����ŷ����������ߡ��Դӷ��ܹܱ��������������չ���������Ѿ������ˡ���̫ҽ˵�Ѿ��������յ�ʱ������Ӧ�û����ˡ�����ʲôʱ��������أ�С�Ӳ�֪���뜏�IJ�����ѩ���������ģ�ֻ�������ﷸ���ֹ���������Ȼ����֮����ʱ�������ƣ�����һ���Ӱ����˳�����Ҳ����ġ�С�Ӳ���ͷ���۾����һ��Ժ�ӣ�����Ժ���е㲻�ԣ����һ�ۣ�Ժ����һ�㱡����ѩ����������ҹ���µģ����⸲��ѩ�ϣ����������ϵı�֦�������ѩ������С�����������������ѩ����ͣ�ˡ���
����
����С�ӽ��˷��䣬�ߵ����߿��˿������ϵĹ����Ѿ����ˣ��ڳ������۾�����������������һ˫�۾�һ��С�����һ㶲ŷ�ӳ�����������ӣ�����������
�����뜏��������ͣ���������������
����С��һ���������ӣ�������������̫��û��˵���ˣ�ɤ���Ų���������ͷ�ӷ�����ȡ������ͼ�����ˣ��˵����ߣ�һ��һ�ڵ�ι�����ԡ�
�����������࣬���ź��ź���ҩ��
����С����ʰ�����ϵĶ������������ţ�������̫ҽ���Ǹ���ͻ���һ�˵ģ���Ȼ�����Ѿ����ˣ��Dz���Ӧ������̫ҽ�ٹ���һ�ˡ��Լ�ȥ�еĻ������Ӹ���˭���չ��أ�
���������ţ�ֻ�������ϵĹ��ӷ�����һ��������
����æ��ͷ�ߵ������ʵ�����������ʲô�Ը�����
����������ʲôʱ������������ϵ��˶�����ͷ����ڵ�ͷ��������ǰ��ֻ������һ����Ӱ��
������������С������һ�£����������ܱ��¶��������ɻ�Ķ���ʧ�裬С���Ŵ�ʣ����ȹ��������Щ�ˣ����¾ͻ����ˡ���˵�꣬�������˿������ƺ������Լ�������ɲ�����
�������ϵ�������һ�ᣬ���ڵ������Ǵ���ȥ�����¡���
����С�ӷ·�����ϡ��ļ���һ�㣬����һ�����ŵ��������ӣ�ֻ������ű����ټ����㲻��ȥ�����¡���
�������ӻ���δ�ţ����Ŵ���վ�����������˴�������ֻ���˼����¾�Ҫ�����ߡ�
����С�Ӽ��ˣ����ŵ���������Ҫȥ������Ӷ���û�к������ء���
����������ȥ�����¡���
���������ӣ��ⲻ�Ϲ���Ĺ�أ���ȥ�ˣ���Щ����Ҳ���������ȥ�ġ����ҽ���˷�գ�����Ҫ�ϳ�����Ҳ�����ŵġ���
����С�ӿ�������ͣ���ſڣ��������ϵ���Ҳ����������������̽�ŵ�����Ҫ��ū������ȥ�����ܹ�˵һ�����������ˣ��������ܹܵ���˼����
�����뜏�ֿ���С��һ�ۣ�С�����←��һ����ֻ������˫�۾������˻���һ�㡣
���������ʲô���֣���
������ū��С�ӡ���
������������ͨ������
�����뜏���������˴��ߣ����Ŵ��أ������۾���
����С�Ӷ��Ŷ�������ǰ���ֿ��˿�����������Ӱ�����������־����������������ѩһ�㣬���˾�����ô��ů�Ͳ�������
����
��������ʱ��С�������ڱ������ˡ��뜏�����ڴ���˯�����ڱ�������һ���������������뜏�����ˡ������ڱ��������۾�������֮�ſ��ڵ�������̫ҽ����
�����ڱ��������뿪�����������������빫�����ˡ����뜏���������̥�������ʹ��Ż�������ʱ�뽫��������ĸ�ӻ�����һЩ���Σ�͵͵�����ڱ������뜏�����������
�����ڱ���д���˷��ӣ�����С�ӣ��Ը���ȥץҩ��
�������빫�ӣ�����ô�ᡭ�������˿ڣ��־������Σ�˵����ô���������ӵ�������
�����뜏��Ĭ�����ţ��ڱ����ǵ�Сʱ������������ҩ��ҩ����������һζ��������ȴ���Ƕ�������˵��̫ҽ��ҩ����һ˿�������Ǻúȡ�
�������������ӣ���������Ļ�������������ġ�ҡҡͷ���ڱ���ת�������š�
��������̫ҽ������
�����ڱ�����ͷ������
�����뜏�Ѿ��Ӵ����������������ӻ��£�¶��������ɫ�ĺ��£��۲����������ڱ�������������������
����
����С��ů�����ຮ��С����������
����С��һů�����꿪������һ������������ʱ���������磬�ճɾ�ָ�����ϡ�
����С����������ů����������͢�ʹ��������о����գ����ּ��ģ�è�ڼ���������ţ��ܱ�����Ҫ����ǿ�����Ҵ������������������Ϊʳ��������ճ�Ҳ�������������ӡ���ʹһЩ����ƶ�ĵط���Ҳ���������ع�Աʩ�����ࡣ
��������С��������ͷ��Ҳ����һЩ�ʵ۱��²�����������������
����
�������ھ��Ǹտ�ʼ�µ�һ��ѩ��ʱ�����ߵ�Ȯ�־ͷ�������ȵ����ġ�Ȯ�ֲ��Ǵ�µ������������壬���ȵ���λʱ�����ġ��������ϱ��Ƴ��������мӣ��깱���Dz��ϣ�����������˲���ϡ��ĺö���������
����˷���糯����������˼�����ࡣȮ����ѩ�ֶ�ʱ������������������������������ۼ����������Թ�����������أ���ʤ������Ȯ�����뺷������ҳ��Ƴ���������Ϊ��֮ʱ������ҳ����ѣ�������Ȯ�ֽ������ػ�ӱ��ݿ�ʼ��
�����ʵ���ʮ�������鴮켣�����һ�۱�������˼�ޡ�
����������ۣ���ɫ��ñ����������һ·ð�ŷ�ѩ���ӱ��ݷ糾���͵ظϵ����ǣ�·��������3ƥ������Ҳ���ǰ������Ӱɡ�ֻ����һ��������һ�����������鿴����Ȥ��
����������˼�����һ�����������ʥ��֮�ʵ�������ɤ�ӣ��������ڰ�����ô���Ӧ����Σ���
����������Ʒ���۵������������������������е���������Ϊ����ʩ��Ԯ�֣����ó˴˻��ᡭ����
����һ�������ֲ�ʧ���ҵı�����ټ������������ݡ�
����
�����ʵ����ڸ�λ��������Զ��û���˿������������飬��ʹ�ܹ����壬�ߵ�֮�ϣ�����˭��������Ӹ�̧ͷ����ʥ�գ��Ա��´��أ����Դ˿̰������������飬��Ȼ��û���˻��������ϵ��һ��
�����ʵ۰����Ŵ��̵İ�ָ��������Ȯ��������������Ѿƣ��Dz������٣����˿˿�ۿۣ�����ý��ء�
����������ʱ�����ˡ��ʵ����������������������ˡ���
�������µ������Ȼ��ֹ��Ȼ����ͳһ������������������ʥ�á���
����ֻ�д˿̲Ż��ѵõ�ͳһ���ʵ۹�����ǵ������ҳ�����Т�����£�Ȯ����Ϊ�⳼����˳���꣬�����мӣ��˴����ѣ������θ�����������εΪ��ʹ������ʳ��ʮ�պ����̡����������Ǽ�λ�佫����һ�������������λ��ҷ��ģ��պ���Ȼ��������������ʱ��
�������˿��ſڹ��ŵı��������������������������ӣ�ǧ���౾�����ĿɼΣ��ʹ�������2ƥ���������̣������Ĵ���Ȯ��������
������������˼���佫���������������ϲ�ع���л����
�����ʵۿ��˿��ǿ��ŵ�λ�ã��ִ������۾���ʳָ������������һ�㣬����⣬�����������б����࣬�ޱ��˳�������
����
�����˳�����Ȼ�ǻ��������������ƨ��ƨ�ߵ������鷿���ˡ�
��������λʶ����ģ������ܴ���ʥ�⣬��Ȼ֪����Щ�������ϲ���̨�棬ֻ��˽����ʾ�ġ�������ʳ����Ŀ����������ӣ����ڳ�����̸��ʵ�������������Т�����µ�����������һ��˵�������δ�ʹ��üͷ��û����չ������λ�����������Ƶ�������ô�����������Դ�µ����Ƿ緶��������Ǹ������⡣
����
�������Ǹ����ľ���Ҫ���������Ū��Ū�ģ�ʱ��͵��˰�����˷�գ��ʵ������ڻʺ��������ƣ����˷��ʵ۾�Ъ���˻ʺ�
�����ȵ��ڶ������磬�ʵ۲ŵ��˿գ��е����е�ʱ�䡣����������ᣬ����뜏���˵�����˵��һ�£���Ȼ�Dz���˵�뜏Ҫ�����µģ�ֻ�Ǹ�֪����һ�������Ѿ����ˣ��������DZ��µ���˼����
�����ʵ���������������������ӵ��������ϣ���һ�ڲ��ݵĶ��裬��������Ҳ�����ŵ���̬������ȥ������
����
�С�������۸���
�����ʵ���ݹ�����ʱ���뜏���ںȾơ�
���������Ȼ������������ֵľƣ�����̫ҽ���ҩ�ơ�������˵���ոշ����纮���ˣ��ǽ������̼��ģ�ƫƫ��̫ҽ˵ҩ�ƶ��빫�ӵ��������к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