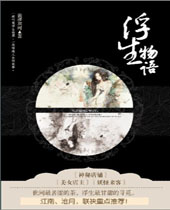只此浮生是梦中-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战地 。。。
落日残照,西风陵阙。
将军站在城上。
前,是浩荡敌军。后,是一城百姓。
敌军扬言再不投降,破城之时便要屠城。
将军看着被攻城石器无数次毁损又被军民一点点修补起来的城墙。然而它已经撑不了多久了。像是被毁损了龙骨的船舷,被掏空了生命里的老朽。他可以想见下一次攻城的惨状。也许,不等敌军屠城,城内便已流血漂橹。
他想,他手上还有三样东西。
短剑,帅印,长刀。
放下帅印与长刀,或是用短剑破开自己的胸膛。
然而他不能。
他知道自己挡不住了。然而他也不能退。
他的身后不只是这一城的百姓。还有比插满旗帜的边关沙盘更广阔的地方。跨过春风不度的西北边关,向山明水秀的中原延伸着国土与在国土上生活着的人们。
他曾经在高岗上扬鞭回马,眺望的故园。
他一人,于这天下,如同蝼蚁。
这一城,却是中原的门户。
于这天下,如栋梁。
栋梁一倒,天下倾颓。
他应当死战,可以牺牲自己与士兵的性命,唯独不能降。
他应当是无愧的。一个精忠报国的将军。自己在为之拼命的理由,也无关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荣光。
他只是像个盾牌一般,戳在江山的门户,以血肉之躯保卫着身后的所有。
可是他沉默着。他已经看了无数遍——有些百姓脸上染上了肃杀的神采,而更多的士兵脸上却已有倦容。
他也已经听厌了。铁骑刀兵,马蹄声乱。
护城的石具砸碎了攀援的敌军归家的梦,铁蒺藜刺破马掌,扬起哀鸣。
然而他依旧是那个岿然屹立的将军。
他的铁甲裹束着他的意志。勒直了身躯与脊梁。
“传我号令。”将军曾经多少次将这句话放在舌底。然而终究无力说清。
向他冲过来的士兵哀哀地喊着。将军,降吧。我们已经撑不下去了。
然后,被人架住,拖走。
片刻,将军的副将行至他身边,铠甲洒上了未干的血。刻满风霜染遍烽烟的一张脸,与任何一个普通军士都无不同。然而他知道,他的副将,一个才加冠的大孩子,亲手杀掉了方才哀求投降的士兵。
其实那个士兵他还记得。他初来边关的那年,招兵买马,充实着人数少得可怜的军队。
边城原本不是边城。只是很多接近边境的小城中的一个。
自朝廷与胡兵战败,边城就成了中原的门户。这么多年来,受惯了洗劫的边关几乎已成空城。
只有一些世代在此的百姓还顽强地,等待着朝廷的兵马到来。
那个老母亲把她脸上还带着稚气、未满年岁的孩子推到将军的面前。两张脸都满怀希冀。
不过数年,那孩子已经是个百夫长了。
然而刚刚,
1、战地 。。。
他哀求着,降吧。
将军知道,他的母亲还在边城某一处柴扉后,为边关的将士们捣衣备炊。
副将看着沉默的将军。
他知道将军是少见的江南的武人。也许将军以前在江南山水琵琶声中舞剑的风姿也如柳如鸿。然而在这样的边城,他眼中的水墨烟雨是致命的伤。
崇尚武勇,论生论死,才是边关最适合的生存方式。
副将指着远处的山岗。凌坟乱冢,纸钱散落。“我的父亲,”他指着一处坟岗,“他在那里。我的祖父,”他指着另一处,“他在那。我的曾祖,”他继续着,声音平静低沉,“他在长安的郊外,敌军入侵,可惜壮志未酬身已老。”
“这一次守城战后,我会去祭奠他们。用敌人的血。或者,下一次,我也躺在那里了。”
“可是我们还算幸运。世代为将,尸骨总有人收敛。”
“我们盼着的只是保家卫国。将军,您这一让,一城的百姓得以保全。可是身后十六州的土地上恐怕要铺满白骨了!”
将军闭上眼,似是已闻到屠城时,刀砍火烧的味道,血与火。
敌军在城外喊话。
攻城的云梯,巨木,火石,混合着闷热窒息的空气。
还有半个时辰。
将军烦躁地喘气。天色渐暗,残阳似血。
脑中再没有百姓的目光,士兵的身影。
他只是想起他还在江南的时候。
将军还不是将军。只是个叫做子衿的孩子。
看着那人的剑——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人间物类无可比。
那人收剑回眸,轻声一叹:子衿,还是个孩子呢。
惊鸿一瞥,江山黯然。
ps:
那个“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人间物类无可比”是白居易的《胡旋女》。
2
2、吴钩 。。。
江南的乐音一向柔软靡丽。管弦丝竹,一曲长调哀婉动人。
说书的先生一拍醒木,张口便是一段才子佳人王侯将相的传奇。
江南也多才子。长衫青丝一束,玉佩轻挽,翩翩于浊世。展扇便是一段才情风流。
江南连剑也是刚中带柔的。如惊鸿,如游龙,离不开烟雨蒙蒙,水墨江山。
子衿住在这样的江南的一个巷子里。
他那时是江南盛产的才子中的一人。
还是个少年。未完全伸展的身躯,以及与之不相符的豪情壮志——
一杆笔,一壶状元红,舍尽天下风流。
那日。
子衿家后院对门住进了一户人家。一个断了右臂的人。
子衿心想,他应当是上一次与胡人的战争中受伤退役的士兵。他轮廓硬朗,行步之间似也带起西北朔风,冰雪黄沙。
子衿有些好奇,为了那人身上的硬——那种连江南的温柔也融不去的、带进骨血硬成石头的感觉,是江南的士子们绝没有的。
那人似乎身份不低,吃穿不愁。当然,他几乎是足不出户——残疾,总是要遭人白眼的,无论是在何地都不能免。
那人的院里常会传来咿呀的锯木声。过不多久,那原本有些空旷的院子便渐渐多了些东西。木制的茶具,马扎,还有种花用的藤架。远远还可以瞟到屋子里木制的床,没有精致的镂饰,只有拙朴的纹路,过硬的棱角。
他仍是惊叹于那人用独臂做出来的东西。他想,他是怎样用一只手完成的呢——
真是神奇。
他开始常常蹭去他家。
“你叫什么名字啊?”
那人皱了皱眉,似乎觉得自己叫得太无礼了些,子衿想。
“吴钩。口天吴,吴钩的钩。呃,就是从那个‘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里取的。”
“哈哈……你就这么对别人介绍你的名字啊?”
吴钩有些迟钝地捋了捋头发:“有什么不对么?”
“不是。我原本以为你跟京城来的钦差是一样的,文绉绉地说半天,其实什么也没提。没想到——你这个人还不错!”
“我还以为江南更讲究这些。”
“哈,也许其他地方是这样吧。不过在这里,你有一壶好酒一手好文章就可以了——不是北方的烧刀子,是青梅酒,或是黄酒。往巷子口哪个戏楼占一张桌子,有些好酒的人循着酒香就来了。往你面前一坐,吟几句诗,看对眼了这个朋友就算交了。”
“还挺豪爽。不过,我现在没有酒,”吴钩四下看了看,“我去拿点食物招待你。”
子衿在石桌旁坐了。石椅有些高,他须得跳上去。石椅子上有些水汽,冰冰冷冷的,沾湿了衣裳。
吴钩端着一些甜食出来——饼,千层糕,糖,芝麻。
还以为他会端出些北方的菜肴呢,子衿心想。不
2、吴钩 。。。
过,食材也缺乏吧。
从胡兵进犯开始,朝廷便不断征粮。加之北方河道淤塞,航运不通,那边的小食也绝少过来了。子衿边想边尝着自己吃惯的零食。
“对了——”这才想起自己还未报上姓名,好不容易感到一点羞赧,“我叫子衿。青青子衿的那个子衿。”
“很风雅。”
“江南最风雅的东西,从来都不是字词文章。”子衿眨眨眼。
“人小鬼大。”
两个人都沉默了。吴钩绝不多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子衿。无忧无虑,无拘无束。
至少,现在是如此吧。
子衿被看得有些不自在了,从石椅上跳下来。拍拍手,翩翩然走了。
“明天我还来找你——记得在石椅上放个垫子,这时节坐凉了容易得病!”
吴钩嘴角溢出一丝轻喟:还是个孩子呢。
子衿记得自己那时还是个任性的孩子。整日整日地缠着吴钩,也不管他有多无可奈何。
3
3、弈棋 。。。
子衿央着吴钩做了一副棋。在最简单的木板上漆一层漆,刻下方格,楚河汉界分明。
子衿第一次看到棋子的时候差点噎着自己——竟然连棋子也是方的。
随即想到吴钩的手多不方便,也莫名多了些惭愧。
子衿向店铺要了些油墨,自己用毛笔蘸了写字,于是棋子终于两军对垒,泾渭分明。
木是软木实心,木制的棋盘架在假山旁的石桌上,走一步棋叩一声,闷闷地响。
子衿觉得,一盘象棋上杀伐决断,揽尽天下风云,应该是比围棋更果决、狠厉、直接的。
他移动着小卒,冲杀过河,几乎呈包围之势。
他悠然地看着眼前的棋盘。
吴钩在棋盘前专注得像是对待天下战局,然而,他却常常会怜惜众多的卒子。
走马,走相,走炮,走車,吴钩往往都不如动一颗卒子那般犹豫。
“这里不对。走马会让帅面临险境。”
“这里不对。走炮这步没什么意义。你那颗卒子就那么矜贵?”
“你居然去动車?”
子衿看着吴钩,一一点出他留下的破绽。
“我只是想看你怎么动卒子而已。”
他居然就是有本事不动卒子。自己要吃去他的卒子他竟然还用車去救?!
“卒子过河难回头。”吴钩轻声回答。
“动了将,或是帅,也总有挽回的余地。真正无法回头又只能步步为营的卒子,必得尽力保全。虽不能说是无伤,亦该愈加珍重。”
“在边关,最多的便是普通百姓与没有官阶的士兵。有的新兵甚至没有练兵的机会便被推上战场。几次战斗后活下来,才算是正式成了老兵。”
“很多时候戍边的征夫们甚至等不到妻子寄来的衣服,就已经死在异乡。”
“将军即使再怜惜士卒,也只能在战场上尽力冲杀,希望能减少一些伤亡。”
“跟着我的一个士兵,就是为我挡箭而死的。士兵的铠甲一般都很薄,兵刃也普通,鞍前马后地照顾我,上了战场也只能用身躯去抵挡。否则,我不只会失去一条手臂吧。”
“中原历朝皇帝偏安一隅,尚文轻武,一个从四品武将遇到六品文职京官都要让道,地位低微,每年的武举状元虽有武功,却乏文采,碰上太平盛世明君贤主反而常常沦为赋闲在家的摆设。”
“混入军队的王孙贵族还好,出身卑微的寒门武将都盼着建功立业,杀敌扬名,却常常忘了保家卫国亦即保卒安民。”
“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子衿不禁感叹。
“正是如此,”——“叩”的一声,小卒将军。
子衿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露出的空门。
以及——吴钩唯一过了河的小卒。
“锋芒过盛,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