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出书版)-第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那么一刻,见识过多少赫赫人物杀死过多少赫赫人物的霍大将军,看
见司马迁的膝盖动摇了——
他,必然动摇。读书人的话都是废话。指使他们惟一要用的就是剑。陛下,
还是贪一时新鲜,陛下不会爱上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不可能取代自己。
——在动摇后,略略有些弯后,他最终没有跪下来,脸上有红的掌印,额头
有没褪的疤痕,这样的司马迁还要做什么呢?
他往前走了一步,又走了一大步,直到剑锋可以刚刚好必死无疑地擦到了自
己的脖子。
冷,咽下唾沫,也会有割破的疼。
他,此刻,必须对峙;失去信念,史记,就不配再写了。
他的信念,如此执着,是不可以此时此刻跪下的。
32
世界上总有一些人,是你不可理解的,他们也许真的很糟糕,很糊涂,很怪
异,不要以为你永远不会理解他们,坚定不是用在这个时候,命运是在轮回里走
过的。
就像霍去病杀不了司马迁。就像汉武帝此时此地居然出现。
好象正版官样的汉剧,定格在那最剑拔弩张的时刻——一切都可能发生,一
切都还来不及发生。
这个舞台上,人们总是反应不及。
武帝他,堪堪站在了太史令的门口,皇帝自己推开门,天子逍遥拎着酒盅,
一切都显得随心所欲,这个高大男人无拘无束地出现在了小小陋室,斜斜靠在了
门边,除了腰带上的碧玉连城,你再也看不出,翩翩贵公子一般形状的男人,原
来是个皇帝啊。
他的手里,甚至还在一晃一晃地掂量着沉酿,如此不慌不忙。
——反显得,这剑拔弩张的两人,像演戏。
但霍去病就是不撤剑,他无视皇家,剑芒隐隐见出血来。司马迁梗着脖子,
不见退让。
就这样僵持。
“爱卿,怎么连你也胡闹起来……”
皇帝拎着他的酒盅,走过来,不愠不火,不怒自威。
“不要过来,陛下——”年轻的美丽的男人,喉头的吞咽是艰难的,他眼里
只是对方的喉咙,只需要轻轻一刺或削开来——他的眼,不美丽,而像狼,贪婪
刻毒,这让美丽扭曲:“他不承认你,他否定我们,他是怎样的贼寇乱党?他手
段不见得多么高明,却把您迷得晕头转向——他算是什么东西!”
“小霍,你要吓到他了。”皇帝的声音仍然是调侃,只是走得更近了。
司马迁闭上眼睛,索性不理。要杀要寡你们一向随便。
——漂亮的人,和固执的人——漂亮,还好,倒是固执,最最让人头疼。
霍去病这时忽然转首,他看着刘彻,星辰般耀目的眼里情感铭心刻骨,他用
如此专注的目光定定看着皇帝,就好象从前,他是小小的孩子,他是牵他手的青
年——
他想唤起他的记忆——是的,我们共有的记忆比谁都多,不是吗?
“我现在只想知道——”他笑得非常残酷,等于拿自己做赌注:“我杀了他,
你会怎么对我——”
话音落了,他就刺下去了。
司马迁想,是时候了。大限来了。
他觉得有些冰冷,太紧张,手脚都冰冷,现在有些庆幸自己是闭上眼睛的了。
喉咙的硬物又进半分——
——“你真想知道朕会怎么对你?”——
这声太清晰,就像在他耳旁,但他睁开眼,却真的看见,刘彻是在自己身旁
——皇帝很少出手,也不需要出手。但现在,他一手抓开了木头一样呆杵的司马
迁,一手就势甩出酒盅击偏了霍去病的利剑,很精准,哪步慢了都要出事。很冷
静,他见到最亲密的人生死也能保持冷静。
现在,他把司马迁再拉过来,抬起他吓得冰冷冷的下巴,抬高了,司马迁硬
邦邦地抬高了,完全看出了他的害怕,皇帝的眼里有些许少年人的恶意,知道怕
了吧?端详了下,才抽出自己随身帕子,捂了伤口,系紧。
“没有朕的宠爱,你知道,你也就再不是霍去病了。”类似的话,他说过。
有人冥顽不灵,还有人,却依赖他的宠爱而活。他无法无天的宠爱。
当他宠爱你的时候,你是可以无法无天的。
皇帝的眼,沉得无边无际,这是皇家的眼,威严纵深,而让人发寒。
霍郎慢慢地放下剑,慢慢地摇头,慢慢地不可置信,慢慢地是笑了还是有泪
了,“哐当”掷剑于地,拂袖转身便走。
这室内,风波席卷而过,竹影凌乱,往日宁静已不复见。
他问他,“还冷吗?朕抱着你呢。”
刘彻轻轻环抱着他,像个小婴儿拍着他的背,摇晃,微微,用他的胡茬反复
磨着他的额头鬓角,像磨蹭一只狡猾又胆小的小猫,蹭出冰冷外的疼痛,司马迁
和刘彻就这样拥抱着,他的英伟张狂包裹住他的书生意气,他的双臂占有而温存
地一点一点紧紧圈紧他,直到不再冷了——一瞬间涌现的,是平静的温情,刚刚
的一幕确实是让人害怕的。无论对谁都是。
33
“这个孩子,到底像谁呢?”近乎感慨,他此时感慨良深倒像是父亲兄长一
般无二来!
司马哼哼,鄙视地。
“为什么不怕我?”
他突然这样问。
问得像个白痴。
帝王也未必时时精彩。维系着时时精彩,那也好累。
“或者……”他抓住他规规矩矩包着的青斤,扯住他端端正正的脑勺,逼迫
他必恭必敬盯住自己,司马迁的眼,规矩端正肃穆,那是一种没有感情的眼神,
但并非无情,只是感情都投注给了枯燥深涩的那里——历史里。
刘彻心里,掠过些什么。这使他的轮廓不像帝王,而开始温柔缓和起来。
“或者,朕不是一个好丈夫,好情人,但朕会是千秋万代里最伟大的君主;
而你,太史令,必须公平地写出,就算我——是你的男人,是占住你身子、把你
当女人一样使用的男主人。”
他推他,突然发力,使他跌跌踵踵撞在墙面。不重,但太突然,同时他说的
话也太恶质,这让他反应不过来——
他注视着他的那种独有的木讷,笑了,然后压过去,很服帖,伸手捏揉他的
下身,隔着布料,轻柔地猥亵。
“朕没告诉过你,你比小霍还风骚吗?你要射的时候,就会放荡地像妓女一
样吸住朕的整根——然后,你就叫——大声地让所有人都听见——朕要让所有人
知道你是谁的——”
他的手指逐渐下滑,从后背滑到了他的后腰,然后在尾椎附近圈点着,就好
象批阅奏章,没有力道不急不徐。汉武帝的鼻翼在深深地吸气,就好象龙要遨游
天际前的姿态,这条真龙所喷出的鼻息抵在司马的脖子和脸上、甚至胸脯上,每
当他有所挣扎,他就更使力,压他陷进墙里。
他们甚至衣着整齐完好。
司马被拉下的襟衣,有完整的湿漉痕迹,那胸膛急剧地发抖,当他恶毒地舔
着他乳首,不依不饶咬着那红色蕊吸取时,催情的效果就完全达到了,司马的反
应是非常明显的——这是一个非常低档次的选手,在淫乱宫闱里连打入冷宫的资
格都不配——恶质地观看对方明显的反应,他继续说着淫糜的话,抓住司马腰,
拉过来,去使力,拱进去。
没有脱衣服,只是这样,他的形状完全勃起,那几乎是隔着衣服在强奸的恶
极!
天未全黑,窗开着,他甚至不知道门有没有合上——
“你够了!”
他在经历慌张、动情、难堪和种种不适应后,最后想起来怒斥自己的皇帝陛
下,狠狠扯着脖子上的丝巾,他想砸还给他。全忘了被剑削开一道凌厉口子。
“动什么——”他拍他手,重重一拍,扭到身后,像扭麻花一样,不管对方
叫着疼。然后不由分说,低下头,去大力咬那细细颈子——
他感觉自己皮肉都要掉了,脖子也快要拧断了,他想喊、但喉头动不了,他
在抵着——
“朕不来,你怎么办?”
“你怎么不把脑袋都送过去让他砍?你是猪你是狗吗,你把自己当成什么?
朕是神仙能一直救你吗,司马迁,就算霍去病刚才杀了你,朕也不能动他,朕是
这个国家的主人,你根本不懂吗?”
“答应我,这些人面前,你往后退,往后退!快,答应朕!”
他如此严厉,面部几乎有扭曲的严厉,就好象匈奴来犯时他在朝廷上拍案而
起惊得臣下均面无人色——而此时,刘彻的下身在钉着这个身体,手指如盘麻花
般拘起,他就像个布袋人,为他所操弄,只是现在脖子坏了,又出血,滴答不停。
他咬了咬牙,不支声,想用毅力对抗这来自于男人而非君主的残暴——
“下贱的东西……”他又再度这样说他,像为激起他更深的激动和羞耻——
就着站的姿势,刘彻解着他的衣服,一件一件的落在地上,他靠着他肩膀,看他
解着自己衣服,乱七八糟扔着,激动羞耻和更难以启齿的一些东西,让司马迁此
时失去反抗的力量,起码这时候,身体确实是屈服了。
那是种让人昏厥的情绪,好象吸进了满头脑的迷药,他双手背在身后,即便
此时已经不被硬压着了,但手还是维持原来的姿势;司马眼睁睁看着刘彻分开自
己臀,看了自己一眼,直直捣进,猖狂迷奸;耳朵边上又是再度萦绕对方下流侮
辱的话,但即便是这样,刘彻说的任何话都起不了鞭策了,这就是寻常百姓家床
头间热炕上小夫妻俚语。
他,是故意的。
模糊地叫着他名字,在冰凉的墙壁上半强迫地占有太史令,“做朕的妓女,
专属的妓女……每天在床上趴好像狗一样等朕临幸,让什么史记什么祖先都见鬼
去,朕烦透了你整月整年的乱跑、烦透看你的白头发、烦透你一看朕的朝服就闹
眼疼——”他激昂地亲着他嘴,伸进舌头,模仿抽查,疯狂挑逗他:“怕了吧?
不点头……就不让你泄。”
他硬是扯过什么绳结绑起他的激昂充血。
这,太故意了!
他不知道说什么,司马迁不知道自己,现在,该说什么。
就好象皇帝临幸妃子总会有近侍登记清楚。他几乎能想象自己的大名登录在
案,是多么让人眼红的频繁。
汉武帝的任性,他见识过,这次又开了眼界。被折腾,到很久。到最后,才
吃不住了,冷汗潸然筋疲力尽,才肯攀住刘彻的肩背,像搭上浮木的可怜人,稍
稍喘息。
“我答应,我答应。”他自己也没想到,这次会答应得这么轻快。是的,他
对他做了承诺。身下的疼其实已经快麻木了,并不是那么渴求解放。但,不再那
样界限清楚壁垒分明,他也不想弄清楚这差别何在,这对他并没有多大意义。
他现在只是答应了,他的君主,他的皇帝,他的男人。
“答应什么?”他摇晃脚底虚浮的他。
“不逞强,老实写书,不把脖子对着刀剑,不能比你死得早——”
“你倒真敢说——朕也答应你,让你跟朕同年同月同日死吧。”他笑了,这
时候看着老鼠被玩得快不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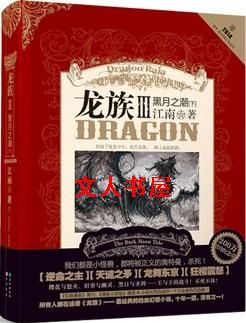

![跳梁小丑混世记16逍遥 作者:易人北[出书版]封面](http://www.xntxt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