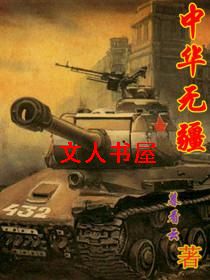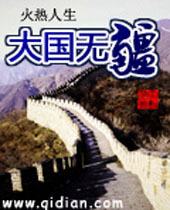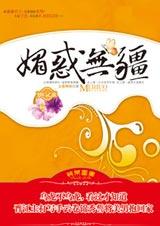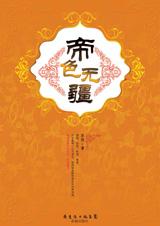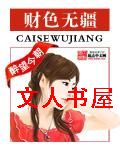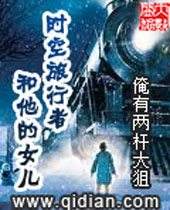行者无疆-第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联想到了中国。
科隆教堂开始建造的时候,中国还在南宋,元好问刚刚写完“醒复醉,醉还醒”不久;而造好之时,李鸿章已经在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已经有自来水和电报了。
这么长的时间,经历了元、明、清三朝,改朝换代,天翻地覆,地面上的像样建筑,能保存多少?天际的尖顶,能维持多久?
科隆大教堂的尖顶已经做成模型陈列在广场上,用世界各种文字说明。
正对教堂大门的,是中文。
人家当然不是要故意劝喻我们什么,但我们中国人看了,或许会有所自省。
3连鬓胡子的西门子先生死于一八九二年,但早在二十年前,他已为中国提供了第一台电报机。那年月中国的灾祸接连不断,全由那个键盘艰难地敲出,嘀嘀哒哒如泣如诉。
今天来到慕尼黑西门子公司总部,看着他的塑像,很想告诉他,在他死后四十多年,公司派驻中国南京的一位代表,利用国际身份,在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下救出了大批中国人。
他的名字叫拉贝,据说与纳粹有过一点瓜葛,晚境寂寞;但古城南京可以证明,万千亡灵可以证明,他是好人。
现在西门子公司的职员,几乎无人知道他。但正是他,曾让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首都在遭受大难时,把西门子公司看作是和平和人道的化身。我想不起世间还有哪家企业,取得过这种身份。
如有可能,请在西门子的历史上,加上他的大名。
教皇的卫士
这曾经是世间特别贫困的地方。
贫困带来战乱。但荒凉的中部山区有一位隐士早就留下遗言:“只须卫护本身自由,不可远去干预别人。”
话是对的,却做不到。太穷了,本身的一切都无以卫护,干预别人更没有可能。但是,别人互相干预的时候来雇佣我们,却很难拒绝。
结果,有很长一段时间,欧洲战场上最英勇、最忠诚的士兵,公认是瑞士兵。瑞士并没有参战,但在第一线血洒疆场的却是成批的瑞士人;更触目惊心的是,杀害他们的往往也是自己的同胞,这些同胞受雇于对方的主子。
瑞士人替外国人打仗,并不是因为人口过剩。他们人口一直很少,却紧巴巴地投入了这种以生命为唯一赌注的营生。说是“赌注”又于心不忍,因为赌注总有赢的可能,但他们却永远赢不到什么,即便打胜了,赢的是外国主子,还有作为中介商的本国官僚,自己至多暂时留下了一条性命。
这样的战争,连一点爱国主义的欺骗都没有,连一点道义愤怒的伪装都不要,一切只是因为雇佣,却不知道雇佣者的姓名和主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发动这次战争。为了一句话?为了一口气?为了一座城堡?为了一个女人?都有可能。
这是一场千里之外陌生人的对弈,却把两群瑞士人当作了棋子。
说起来这样的战争真是纯粹,只可怜那些棋子是有血有肉、有家有室的活人。刀剑刺向同胞,杀喊和惨叫中裹卷的是同一种语言,与双方主子的语言都不相同。可能,侧耳一听那喊声有点熟悉,定睛一看是久未谋面的亲戚,但刀剑已下,喊声已停,只来得及躲避那最后的眼神——这种情景,应该经常都在发生。
经过几百年这样残酷的训练,我相信这个族群必然会淡漠理义和感情。这在瑞士的思维领域和创作领域都能看出一点踪影。
这种训练的正面成果,是养成了一种举世罕见的忠诚。忠诚不讲太多的理由,有了理由就成了逻辑行为,不再是纯粹的忠诚。因此,戒备森严的罗马教皇从来不对贴身卫士精挑细选,只有一个要求:瑞士兵。
直到今天,罗马教廷的规矩经常修改,他们的多数行为方式也已紧贴现代,唯有教皇的卫士,仍然必须是瑞士兵。
但是,除了教皇那里,瑞士早已不向其他地方输送雇佣兵。这是血泊中的惊醒,耻辱中的自省,他们毕竟是老实人,一旦明白就全然割断,不仅不再替别人打仗,自己也不打仗,干脆彻底地拒绝战争。
他们太熟悉战争又太不熟悉战争。熟悉的,是刀刃血拼;不熟悉的,是战争的发动及其理由,战争的推进及其计谋,战争的结束及其善后。严格来说,他们还不大知道如何为自己而作战。
于是他们选择了中立。
其实,他们原来也一直中立着,因为任何一方都可以雇佣他们,他们没有事先的立场;如果有了立场就要因雇主的不同而一次次转变,多么麻烦,因此只能把放弃立场当作职业本能。
从接受战争的中立,到拒绝战争的中立,瑞士的民族集体心理实在是战争心理学的特殊篇章,可惜至今缺少研究。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已经为它的中立提供了奇迹般的机会,而它,也成了世界的奇迹。
瑞士没有出现铁腕人物,也没有发现珍贵矿藏,居然在一百多年间由一个只能输出雇佣军的贫困国家跃上了世界富裕的峰巅,只因它免除了战争的消耗,还成了人才和资金的避风港。中立是战争的宠儿,也是交战双方的需要。
也许,这是战神对他们的补偿?战神见过太多瑞士兵的尸体,心软了。
那年月瑞士实在让人羡慕。我曾用这样几句话描述:人家在制造枪炮,他们在制造手表,等到硝烟终于散去,人们定睛一看,只有瑞士设定的指针,游走在世界的手腕上。
闹市草莽
欧洲的好城市都很难用“繁华”一词去形容。如果以美国式的新锐密集去想像它,或者以亚洲式的光怪陆离去揣测它,就都错了。
一路行来,觉得这些城市千百年来都在自身等级上爬坡。有的爬着爬着爬不动了,便蹲坐在某个高度上,一蹲就蹲了好几百年,有的则还要往上爬。脚力不同,方向一样,因此也就高高低低分出了层次。这种层次,与我们中国人想像的有很大的不同。
粗粗一分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叫打点生活,第二层次叫打点历史,第三层次叫打点自然。
打点生活是基础。别看它们样子陈旧,现代设施却很完善,不管是私人住房还是街道社区,大多舒适而方便。正是这种现代意义上的便利,使一切陈年的遗留不显腌臜,使各种土俗的风物别具厚味,因此也使打点历史有了可能。欧洲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城市毁损严重,但大家不约而同,那样精细地护惜遗迹,那样虔诚地挽留历史,结果,今天欧洲城市的古典格局,居然远超别处很多并未经历战火的城市,这真是欧洲文明的骄傲。
有了这两番打点,人们既可享受现代的方便,又可品味古典的情韵,这便是十足的欧洲式奢侈。单有一方,奢侈不起来。
一般也就够了,却还有更奢侈的,那就是要在城市里打点自然。这事历来有人向往,因此很多城市有山有河,有湖有林。可惜的是,时间一长,这些山河湖林也渐渐城市化,像威尼斯的那些小河和巴黎的赛纳河都是如此。美则美矣,却承担太重、装扮太累,已不成其为自然。这总于心不甘,有没有可能来一个倒置,让城市百物作为背景,作为陪衬,只让自然力量成为主题,把握局面?
让人动心的“维也纳森林”只围在郊外,而柏林,则活生生把森林的灵魂和气息引进市中心,连车流楼群也压不过它。更叫我满意的便是瑞士首都伯尔尼,那条穿越它的阿勒河(Aare)不仅没有被城市同化,而且还独行特立、无所顾忌,简直是在牵着城市的鼻子走,颐指气使,手到擒来。
伯尔尼把中心部位让给它,还低眉顺眼地从各个角度贴近它,它却摆出一副主人气派,水流湍急,水质清澈,无船无网,只知一路奔泻。任何人稍稍走近就能闻到一股纯粹属于活水的生命气息,这便是它活得强悍的验证。它伸拓出一个深深的峡谷,两边房舍树丛都恭敬地排列在峡坡上,只有它在运动,只有它在挥洒,其他都是拜谒者、寄生者。由于主次明确,阿勒河保持住了自我,也就是保持住了自己生命的原始状态。与那些自以为在城市里过得热闹、却早已被城市收伏的山丘河道相比,它才算真正过好了。
这就像一位草莽英雄落脚京城,看他是否过好了,低要求,看他摆脱草莽多少;高要求,看他保留多少草莽。
突破的一年
那天我独自在伯尔尼逛街,绕来绕去几次迷路,后来终于悟得一个诀窍,一旦迷路就找河,找到了阿勒河就找到了最忠诚、最年老的向导,再也错不了。如此几度反复,我把伯尔尼的主要街道弄得清清楚楚。傍晚回到旅馆,伙伴们从广告资料上查到一家应该不错的餐馆,却不知道怎么走,我豪迈地当门一站说:请跟上!路线一旦摸清,以后几天逛街就变得潇洒,只一味摇摇摆摆、东张西望。克拉姆大街起头处有一座钟楼,形体不像别的钟楼那样瘦伶伶地直指蓝天,而是胖墩墩地倚坐街市,别有一番亲切。它的钟面大于一般,每小时鸣响时又玩出一些可爱的小花样,看的人很多。此刻正是敲钟时分,我看了一会儿便从人群中钻出,顺着大街往东走,觉得这一带该是每小时都被同一种钟声统领的族群所在。人的生命存在,无非印证于时间和空间,因此在这钟楼下的时间共享,其实也就是生命共享。这种共享既然被一小时、一小时安排得精打细算,那么即便素昧平生也会觉得已经深深地朋友了一场。
突然觉得右首一扇小门上的字母拼法有点眼熟,定睛一看居然是爱因斯坦故居。我认了认门,克拉姆大街四十九号,然后快速通知车队的伙伴,要他们赶紧来看。
瑞士拿不出自己悠久的文化史,只是近百年有些国际间的文化人贪图它的安静、美丽会到这里来住一阵,结果它也就频频地进入人类文化视野,用不着再气短自惭。
愿意来住的文化人是什么等级?住了多久?在这里有什么创造?……这一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一座城市的器识和荣辱,至关重要,对于自身根基较薄的城市更是这样。现代国际间各个城市的文化史,其实就是文化创造者们的进出史、留驻史。因此,在伯尔尼街头看到爱因斯坦踪迹,应该当作一回事。伙伴们一听招呼就明白,二话不说跟着走。
没有任何醒目的标记,只是沿街店面房屋中最普通的一间。一个有玻璃窗格的木门,上面既写着爱因斯坦的名字,又写着一家餐厅的店名。推门进去,原来底楼真是一家餐厅,顺门直进是一条通楼梯的窄道,上了楼梯转个弯,二楼便是爱因斯坦故居。
这所房子很小,只能说是前后一个通间。前半间大一点,二十平方米左右吧,后半间很小,一门连通,门边稍稍一隔又形成了一个可放一张书桌的小空间。那张书桌还在,是爱因斯坦原物。桌前墙上醒目地贴着那个著名的相对论公式:E=mc2;上面又写了一行字:一九〇五年,突破性的一年。
故居北墙上还用德文和英文写出爱因斯坦的一段自述:“狭义相对论是在伯尔尼的克拉姆大街四十九号诞生的,而广义相对论的著述也在伯尔尼开始。”
伙伴们很奇怪,英语并不好的我怎么能随口把“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这些物理学专用名词译出来,我说我很早就崇拜他了,当然关注他的学说。但自己心里知道,当初关注的起因不是什么相对论,而是一位摄影师。
那是六十年代初我还在读书的时候,偶尔在书店看到一本薄薄的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