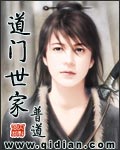大宅门-第9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玉婷:“快进来吧,我七哥来半天了。”
西客厅里。
众人在沙发上坐了一圈儿,苦菊忙着倒茶。
玉婷:“我这儿最保险了,一年也来不了几个人。”
景琦注意地观察着玉婷和万筱菊。
万筱菊:“我二位师哥一说上您这儿来,我就说不合适。这是冒风险的事儿,怎么能叫您……”
景琦:“甭说客气话,请都请不来,唱了一辈子《打孟良》、《打焦赞》、《打耶律》、《打韩昌》、《打瓜园》,今儿又唱了一出打鬼子,得犒劳您。”大家都笑了。
齐福田道:“玉婷姑娘见义勇为,拔刀相助,对万老板可真是没的说。”
玉婷:“这不应该的?!总算给了我一个给万老板效力的机会。”
万筱菊忙欠了欠身:“哎哟,这可不敢当!”
玉婷:“住下吧,想住多少日子就住多少日于。”
景琦心领神会地微微笑着:“我说什么来着?!……不过老住这儿也不是长久之计,最好早点儿离开北平!”
陈月升:“我们想法子,先去乡下躲躲。”
“我们走啦!”齐福田站起来,景琦和陈月升也站了起来。
玉婷起身拦住:“哪儿也不能去,这儿凑合一宿,天亮了再走。现在出去不是找挨抓吗?”
景琦:“说得是。坐下吧,干脆,齐老板,今儿给我说《锁五龙》。”
玉婷:“万老板,您住北屋,都收拾好了,您先看看。”
万筱菊:“不忙不忙。”
景琦:“去吧去吧,别吓着就行了!”
“怎么了?”万筱菊莫名其妙,奇怪地看着景琦。
玉婷:“听他胡说呢!来吧!”玉婷先出了门,万筱菊忙跟了出去。
景琦着他们出了屋,说道:“这回我妹妹可遂了心愿了。”
北屋卧室。
玉婷进了屋,掀起门帘,万筱菊怯怯地站在门口没敢进。
玉婷:“进来呀!”万波菊迟疑地走进了屋。
玉婷心绪复杂地望着万筱菊。
万筱菊不好意思地环视屋内,立即惊呆了。但见满屋菊花,墙上赫然挂着他和玉婷的照片。万筱菊很是惊慌:“您这是?……”
玉妹笑了:“吓着了不是?!我七哥刚才不说了吗?叫您别吓着。”
万筱菊诚惶诚恐地望着,屋里到处是菊:种在盆里的菊花,绣在帐子、被子、枕头上的菊花……
万筱菊:“您这菊花也是?……”
玉婷:“应您那万筱菊的‘菊字。”
“您这么抬举我,我做梦也没想到……”万筱菊充满了敬意地望着玉婷。
玉婷向床边走去:“怎么?没人告诉您?我和您的相片儿结婚已经十年了!”
万筱菊大惊失色,呆呆地说不出一句话,看着玉婷拿起床头的盖头,嘲弄地看着,慢慢盖到了自己的头上。
万筱菊痴痴地走到床前,坐到了玉停身边,默默地看着。蒙着盖头的玉婷虽一动不动,但心潮澎湃,耳边似乎响起了十年前“结婚”时的京戏曲牌……
万筱菊无限伤感地望着,眼里不禁涌出泪水,轻轻揭下了玉婷的盖头,玉婷仍低着头一动没动。
两人默默地坐着,万筱菊轻轻拉起玉婷的手,玉婷突然将手抽回,抬头望着万筱菊,万筱菊有些惶恐地向后挪了挪身子。
玉婷看着万筱菊,眼中充满了陌生感和疑问。万筱菊不知所措地低下了头。
玉婷慢慢站起身走出了房间。万筱菊低头坐着没有动……
玉婷家门外街上。夜。
郑老屁架着黄包车,玉婷坐在车上,景琦站在车边:“这是干什么?怎么刚见面一会儿,你就走了?”
玉婷:“你那儿是我的娘家,我回娘家住几天。”
景琦:“你想了那么多年,今儿好不容易见面儿了……”
玉婷:“七哥!我是和相片结的婚!”景琦愣了,不解地望着玉婷。
玉婷:“老郑,走吧!”车走了,剩下景琦呆呆地望着。
玉婷家西客厅。夜。
齐福田看着从外面回到屋里的景琦:“她就这么走了?”
陈月升:“闹什么不痛快了吧?”
景琦:“说不清,我妹妹不是那小心眼儿的人。”
齐福田:“那是为什么?”
不待景琦再说话,门一响,万筱菊满腹心事地走了进来,低着头坐到沙发上。
齐福田、陈月升、景琦面面相觑。
万筱菊低着头一言不发。
四个人默默地坐着。万筱菊双手抱头伏在膝上一动不动。
百草厅门口。
门口停着三辆摩托车,四个日本宪兵和四五个汉奸站在门口,堵死了大半条街,百草厅里不时传出凶狠的吆喝声。十几个胆大的行人在路边看热闹,“南记”和几个铺面都在慌忙上板儿。
福特汽车慢慢开来,白颖宇坐在车里,车慢慢地停了。颖宇张望道:“前边儿干什么呢?出什么事儿了?”
司机:“站着鬼子呢,好像是冲着百草厅。”
颖宇:“甭理他,开过去!”
司机按着喇叭缓缓向前开。站在街上的鬼子和汉奸都回过头看。汽车缓缓前行,不停地响着喇叭。一日本兵大步向汽车走来,后面跟着汉奸翻译官,到了车前。
日本兵喝道:“干什么的?下车!”翻译敲着车窗:“下车!”
颖宇探出头:“我去前门,让让道儿!”
日本兵:“见了皇军为什么不下车?”翻译又道:“太君问你,见了皇军为什么不下车?”
颖宇:“见了皇军我为什么要下车?”
翻译向日本兵说着什么,日本兵大怒,一挥手。翻译喊:“把他拉下来!”俩汉奸上前开门,将颖宇从车中拉了出来。
颖宇大叫:“干什么,干什么,我去前门,招着你们啦?”俩汉奸将颖宇揪到车前,将他死命按到地上。
汉奸:“跪下!”颖宇挣扎着,被汉奸死死按住跪在地上。
颖宇大叫:“你们要干什么?我是百草厅的东家,你们敢这样对待我!”
翻译:“正合适!你们百草厅出了共产党!”
从百草厅门口,两个汉奸押出了赵大水三查柜皮云良焦急地跟着跑了出来。
日本兵一挥手:“上车!”拉开汽车门坐到了前座。汉奸押着赵大水到了车前往车里推。
颖宇仍被死死按住跪在地上,他挣扎着喊:“撒手!讲不讲理你们?!”
日本兵命令司机:“开车!”司机犹豫着,日本兵突然拔出刀架在了司机的脖子上,大喊:“开路!”司机惊慌地望着车前仍被按在地上的颖宇。日本兵又瞪眼大喊:“开路!”吓得司机慌忙向前开,同时猛打方向,但汽车仍是冲向颖宇。俩汉奸一见,忙松手跳开上了摩托车,颖宇吓呆了。就在汽车即将撞过来的瞬间,皮云良猛地一个箭步冲上去,抱住颖宇向路边滚去。
汽车轰地驶过,露出了躺在路边的颖宇和皮云良。围观的人“哦——”的叫了一声。
颖宇抬起身大骂:“操你妈的小日本儿,想轧死我?!”
皮云良忙拉起颖宇向百草厅走去。
百草厅公事房。
颖宇躺在沙发上,小胡正给他揉肩捶背,伙计忙着端水倒药。皮云良在角落里低声打着电话。
景琦匆忙走进屋:“三叔!没事儿吧?”
颖宇:“没事儿,要不是皮头儿,我今儿就见不着你了。我跟他小日本鬼子没完!”
皮云良挂上电话:“老太爷,少说几句吧,你儿子是国民党,叫日本人知道了也没好果子吃!”
颖宇坐了起来:“我儿子跟蒋委员长去了重庆,他能怎么着?!”
景琦吩咐着:“赶紧送三老太爷回家!路上小心!”几个人扶颖宇起来,向外走去。
景琦嘱咐着:“三叔儿,景武去重庆的事儿,少往外说!”
“反正也这样了,这么活着还不如死了好,明儿我去重庆找我儿子去……”颖宇唠唠叨叨着被人们扶出了门。
屋里只剩了景琦和皮云良。景琦道:“柜上怎么会弄出共产党来了?”
皮云良:“赵大水是共产党,您信吗?”
景琦:“我当然不信,可总得有个缘由啊?”
皮云良:“前些日子卖了一批成药,是山西一个大户买走了,愣说这批货是运到陕北匪区的!”
景琦:“那到底是不是呢?”
皮云良笑了:“是不是跟咱们没关系!咱们是买卖人,谁给钱就卖谁!”
景琦:“话是这么说,可真要是卖给八路的……”
皮云良又笑了:“七老爷,我那天不说了吗?您不能老在大宅门儿里蹲着,您得知道知道外边儿的事儿!”
景琦:“家里还乱不过来呢,还外边儿呢!”
皮云良:“您是明白人,八路是干什么的?打日本的!您忍心看着伤员没药治?!”
景琦惊讶地:“这么说是真的?你都知道广皮云良:”七老爷不用刨根儿问底儿了吧?!您要害怕,咱往后不卖!“
景琦:“我说不卖了么,啊?我说了吗?!我害什么怕?!我恨不得把日本鬼子一个一个都挑喽!”
皮云良:“那咱们都睁一眼儿闭一眼儿。可我告诉您,赵大水绝不是共产党,您得救他!”
景琦:“闹到这份儿上了,我怎么救疗皮云良:”您还没看出来,这都是王喜光闹腾的,可他也是瞎猜,并不知底,无非是想敲您一笔竹杠!“
景琦:“花点儿钱无所谓,这汉奸不能当!”
皮云良:“他这就是撒网呢,叫您一点儿一点儿的就范,这网会越收越紧,您躲不开!我倒觉着您不妨当这个会长,何不将计就计!”
景琦:“那你怎么不当?”
皮云良:“我还真想当!我要是当了,叫日本鬼子寸步难行!”
景椅惊讶地:“怎么个将计就计,寸步难行?”
皮云良笑了:“我不能再多说了,七老爷一世英雄,什么没见过?!
您甭跟王喜光顶着干,何不把他哄顺了,他拿了钱,决不会在赵大水的身上扯不清!“
景琦以异样的眼光望着皮云良:“看不出来你挺有心计的,我没白提拔你。”
皮云良:“只要咱们中国人抱成了团儿,日本鬼子斗得过咱们吗?!”
景琦久久审视着皮云良,若有所思。
药行商会。
药行会馆门上已挂上了伪药行商会的牌子。景琦走进大门。
会客室里,景琦和王喜光坐在沙发上,两人对视着,忽然都笑了。
景琦道:“这事儿无论如何得请王会长帮帮忙。”
王喜光:“七老爷今儿怎么这么客气?您也有求着我的时候?”
景琦:“当年你说得对,谁都有走窄了的时候,请王会长高抬贵手!”
王喜光:“我抬手没用,赵大水是日本人抓的。”
景琦:“日本人还不是听你的!”
王喜光一下子蹦了起来:“哎哟祖宗!您想要我的命啊!”
景琦:“赵大水怎么会是共产党?他听都没听说过!”
王喜光笑了:“我知道他不是共产党。”
景琦:“那你抓他干什么?”
王喜光神秘地:“我就是想叫你知道,不论你们柜上还是家里,我想抓谁就抓谁。”
景琦:“那你抓我,把赵大水放了。”
王喜光:“要放人也不难。”王喜光从桌上拿过一张委任令:“您在这上头签上个字儿!”
景琦急了:“两码事!这跟当不当会长有什么关系?”
王喜光:“一码事!你只要一天不把名儿签上,我叫你一天不得消停!”
景琦压住火儿望着王喜光。王喜光则嬉皮笑脸戏弄地看着景琦。
景琦:“你先放人,咱们好说!”
王喜光:“别来这套,我上过一回当了,什么叫‘好说’,香秀害得我跑外地躲了两年多才敢回北平。叫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