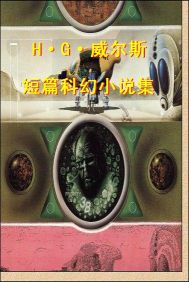乔治·法莱蒂-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遇到红灯,于勒停车等候。一个女人正推着婴儿车横穿过马路。他们右边是个骑黄色自行车的人,他身穿蓝色运动衣,靠在路灯边,两脚踏在踏板上,一只手抓住灯柱维持平衡。他们的四周五彩缤纷,暖意袭人。喧哗的夏天已经抵达露天咖啡座,到达充满人群的街道和生机勃勃的海滨大道,到处都是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别无所求,只想在这个夏天过得快快活活。一切事物各就其位,井井有条,只有这辆等待在鲜血般殷红的红灯前的车是个例外。汽车里充斥一种诡异气氛,它仿佛遮天蔽日,将七彩世界转变为沉郁的黑白阴影。
“法医那里有消息吗?”弗兰克问。
红灯变绿。于勒挂上档,开动汽车。骑自行车的人飞快骑开。海滨大道上汽车鳞次栉比,自行车远比堵塞在交通大流中的汽车要快。
“我们拿到病理分析报告了。他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了解剖。全都证实了。女孩是被溺死的,但是她的肺部没有海水,这说明她没有机会升上海面就死了。要是上下沉浮好几次的话,肺部总会呛进海水。因此,凶手想必是在水中突然袭击她,把她朝下拖,直接淹死了。他们仔细检查了尸体。没有发现任何标记或者痕迹。所有能用的检查设备都使上了。”
“那男的呢?”
“他是另一回事。”于勒脸色阴沉下来,“他被非常尖锐的利器刺中。伤口从上往下。刀刃穿透第5和第6根肋骨,直接刺进心脏。几乎是立即死亡。杀手想必在外面甲板上突然袭击他,那里地上有血迹。他是被突然袭击的,约肯·威尔德个子不矮,虽然不是大高个,但在赛车手中算是高的了。他体格强健。我意思是他经常慢跑、练体操等等。因此,进攻者想必比他更强壮、有力。”
“尸体遭到过奸污吗?”
“没有,”于勒摇头道。“至少男方没有。女尸刚刚进行过性交。阴道里有精液,但可能是威尔德的。DNA测试证明有90%的可能。”
“那就排除了性动机。至少不是一般的性犯罪。”弗兰克评论道,好像在一把大火烧毁房子后发现幸存一张桌布。
“就指纹和其他有机痕迹而言,他们发现了不少。这些都会送去做DNA测试,不过我担心可能会没多大帮助。”
他们穿过波里厄,从海岸上奢侈的旅馆前经过。停车场里闪闪发亮的汽车静静停在树荫中,散发着皮革和石楠的味道。到处都是开满鲜花的灌木丛,晴朗的阳光中一片花团锦簇。一幢别墅花园里开满红色芙蓉,令弗兰克眼前一晕。又是红色。又是鲜血。
“这么说我们什么线索都没有,”他的思绪飘回车里。他拨弄一下空调出风口,让冷风吹到脸上。
“什么都没有。”
“根据脚印做的身材估测呢?”
“没有效果。他大约6英尺高,体重170磅左右。成千上万的人都是这种身材。”
“换句话说,是运动型的。”
“是的,运动型。而且手很灵巧。”
弗兰克脑海中涌起一连串问题。但是他的朋友沉浸在思绪中,弗兰克不想打断他。
“他对尸体干的事并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他技巧高超,显然有过经验。也许他有医学背景……”
“有一定道理。或许值得往这方面试试。”弗兰克不忍把朋友的希望完全打破,“但是这样过于巧合,我的意思是,这是自圆其说。实际上,人体解剖和动物解剖非常近似。我们的朋友只需要在两只兔子上练练,就足够他在人体上实践了。”
“兔子?哈,原来是个养兔爱好者……”
“尼古拉斯,他很聪明。一个疯子,同时又像冰一样冷静。让游艇撞向其他船,自己安然从原路返回。能干出这些事的人,想必头脑清醒,做事有条不紊。他在嘲弄我们,也许还在笑话着我们……”
“你指的是音乐?”
“是的,他最后放的那段是《男欢女爱》的配乐。”
于勒想起他多年前看过勒卢赫的这部电影,那时他和妻子谢琳娜刚刚开始约会。他记得里面的爱情故事,当时觉得它对日后的生活是个好兆头。弗兰克继续说着,他想到一个直到刚才才关注到的细节。
“电影的男主人公是一名赛车手。”
“你一说我也想起来了……身份和约肯·威尔德一样。不过……”
“没错。所以说他不止在收音机上宣布要杀人,而且还说明了要杀的人是谁!我想这还不算完。他一旦开始,肯定还会继续下去。我们必须阻止他。我不知道怎样做,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必须不惜代价做到这点。”
汽车开到加尔诺大道尽头的下坡路,遇到红灯,再度停下。海滨城市尼斯正伸展在他们面前。尼斯是个陈旧、充满尘世气息的城市,与华丽辉煌、住满有钱的退休者的蒙特卡洛截然不同。于勒一边朝马塞那广场开去,一边扭头看看弗兰克。后者正直勾勾地盯着前方,好像凝神等待倾听塞壬【希腊神话中人首鸟身的海妖,以歌声诱惑船只触礁。】歌声的奥德修斯。
11
尼古拉斯·于勒在赫库布里叶街的奥瓦尔警备中心大门前停车。一名笔挺地站在门卫处的警察凑过来,不耐烦地命令他们从警务人员的专用入口处挪开。警察总监从车窗里向他晃了晃警察徽章。
“我是摩纳哥保安局的警察总监于勒。我和警察总监弗罗本约好见面。”
“抱歉,警察总监。我没有认出是您。需要我效劳吗?”
“告诉他我来了,好吗?”
“遵命,长官。您先请进吧。”
“谢谢你,警官。”
于勒又开了几码远,把车停在街边阴凉处。弗兰克下车四处打量。长方形建筑像棋盘上的格子一样排列。每幢楼面对大街一面都有个楼梯入口。
警察总监好奇地揣摩这一切看在一个美国人眼里会是什么感觉。尼斯可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陌生城市,甚至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他固然能理解这里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却不可能溶入它。小房子,小咖啡馆,小人物。这里没有美国梦,也没有可供撞击的摩天大楼,只有小小的梦想,而这些梦想即使真的存在,也每每为海风所腐蚀,宛如这些房子的外墙。小小的梦想,不过一旦被打破,结果也一样痛不可当。
有人在警备中心大楼的墙上贴了张反对全球化的海报。有人为世界平等而抗争,也有人为了不失去身份而抗争。欧洲、美国、中国、亚洲。它们过去只是地图上染了不同色彩的小块,货币兑换比率后面跟的缩写,或者图书馆里字典上查到的名字。现在有了因特网,有了多媒体,也有了直播新闻。各种迹象都说明世界正在扩张或者收缩,至于它们究竟说明世界是在扩张还是在收缩则全由你的观点决定。唯一真正缩短距离的是邪恶。它无处不在。它在各处都持同一种语言,以同样的墨迹写下信息。
弗兰克关上车门,转过身来。于勒看到眼前是一个38岁的男人,黯淡无神的眼睛却像个被生活压垮的老人。晒得黝黑的拉丁面孔,眼睛和头发颜色更深,腮帮上冒出胡茬。一个运动员般身材强悍的男人。一个在警察徽章和正义的保护下杀过人的男人。也许邪恶无药可避,无药可治,然而毕竟还是有弗兰克这样的人存在,他们与邪恶打过交道,却幸免于难。
战争永远不会结束。
于勒锁上车门,看到了谋杀处的警察总监弗罗本。弗罗本也参加了这个案件的调查。他从他们前面那幢小楼的木门里走来。他冲于勒咧嘴一笑,露出又大又整齐的牙齿,映亮了脸上鲜明的五官。他有一副巨大的身躯,把名牌西服的上衣撑得个结结实实。鼻梁折断过,显然练过拳击。弗兰克看到他眉毛周围的细小伤疤,更证实了猜测。
“你好,尼古拉斯,”弗罗本同于勒握了握手。他的嘴咧得更大了,灰色眼睛眯缝起来,眼睛周围的伤疤和皱纹挤成一团。“情况怎样?”
“你说呢?忙得颠三倒四却没有一点头绪。我需要一切帮助。”
“这位是联邦调查局特工弗兰克·奥塔伯,”弗罗本的目光转向弗兰克时,于勒介绍道,“非常特殊的人物,他被派来参加调查。”
弗罗本没有说什么,不过他用目光表明了对弗兰克的钦佩。他伸出一只手指粗大有力的手,坦率的笑容对着他,“我是不值一提的谋杀处警察总监克劳德·弗罗本。”
弗兰克接受弗罗本那夸张的握手礼时,觉得对方如果愿意,随时可以捏碎他的手指。他立即喜欢上这个人。他看起来既强健有力又不失细致。弗兰克觉得他下班后肯定会陪着孩子玩耍,给他们做模型小船之类,以出人意料的耐心做出那些精密的部分。
“关于磁带,有什么新消息吗?”于勒开门见山地问。
“我把它给了克拉沃,他是我们最好的技师。简直像个魔术师。他正用设备分析着它,我刚从他那儿来。来吧,我带你们去看。”
弗罗本带领他们走进刚才他出来的那扇门。他带他们走过短短的走廊,走廊里一扇大窗投进充足的光线。于勒和弗兰克紧跟着弗罗本长着椒盐色头发的后脑勺走,他的脖子短而粗,架在宽阔的肩膀上。弗罗本突然停下脚步。他站在通往左边楼下的台阶前,大手一挥说:“你们先请。”
他们走下两段台阶,走进一间满是电子设备的房间。地下室的光线非常暗淡,幸好屋顶上有几盏日光灯照明。
工作台前坐了个瘦瘦的年轻人。他的头发剃光了,以掩饰秃头。他穿着牛仔裤和白色外套,外套下拖曳出一角格子衬衫,鼻梁上架了副镶黄色镜片的眼镜。三个人站在他那把带滑轮的椅子后面,看他摆弄一个电压计。他转过头来看看他们。于勒好奇他戴着这样的眼镜走进大白天,会不会把眼睛灼瞎。
弗罗本没有给他们做介绍,那人也并不介意。也许他觉得这些陌生人挤到这里,自然有其道理。
“怎么样,克拉沃?关于这盘带子,你有什么发现吗?”
“没多少,总监,”技师耸了耸肩说。“我没有什么好消息。我尽一切可能分析了磁带。什么也没有发现。里面的声音是人工合成的,无法分析。”
“什么意思?”
克拉沃可能意识到并非所有人都像他一样满脑袋科技知识,于是耐心解释起来:“所有人的声音都有一定频率,这可以作为识别每个人的标记之一。声音像指纹和视网膜一样可以加以分析。它们有固定不变的高、低和中声调,哪怕你伪装声音,比如用假声发音,也没办法改变这些声调。我们可以用特殊仪器画出这些频率的曲线,然后用表格形式表现它们。这是很简单的技术。比如录音棚里就会用到它。它们被用来分散频率,以便避免一首曲子里有过多的高或者低声调。”
克拉沃俯身到计算机键盘上,挪动起鼠标。他点击了一些图标,屏幕上打开一个白色背景,上面有一些平行线。另外还有两条锯齿状的线条,一条绿色,另一条紫色,它们交缠在平行线条之间。
“这是蒙特卡洛广播电台主持人让…卢·维第埃的声音,”技师用鼠标点着绿色线条说。“我分析了它,这是它的声谱线。”他又点了点鼠标,屏幕上打开一张图表,深色背景上有一条弯曲的黄线,被一些蓝色平行线间隔着。克拉沃指着屏幕解释,“这些蓝线就是频率,黄线是被分析的声音。不管你从磁带的哪个部分提取维第埃的声音,把它们的声谱重叠,结果都是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