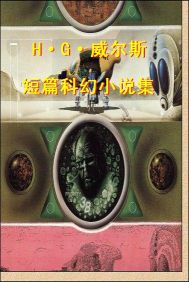乔治·法莱蒂-第4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光火石之间他明白了一切。他知道非人是谁了。
他突然隐隐觉得有脚步声朝他走来。他以为是那个黑衣女人回到儿子的墓地来了。
他心里充满发现的狂喜,心跳得像面鼓一样,所以没有注意脚步走到了他身后,一个声音突然响起:
“恭喜你啊,警察总监。我真没料到你会找到这里。”
警察总监尼古拉斯·于勒慢慢转过身。他看到枪口正对着自己,心想,今天的运气到头了。
44
天还没亮,弗兰克就醒了。他睁开眼睛,又发现自己呆在一张不属于他的床,一个不属于他的房间,一幢不属于他的房子里。不过,这次与以往不同。他回到现实,却不必重复前一天的心情。他转向左边,借着台灯微蓝的光线,端详身边沉睡的海伦娜的身体。毯子半开半掩,他欣赏着她丰满的身体,线条优美的肩膀延伸到流畅的手臂。他侧过身来,像走近陌生人提供的食物的流浪狗一样小心翼翼接近她,直到嗅到她皮肤上自然的芳香。这是他们在一起度过的第二夜。
前一晚,他们回到别墅,几乎有点担忧地离开弗兰克的汽车,好像离开汽车狭小的空间意味着变化,仿佛汽车里创造出的一切一旦暴露到外面的空气中,就会溶解殆尽。他们悄悄走进房子,几乎是偷偷摸摸地,好像他们将要做的事并非他们的权利,而是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
弗兰克诅咒这种病态感觉,以及导致这一切的那个人。他们没有顾得上吃海伦娜提到的食物和酒。这里只有他们俩,自然而然地,他们的衣服突然松动了,滑落到地上。他们有另一种饥渴要满足,它已经被过久地忽略,长期被按捺,以至一旦真的要满足它,他们才发觉这欲望有多强烈。
弗兰克躺回枕头,闭上眼睛,任各种意象在脑海中播放。
门。
走廊。
床。
海伦娜的头发,它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和他的头发纠结,诉说熟悉的语言。
她隐蔽在阴影下的美丽双眼。
弗兰克拥抱她时,她突然之间的受惊表情。
她的声音,她的嘴唇掠过他的时发出的一声低叹。
请不要伤害我,她哀求道。
弗兰克的眼睛因爱而润湿。他曾经徒劳地呼唤这种帮助。海伦娜也同样徒劳地寻找过它。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都狂怒而脆弱地互相寻找,认出了彼此的需要。他尽可能温柔地进入她的身体,渴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神,可以挽回时间,改变事物的进程。他在她的身体里释放自己,意识到是她赋予了他成为神的力量。他们可以一起抹去痛苦,哪怕无法忘却回忆。
回忆……
他自从哈瑞娅特死后,就再也没有和别的女人在一起过。就好像他身体的一部分被抑制了,只执行着基本的生存功能,让他吃、喝、呼吸,像机器人一样在世界上游荡,只不过这机器人是由血肉制成,而不是金属和电子元件。哈瑞娅特的死让他明白,爱是不能任意志命令的。没有人能够强迫自己不再去爱,更没有人能够强迫自己再次去爱。无论意志再强大都无济于事。这全靠机缘,一千年的经验、谈话和诗歌都无法解释它,只能描述它。
海伦娜是命运突然赋予的礼物,是在他成为一棵贫瘠干枯的植物,机械地围绕着照耀不到他的太阳旋转时,给他的一个无声惊喜。她让他发觉,在烤焦的岩石和泥土中,一丛奇迹般的绿草正茂盛繁殖。这并不是回归生命,而是一个小小的、温和的允诺,一个在温柔的希望中成长的可能性,它带来的与其说是幸福,毋宁说是颤抖。
“你醒了吗?”
海伦娜的声音突然传来,打断了他脑海里像新洗出的照片一样播放的回忆。他转脸看着她,看到她在台灯光辉中的轮廓。她正看着他,胳膊肘枕在床上,用手托着头。
“是的。”
他们凑近了些,海伦娜的身体滑进他的怀抱,就像水冲过障碍,滑入河床那么自然。弗兰克再度感觉到海伦娜的皮肤抵着他的身体的奇迹。她把脸贴在他的胸膛上,闻着他的气息。
“你的味道真好闻。弗兰克·奥塔伯。而且你很帅。”
“我当然很帅。我是乔治·克鲁尼的翻版,可惜没人注意到这一点……”
海伦娜的嘴唇吻上了他的。他们再次做爱,带着被欲望唤醒却还昏昏欲睡的懒洋洋的舒适感觉。他们像真正相爱的人那样,忘记了世界的存在。
等他们清醒之后,他们不得不偿还旅程的代价。他们默默躺着,盯着头顶的白色天花板,周围的事物仿佛都在琥珀色光线中流动。这些存在不可能仅仅闭上眼睛就忘记。
弗兰克整天都呆在警察总部,继续对非人的调查。随着时间流逝,他发觉所有的线索都没有结果。他试着保持斗志,集中注意力。他的思绪一直关心着追踪那个写在小纸片上的线索的尼古拉斯·于勒。他也想着海伦娜,她被可恶的勒索所束缚,囚禁在那个可恶的避世又牢不可破的监狱里,尽管门窗都朝世界开放,她却无法走出。
晚上,他回到博索莱依,在花园里找到她,感觉就像是一个朝拜者在漫长艰辛的沙漠旅行之后,终于得到报偿。
弗兰克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内森·帕克从巴黎打来过两次电话。第一次,他谨慎地避开,不过海伦娜拉住他的胳膊,止住了他。这个姿势如此果断,令他暗自吃惊。他听着她和她父亲谈话,大部分都是单音节词,而她的眼睛里充满恐惧,他担心这种表情永远都无法消除。
最后,斯图亚特接了电话,海伦娜和儿子说话时,眼睛亮了起来。弗兰克意识到这么多年,是斯图亚特给了她活下去的力量,给了她一个逃脱的隐蔽场所,让她暗自祈祷总有一天会遇见救星。同样地,他也意识到要赢得她的心,也必定要赢得她儿子的心。这两者缺一不可。弗兰克思忖,面对重重阻碍,不知自己能否成功?
海伦娜举起手,放到他左胸前的伤疤上,一道与周围黝黑色皮肤形成鲜明对比的粉红疤痕。海伦娜感觉得出这是一部分不同的皮肤,是后来新生出来的,好像是套盔甲的一部分。就像所有盔甲一样,它抵御着打击,不过也挡住了温柔的爱抚。
“它疼吗?”她沿着它的轮廓,轻轻用手指碰它。
“现在不了。”
一阵沉默,弗兰克觉得海伦娜是在爱抚他们两人的伤疤,而不止是他的。
我们活着,海伦娜。被打垮、囚禁,但是我们活着。外面传来了即将把我们从废墟中挖掘出去的声音。快点呀,我求求你,快呀。
海伦娜微笑了,房间里仿佛多了一轮太阳。她突然翻了个身,爬到他身上,仿佛刚刚进行了一次小小的征服。她轻轻啃着他的鼻子。
“要是我把它咬下来会怎样?乔治·克鲁尼就比你多了个鼻子了。”
弗兰克用手推开她的脸。海伦娜试着抵抗,但是一下就被迫松开了他的鼻子。弗兰克觉得她的眼睛里充满着人类可能有的所有柔情爱意。
“我担心的是,不管有没有鼻子,要是没有你的话,我的生活都会一团糟……”
海伦娜的脸上掠过阴影,她的灰眼睛里露出仇恨的眼光。她轻轻抓住他的手腕,把他的手从她的脸上拿开。弗兰克明白她眼里流露出的含义,想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
“嗨,出什么事了?我没干那么可怕的事吧?我又没要你嫁给我。”
海伦娜把脸埋在他肩膀上。她的声音告诉他这段短暂、幸福的时光已经过去。
“我已经结婚了,弗兰克。或者至少我过去是结过婚了。”
“你说的过去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政治是怎么回事,弗兰克。完全是装样子而已。所有东西都是假的,所有东西都是装出来的。就像在好莱坞一样,在华盛顿,私底下所有事情都是被容许的,只要不公开。一个有身份的人不能容许女儿未婚先孕的事情发生。”弗兰克静静听着,等待着。海伦娜说话时,温暖的气息抚弄着他的身体。她的声音从他的肩膀上传来,听起来却好像来自一口深井。“哪怕这人是内森·帕克将军也一样。所以,表面上我是兰戴尔·科冈上校的未亡人,他在海湾战争期间死了,在美国留下一个怀着别人孩子的妻子。”
她爬起来一点,看着他的脸。她嘴上带着笑容,却紧张地看着弗兰克的眼睛,仿佛在乞求原谅。弗兰克从来没见过这么痛苦的微笑。海伦娜描述她的困境时,仿佛是在讲述另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她既怜悯又厌恶的女人。
“这个男人只有在结婚那天才见到一次,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直到他变成躺在棺材里的尸体。我成了他的寡妇。别问我父亲是怎样说服他娶我的。我不知道他以什么作为交换,不过我能想象得出。基本上那就是一次代理的婚姻,结婚一段时间作为烟幕,然后就以离婚了事。同时,给他一个升迁,铺条红地毯……你知道可笑的在于什么吗?”弗兰克没有说话,静静听她说下去。他知道可笑的事其实肯定一点也不可笑。“兰戴尔·科冈上校在海湾战争里一枪未发就死了。他在卸载过程中死的,被一枚从架子上松动的“战斧”导弹撞到。历史上最短暂的婚姻之一,嫁的是一个傻瓜,他自以为……”
弗兰克没来得及回答。他仍旧沉浸在对内森·帕克的阴谋和力量的惊愕中。突然桌子上的手机颤动起来。弗兰克趁它还没响,赶快抓起它。他看看时间,正是麻烦该来的时候。他接通电话。
“喂?”
“弗兰克,我是摩莱利。”
依偎着他的海伦娜看到他表情严肃起来。
“摩莱利,怎么了?出事了吗?”
“是的,弗兰克,不过和你想象的不一样。警察总监于勒出了交通事故。”
“什么时候?”
“我们还不知道。法国交警刚刚通知了我们。一个训练猎狗的猎人发现他的汽车倒在普罗旺斯的奥瑞奥尔附近的一道沟里。”
“他情况如何?”
摩莱利的沉默说明了一切。弗兰克内心痛苦地颤抖起来。
不,尼古拉斯,不应该是你,不应该在现在。不应该以这种可恨的方式啊,你的命已经够惨的了。不应该是这样,神婴。
“他死了,弗兰克。”
弗兰克死命咬住牙关,几乎听到牙齿格格作响。他把指关节捏到发白。有那么一会儿,海伦娜担心他会把电话捏碎。
“他妻子知道了吗?”
“不,我还没有告诉她。我想也许你愿意自己去。”
“谢谢你,摩莱利。你做得对。”
“我宁愿不要这个称赞。”
“我知道,我也替谢琳娜·于勒谢谢你。”
海伦娜看着他走向散放着衣服的扶手椅。他穿上衣服。她从床上起来,用毯子裹着身体。弗兰克没有注意到她这个还对裸体不太自在的姿势。
“弗兰克,出什么事了?你要去哪?”
弗兰克看着她,海伦娜看到他脸上的痛苦神情。她默默看着他套上袜子。他的声音从覆盖了不少伤疤的背后传来。
“去世界上最悲惨的地方,海伦娜。我要在半夜叫醒一个女人,去说她的丈夫永远不会回来了。”
45
尼古拉斯·于勒的葬礼上下雨了。老天显然决定中断一下明亮的夏天,让天空倾注雨水,它很像地上的人为于勒淌的眼泪。这是一场不容分说的大雨,就像一位无名的警察总监的生活一样由不得改变。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在小小的任务中耗尽了这一生。现在,他可能已经不知道自己得到了活着的时候唯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