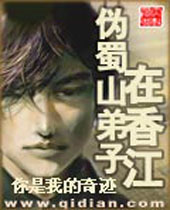香江边上的思考-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考一个问题: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究竟复兴什么?是秦帝国的格局,还是大清帝国的格局?是法家思想主导,还是儒家思想主导?我们究竟需要一种什么样的“中国”?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天下”?中华文明的复兴究竟给人类贡献怎样的生活方式和伦理典范?因此,处理香港问题并不是处理发生在香港的问题,而是处理中华文明复兴中最为核心的问题。一如当年柏克所言:“一个伟大的帝国,一群渺小的心灵,是很不般配的。……我们就应当将自己的心灵,拔擢于崇高的境界,以无负上天命我们接受的委托。”(《美洲三书》,153页)在这里,我们只要把“上天”改称为“祖先”就可以了。二○○三年以来,中央不断调整治港思路,强调要解放思想,但思想的关键不仅在于解放,而要像柏克所说的,“拔擢于崇高的境界”,而这个境界就是全面准确地把握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政治想象力,及其恢复中华文明秩序的崇高境界。
如果我们把香港问题、西藏问题乃至台湾问题放在整个中华文明秩序中来思考,既能想象出它们之间的共同点,也能想象出它们之间应该存在的差异。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出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代共和国领导人在关于“中国”建构上的内在张力,这实际上是贯穿于中国历史上的法家与儒家、郡县与封建以及民族国家与文明中国的内在张力,而且也能够看出他们在“中国”建构上的连续性和继承性。
基本法之谜——香江边上的思考之十
强世功/著 原载《读书》2008年第9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九八二)在香港有效吗?在法理上这似乎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香港既然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岂能在香港无效。但,是这样吗?比如宪法第一条规定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后来修宪增加了“三个代表”的内容,如果说这些内容适用于香港,恐怕香港的资本家在八十年代就已经跑得差不多了。宪法规定我国的政体是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全国人大代表中固然有香港代表,可香港特区并非按照人民代表大会制组织起来的。宪法中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是国家最高审判机关,可香港的案件不能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既然是“两制”,就意味着宪法中规定的社会主义这一制的内容不能适用于香港,但由于是“一国”就意味着宪法中关于国家建构的内容适用于香港,然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从宪法中把“国家”和“社会主义”这两个要素彻底剥离呢。
可见,我们不能笼而统之地说宪法在香港有效(valid )或者无效(ineffective ),更不能说宪法的哪些条款在香港有效,哪些条款在香港无效。因为仅从宪法来看香港,实际上忽略了基本法对中国宪政体制的特殊贡献,看不到“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给中国宪政体制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因此,面对这些纠缠不清的问题,恐怕需要我们从基本法中寻找答案,对这部法律需要重新理解。在香港回归后的“宪政第一案”——马维锟案中,特区上诉法院对基本法有一段生动的描述:基本法不仅是《中英联合声明》这个国际条约的产儿,它也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国内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法。它将载入《中英联合声明》中的基本政策翻译为更为可操作的术语。这些政策的实质就是香港目前的社会、经济和法律制度将会五十年不变。基本法的目的就是要保证这些基本政策的贯彻落实,以及保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继续稳定和繁荣。因此,主权变化之后保持连续性是至关重要的。
基本法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文件。它反映两国之间签订的一个条约。它处理实施不同制度的主权者与自治区的关系。它规定政府不同部门的机关和职能。它宣布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它至少有三个纬度:国际的,国内的和宪法的。人们必须认识到它不是由普通法的法律人所起草的。它是用中文起草的并附带了一个官方的英文本,但发生分歧时中文本优先于英文本。(HKASR v。 Ma Wai…Kwan,CAQL1/1997 )这段文字反映了基本法的特殊性,只不过香港法律界人士普遍强调基本法来源于联合声明,而忽略了基本法来源于宪法及其与宪法的关系;强调基本法是香港特区的宪法,而忽略了基本法也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强调基本法保护香港的经济、社会和法律制度“不变”,而忽略了基本法处理“主权者与自治权的关系”给香港带来的变化。香港回归之后,经济、社会方面的“两制”并行不悖,相互辅助,可在人大释法、二十三条立法以及处理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上却产生了紧张和冲突。
表面上看这是“两制”问题,可实质上是“一国”的建构问题,即要在香港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一国”的要素。由此引申的问题是:难道我们的“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 )依然没有完成?难道我们经历了一九四九年第一次建国之后,还要经历“第二次建国”?如果这是第二次建国,那么基本法就不能只看做香港特区的“小宪法”,而应当看做是国家宪法的一部分。
从法理上说,新中国从来不承认三个不平等条约,香港的主权一直属于中国。宪法作为建构国家主权的法律文件,无疑适用于香港。可事实上,中央政府对香港仅仅拥有“主权权利”,而不具有“主权行使”(参见《香江边上的思考之六》),因此宪法的内容在香港实际上无效。中央对香港恢复主权行使就意味着中央要将“主权权利”转化为“主权行使”,使宪法的内容在香港发挥实际的法律效果。然而,由于中央采取“一国两制”,并通过《基本法》将“一国两制”固定下来,这就意味着基本法对宪法的内容加以有限吸纳和过滤,使其既满足“一国”的要求,同时保证“两制”。因此,基本法就是宪法的补充性法律,基本法的起草过程实际上类似中央(内地人)与香港人补结社会契约的过程,只有在缔结社会契约的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基本法制定过程中的曲折故事。
一九八五年六月,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最初确定香港草委的名额为十八名,后来考虑到代表性,增加到二十三名,在五十九名草委中占40%,而且在每一个专题小组中,都有一名内地草委和一名香港草委负责。正是基于缔结社会契约的需要,香港草委就必须要有“广泛的代表性”,最大限度地体现香港主流社会力量,最大程度地体现香港社会各阶层的代表。考虑到香港当时的实际情况,草委们在总体倾向上“偏中上,中层、基层少一点”。香港媒体称之为“包罗各界精英,照顾各方利益”。“这样的安排,照顾到了香港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代表性比较广泛,可以更好地反映香港各界同胞的意见、要求和愿望,使起草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能够更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彭冲:《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名单(草案)〉的说明》)尽管香港草委具有广泛代表性,但由于这些草委不是选举产生的,缺乏相应的代议基础。为了奠定基本法这个社会契约的政治基础,中央借鉴港英政府建立咨询委员的“行政吸纳政治”模式,成立了“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作为代表香港市民向基本法草委提供参考意见的咨询组织,从而增加香港人民参与订立基本法这个社会契约的机会。为了增加各界别的代表性,原定八十名的咨询委员会最后扩大到一百八十人,成为包括工商界、金融地产界、法律界、专业人士、传播媒介、基层团体、宗教以及部分草委和旅英侨领。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组建大大地刺激了香港社会的政治热情,中产专业界的政治热情急剧高涨,43各种团体、组织纷纷产生,基本法制定的过程奠定了大众民主参与基本法的正当性。
正因为如此,基本法的制定过程看起来像制宪会议,更像内地草委与香港草委之间“有限度”的对等谈判,之所以说是“有限度”,就是谈判的内容已经确定了,即联合声明中刊载的中央对港方针政策,而在谈判形式上,中央都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因此它又体现出全国人大制定法律的特征。正因为如此,基本法起草的程序就变得很重要,中央提出采取民主协商,可有香港草委反对,认为协商不明确,不科学,而主张采取程序正义的投票表决方式。可是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内地与香港在思维方式上有很大差异,而香港内部各阶层也缺乏互信,采取投票表决的程序主义只能导致政治分化,形成多数压迫少数,无法达成共识。为此,中央坚持采取民主协商、求同存异的方式凝聚社会共识。而这个凝聚共识的过程实际上也是香港社会接受中央对港方针政策的过程。
经过讨论,民主协商原则获得大多数草委的赞成,连咨委会也主张采取“民主协商,兼容并蓄,求同存异,不强求一致,不采取表决方式。”这种协商政治要求内地草委更多地倾听并采纳香港草委的意见,有利于保护少数,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实现双赢。因此,邓小平提出起草基本法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宜粗不宜细”。
基本法既然是中央(内地)与香港之间重订社会契约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央与香港特区关系法”。中央与特区关系自然是争议的焦点,但香港政治体制之所以引发巨大争议,实际上也是因为涉及中央与特区的关系。比如,香港政治体制中最大的分歧就是采取“立法主导”,还是“行政主导”。立法主导模式类似于内阁制,将政治权力的中心放在立法会,特区政府由立法会产生并向立法会负责。行政主导模式类似于总统制,赋予行政长官更大的权力,行政长官不是由立法会产生,也不向立法会负责。“民主派”主张采取立法主导模式,因此主张规定政党政治,这样政党通过获得立法会多数席位而推出行政44长官进行组阁。大家都很清楚,在香港特定的民情下,主张与中央对抗的“民主派”更容易通过普选掌握香港的政权。这样的政治模式必然影响中央与特区关系,影响到“一国”的建构。由于政党政治涉及到中央与特区关系的根本,基本法草委会政制小组罕见地以表决形式否定了该提议。
在基本法起草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陆政治民主化讨论也如火如荼,民主普选,三权分立学说尘嚣云上。本来《联合声明》中只规定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由选举产生,并没有规定普选产生。可在这种政治氛围中,普选概念很容易引入基本法。在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北京举行的基本法草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委员们尽管在具体政体方案上相争不下,但都同意把“三权分立”作为香港政体模式。就在这时,作为“一国两制”的掌舵人,邓小平从全球战略高度敏锐地意识到自由化思潮席卷香港、东欧、苏联和中国内地的国际大气候。对内地而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依附于西方的统治,其结果只能将中国引入内乱,丧失了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大好时机。因此,邓小平在一九八六年中央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