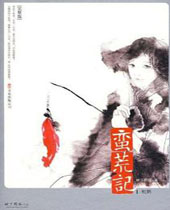碧檀记-第5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谭央逃也似的离开了那座公馆,回去的路上她忽然想到,于他而言,他又是如何带着女儿继续生活在他们福煦路的家。诚然,他比她坚强,可是坚强就代表不难过不痛心吗?
那漫长的人生路,他们将如何独自生活下去,活在那余下的岁月中……
之后谭央还去了个做木器的小店,她叫小老板做了个碧檀木的小匣子。她把匣子拿回家,取出洋行的存款单子,将单子牢牢地锁在了匣子里。
明晃晃的灯光下谭央伏在桌子上看着匣子盖上刻出的苦难佛,那一刻,她忽然明白了父亲三十年前的心境,明白了父亲总是对她说的那句“欲望满则灾祸至”。如果没有这样一笔巨大的不义之财,那么三十年前他们兄弟不会反目,三十年后他们夫妇不会离散。他们没有谁用到了这笔钱,可是这笔钱却将他们害得面目全非了。谭央摸了摸苦难佛脸上慈悲的笑,长长的叹了口气。
谭央去了几次福煦路的毕公馆,她想见女儿,却屡屡碰壁,甚至于她鼓足勇气想去找毕庆堂理论,毕庆堂也避而不见。谭央还是了解毕庆堂的,明白他手里握着最后这张王牌是不会轻易撒手的,谭央心中便有了愤恨,恨他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就连爱情婚姻,妻子女儿都能计算其中。
谭央静下心来,一些想法也渐渐明晰了,他惯于如此狠毒冷酷的行事,如今他们不为这些事,终有一日也会为了旁的事分开,他们终究,不是一样的人。
毕庆堂在谭央离开的巨大失落与气馁中紧紧的握着女儿,他还有一丝希望,也许贫苦艰难的生活不能打败谭央,女儿却能。他以为谭央爱囡囡,挟着女儿,或许谭央便有思女情切低头回归的一天。她回来,哪管是与他貌合神离的过日子,他加倍待她好,她终会有回转过来的时候。不知他是犯了糊涂,还是相识十载他还是不了解谭央。他的偏执无法挽回他们的婚姻,却将他心爱的人,他那琴心剑胆、宁折不弯的小妹,越推越远。
谭央在相见无望的落寞中惦记着女儿,这同她在德国读书时又不一样,那时几个月不见却知分离是短暂的,以后还要天长日久的在一起。如今半个月不见,可她却知道,以后母女俩相见的机会越发的渺茫了。
谭央不敢继续思念女儿,沉溺于无望的思念是殊危险的事,她必须找些事情做,她想起马院长的建议,恐怕,她是要开一家小医院吧,人总要有些事情做的,特别是悲伤中的人。
作者有话要说:时间过得好快,和上一章的更新隔了那么久,我的小孩都快周岁了。偶尔抽空看看我这篇文章,竟然一直有人留言,前些天看纸醉的留言更是叫我下定决心一定要给这篇文章一个结局,而且一定要好好写,这样对自己负责,更是回报那么执着追文的姐妹们!滥情的亲一亲诸位,好久不见,很想大家!
57(55)新朋
两天后;谭央依着马副院长给的地址;去找那对日本留洋回来的医生夫妇;先生姓吴单名一个恩字;太太叫林稚菊。去之前谭央特意找出一件深色的旗袍穿上;显得庄重些;更是怕人家夫妇因她年纪轻,轻看了她。
下午两三点钟的弄堂里带着昏昏欲睡的疲乏;二楼的小窗子搭出的竹竿上密密匝匝排开了各种颜色的衣服,阳光透过晾衣服的缝隙挤进来,比这窄窄的弄堂更叫人觉得局促拥挤。
小夫妻俩租了一个亭子间住,谭央踩着高跟鞋走上颤悠悠的木楼梯,不用敲门就看见门敞开着;里面堆着用布打好的包裹,一个四五十岁的妇人用上海话指着面前的樟木箱子挑剔来挑剔去,妇人对面站着一个年轻女人,穿着棉布旗袍,抱着肩膀,用苏北话干脆利落的回击着,她身后站了个高高瘦瘦的男人,垂头丧气的看着地面。
谭央见她们交涉得甚是投入,没人看到她,便轻轻敲了敲门板,三个人转过头来望向她,她礼貌的笑了笑,“我姓谭,叫谭央,不知这是不是吴恩吴医生家,有事情找吴医生和太太帮忙。”就看那对年轻的夫妇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妻子刚要往门口走却被那妇人拽住,嚷着,“喔呦,阿拉买哦!”
丈夫见了只得自己走到谭央面前,匆匆扫了谭央一眼,随即又低下头,“在下是吴恩,前两天马院长说起您。没想到,谭医生您这么年轻。”谭央听了,颇有些气馁,做女人的忌讳别人说她老,可是做医生的却又偏偏怕人说她年轻。吴恩也不等谭央接话,又自顾自的接着说,“谭医生,我们怕是不能去你的医院了,昨天接到家信,家父过世了,我们要回安徽老家,”顿了顿,他又说,“回去就不打算回来了。”
谭央没想到自己还没开口就被拒绝的这样干脆,她刚要说些吴医生节哀这样的话,吴恩却被叫过去帮忙抬樟木箱子了。吴恩弯下腰时,裤腿下面就露出了他掉了帮的旧皮鞋。谭央想自己在这里也给他们夫妇添乱,索性就回去吧。可回过身,一打眼就望见门旁边那口见了底的米缸了。
家里竟然没米,还要去卖随身的家什,看这对夫妇的落魄模样,她便觉心中不忍了。谭央本就随她父亲,很有些古道热肠的侠气,又刚刚落魄过,懂得衣食无着的凄苦,她取出手包里的钱尽数塞进了米缸里,这才匆匆离开。
走到巷口谭央忽然想起了,竟然没给自己留些坐车的钱,可是回头取,又不像话了。她暗暗自嘲,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自己惯于做这种傻事,譬如当初在外滩,用所有的钱买了报童手里的报纸。她是远没有表面上看来的那样温和沉静,内里的冲动热诚她自己最清楚。就好像毕庆堂每每调侃她说她是个烈性子的好汉,惯于披着一张画皮来哄人。
不经意间,又想起了他,谭央叹了口气,这口气是心中的苦涩,随着哀怨逃将出来,肆无忌惮的弥散在她周围。
因为离家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谭央也不急,一个人不紧不慢的沿着大道走,走了一段后听见有人在后面大声的喊她的名字,回过头,竟看见林稚菊一路小跑的追过来,跑到谭央跟前,林稚菊一手扶着腰上气不接下气的喘着,一手举起一打钱,“谭小姐,你的?”
谭央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字斟句酌的怕伤了林稚菊的自尊,知识分子的尊严是最要命的东西,她自己是这样,便更能推己及人,“嗯,我看吴先生家里出了事,你们回安徽山高路远的,可能会用到,这,我可能鲁莽了。”林稚菊看到谭央一副做了错事被抓现形的样子,本来紧张局促的气氛也和缓了下来,笑道,“谭小姐,您没鲁莽,我们很需要钱呢,但我们不能白白拿您的钱,就当预支薪酬行吗?”
“真的吗?吴先生吴太太愿意?”谭央抬起头笑着问林稚菊,因为意外的好消息,眼角眉梢的欣悦让她整个人都跟着明媚起来了,很美,美中包含着温柔善意,林稚菊立时便喜欢上了眼前的这位年纪轻轻的小院长,“愿意,哪里去找你这样慷慨的院长,但你要给我们一个月时间,处理处理家里的事。”
谭央听了连连点头,“好,正好我也有时间去筹备医院!”林稚菊略想了想后又笑问,“不知谭院长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吗?”对于这个陌生的称呼,谭央有点儿不自在的把手包换到另一个手,一本正经的说,“有!”林稚菊认认真真的听,谭央接着说,“你给我点儿钱,我要叫辆黄包车回去,忘了给自己留钱了!”
说罢,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的愣了几秒,随即不约而同的相视一笑,黄昏的大道上,她们笑得像一对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副莫逆于心的样子。
有些人相识几十年还是白头如新,有些人初次相见却能倾盖如故,其实友情和爱情一样,也要靠眼缘。也可以说,但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大同小异的,是不是吸引你,会不会气味相投,三五句话就了然于心了,用不着那么多的揣测琢磨、历练考验。
林稚菊与谭央携着手去找黄包车,谭央上车后,林稚菊忽然拽住她问,“你是学小儿科的对吧,那你开的医院有没有外科医生?”谭央摇头,“还没,也许要登报纸找个。”林稚菊高兴的说,“不用不用,我们有位师兄,医术高明的很,就是性子古怪极了,在哪里都做不久,你干脆把他找来,只要有个地方叫他做医生,你给他多少钱都不打紧!”
一个医生能盛赞另一个和自己同辈的医生医术高明,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这个医生的心胸是开阔的,第二,这位被称赞的医生的医术也是真的高明很多。谭央懂得这个道理,开心的应承,“那自然好!我什么时候去找他?”“哎,你自己别去了,他那个人肯定会叫你碰钉子的,等我们从老家回来,我和老吴带你去!”
谭央被黄包车拉着走了一段了,回过头还看见林稚菊站在夕阳里笑着冲她挥手,谭央心里竟觉出了温暖,她想起了章湘凝,东吴大学毕业后为了逃避家里安排的婚事,她跑去英国读书,读了硕士读博士,还威胁她父亲,若是不解除婚约她便不回来了。英国很远,她与谭央的联系也就是几封稀稀疏疏的信件,此时此刻,谭央倒真是很想念她。
谭央在报纸上看到有个卖洋房的,出奇的便宜,她随房主去看了看,三层的小楼,算不上旧,地点也好,闹中取静的,正是做医院的好位置。谭央看周围也有不少寓所,住的全是受过西洋教育,有几个小钱却称不上财大气粗的洋行职员,正是能光顾她们这种小医院的人。谭央总听毕庆堂给她念叨些生意经,所以这一点儿眼光还是有的。所以说,这女人的第一个男人啊,甭管是好是坏,都影响你一生的眼界和品位,马虎不得。
房主要价很低又急着出手,谭央算了算,正好手头同里的租子够了,两个人就约好第二天交钱过挈。谭央往回走的时候一个坐在路边拉活的车夫还好心好意的提醒谭央,这是凶宅,死过母子俩,没有人愿意买的。谭央倒是如释重负的笑了,“我买房子是唯独不怕这个的,多亏你告诉我,不然房子卖得那么便宜,我还怕被骗了呢!”
之后谭央就找人清洁粉刷房子,还去采买桌椅,诊床,屏风,又忙不迭的去卫生学校聘了两个刚毕业的女孩子做护士。
谭央就这样脚不着地的忙着,她不敢停,停下会想女儿,也会想起毕庆堂,想起他们之间的恩爱和仇怨,一段感情即便只存在你生命中的一小段,它也会永远停留在你的记忆中,更何况还是带着刻骨的爱的一桩美好婚姻。
方雅不知在毕庆堂那里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这一日火急火燎的来找谭央,倒像是来救火的,又正义又本事。还摆出了一副长辈的架势,要调停谭央和毕庆堂之间的矛盾。谭央并没有说她和毕庆堂之间的种种仇怨,可是那语气、那神态却叫方雅的心凉了。方雅是个何等聪明的女人,于男女之间□上尤其通透的很,她看出这对夫妻重归于好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了。
谭央坐在沙发的一角,低着头,抹着眼泪,那绝望无助的模样叫方雅也心头酸楚,她抚着谭央的肩轻声劝着,“若是真不能再回去了,那就硬气些,难过也是没有用的,你便当他死了,还没来得及做伤你心的事就先死了!”谭央听了微微点头,拿手帕擦了擦眼角的泪,又哽咽道,“可他还不叫我见女儿,方雅姐,我想囡囡啊!”
方雅听罢站起身恼怒道,“这个庆堂,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