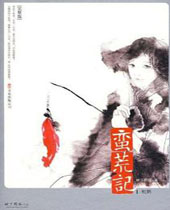锦荷记-第3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世事无常,斗转星移。命运究竟会把他们两人带向哪里?
作者有话要说:亲爱的童鞋们,偶又在吹牛了 … 目前还没有治愈乙型肝炎的抗体 (为了显得靖平厉害,又不能侵犯前人的专利,偶就被迫发挥想象力,撒谎吹牛了,大家表见怪。)
大家能看出来云深的家族危机和问题四伏,她置身这样的环境里,称不上太幸福,而且今后的一些坎坷纠葛也跟她的家族和身份脱不了干系,所以云深的公主身份带给她的痛苦会多于幸福。
另外,聪明的童鞋们,大家也能看出来,云深的情敌就要登场了。
巴尔蒂莫的重逢(靖平)
上一次见Rubinstein 教授是三年前,我和他一同在大阪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当时会后我去给云深买礼物时,他还笑我变成了孩子王。以后虽然常有电话和邮件的联络,却始终没有再见。
然而时隔三年后的再次相见却并没有让我感到喜悦,因为这次的会面地点是在霍普金斯医学院的Sidney Kimmel癌症中心 … 他的病房里。
他被却确诊为肝癌,刚做了手术。
我得到消息后,立即从斯德哥尔摩赶了过来。见他之前,我询问了他的主治医生,得到的回答是 – 他所剩的时间只有一年到一年半。
我生命里又一个重要的人要离开了。岁月究竟还给我留下多少情感是可以把握的?
走进Rubinstein 教授的病房时,一位年约六旬的妇人正坐在他床前。
Rubinstein 教授看到我,高兴地大声说:“我的伙计来了!”他明显地消瘦,原先一头浓密粗硬的头发因为化疗已经脱光,但一双眼睛却如旧时一样矍铄有神。
他为我介绍了那位妇人,说是多年的老朋友。我们寒暄几句后,她就匆匆告辞。于是病房里剩下我们两人。
“你没给我带酒来?他们现在不让我碰酒,连注射时的消毒酒精都省掉,怕我拿去喝了。”他对我眨眨眼。
“我没这个胆。”我故作轻松地对他笑。
“没交情!没有我当年把你从一个小菜鸟提拔成我的研究助理,你今天能当上瑞典人的院长,还跟霍普金斯学院对着干吗?”他故意瞪眼。
“对,我有今天全靠了你。你教出我这样一个霍普金斯的叛徒,他们不让你喝酒也是该的。你现在住的可是霍普金斯的内部医院。”
“听着小子,别光顾着看我的笑话。你得快点在瑞典干些名堂出来给我瞧瞧,我的时间可不多了。”他一派轻松无谓地玩笑着。
我心里一抽,赶紧转开话题调侃他:“方才那位女士只是朋友吗?我看不止吧。”
他笑笑:“她是我年轻时的恋人。”
我突然觉得我触到了一个此时并不恰当的话题。
他却不以为然:“想听故事吗,靖平?”
我有些歉意地注视着他,预感到这不会是一个轻松的故事。
“我那时还年轻,也还没什么成就。她是我的恋人,也是我唯一爱过,而且现在还爱着的女人。我当时认为自己要么会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工作狂,要么会是一个一文不名的窝囊废。而这两种人都不会让她幸福。于是我替我们两人做了决定,把她让给了一个我和她共同的朋友,一个家道殷实,又英俊体贴的老好人。后来他们就结了婚,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最近刚当了爷爷奶奶。我以为这么多年以来,我成就了她的幸福。可刚才她告诉我,那不是她想要的。多么可笑,我自以为伟大的自我牺牲,换来的居然是我和她的遗憾。”他脸上是我从未见过的自嘲和失落。
“但你的初衷是好的。”我安慰着他,但却仿佛像在安慰自己。我对云深的安排终是为她好,虽然当时看来是违背了她的意愿。
“靖平,你和我在事业上都是极自信的人。干我们这行的,要的就是极强的自信坚持和冷静理性,否则顶不住他人的异议和瓶颈时期的自我怀疑,出不了成就。但感情,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不要用理智去分析感情,不要替对方作决定。要跟随自己的心,而不是大脑。”他目光熠熠地注视着我,这话显然是专门说给我听的。
我苦笑一下:“老爷子,你到底想说什么?”
他有些粗鲁地回答:“别跟我装傻,说什么自从你的疏影死了以后你就不会爱了的屁话!别看那些狗仔报纸一天到晚在猜你是不是性冷淡,我可知道你心里现在有人。跟你师徒这么多年,又一起熬了这么多夜,你在爱一个人的时候,眼睛里会有什么样的神情,我清楚。”
我在爱她吗?我能爱她吗?
沉默半晌,我开口:“我和她之间隔着太多东西,年龄,舆论,伦理。她身份不一般,我必须要考虑她因此可能会承受的压力。”
“那些都是狗屎!” Rubinstein皱着眉头开始发咆:“只要她也爱你,就再没有什么东西能隔在你们之间了。”
我回答:“问题就在于她年龄还太小,并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男女之爱。”
Rubinstein看我半天,叹了一口气:“明白了,是你那个小外甥女,对不对?”
我一惊,望他一眼,然后默不作声。
“爱个自己看着长大的孩子让你感觉罪恶,是吗?” 他的眼睛似乎能看穿我。
“是的。” 我沉默片刻后答道。
“你对她做过过份的事?”
我想起西安雨夜的那个吻,苦笑一下,摇摇头。
“那你还罪恶个什么劲儿?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瞻前顾后婆婆妈妈的?真是见了活鬼!” Rubinstein皱着眉低咆着。
他拧着已经没有眉毛的眉头看我一会儿,然后闭目叹了一声:“靖平,你在害怕吗?怕经历过的痛苦再发生一次。”
我心里一震,抬头直直看他。
“疏影去世的时候,当时的你就像变了一个人。连我看着都害怕,以为保不住你了。你这么强的人能变成那样,那种折磨,我想象得出来。”
“靖平,坐过来。” Rubinstein轻轻拍拍他的病床。我依言坐在床沿上。
他看我半晌,枯瘦的手伸过来,握住了我的:“听我说,儿子。你是我接触过的人里脑子最聪明,胆子最大的一个。但是现在你反而犹豫,是因为你太在乎。越是替对方想得太多,反而忽略了爱情本身。爱情是这世上最没逻辑和理性的东西,它会发生在任何阶层,年龄,甚至性别之间。当它出现时,即便是一个孩子也能凭直觉知道,那就是爱情。爱情也挺简单,你爱一个人,愿意为她承受痛苦,认为值得。但你爱的那个人也是同样这么想的。因为对她来说,最大的幸福就是和你相爱,而不是你为她所设计的一场完美的但却没有爱情的幸福。生命很短,难道你非得要等到她也得了什么绝症再爱吗?”
作者有话要说:Rubinstein教授跟靖平很有父子缘,上辈子估计是靖平他爹。
偶很喜欢这个老爷子,但是不得不不牺牲他的生命来给靖平敲警钟 … 生命苦短,及时行乐咯。(但是千万表学倪震喔。:D)
彩虹(靖平)
我这次来巴尔蒂莫只为探病,除了Rubinstein和他的主治医生再无旁人知道。我尽量小心,但还是被医院的人认了出来,通知了学院。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坚决推掉了霍普金斯学院要为我举行欢迎宴会的提议,也拒绝了当地报刊和电台的采访要求,只应邀为医科和商学院的学生做了两个讲座,而剩下所有的时间,我都待在Rubinstein的病房里帮他坐卧饮食,陪他聊天闲谈。
如同以往一样,我们聊专业,政治,球赛,音乐,电影,而感情的事却是不再提了。
那位Rubinstein从前的恋人时常来看望他。每次她来时,我都知趣地离开。他们之间能独处的时间怕是已无多。
临走的那天上午,我站在Rubinstein床前,伸手展平他被角上的褶皱,朝他轻松地一笑:“过几个月我要去纽约办事,到时候咱们再好好聚聚。要不你好些了就到北京来看看我的实验室?”
他专注地看着我,目光深邃温和。然后静静一笑,说了一句当年安慰做不出试验的我时用过的话:“你会做得好的。”
他是指我的事业,还是爱情?
从他病房出来以后,司机载着我,从医院驶往机场。
昨晚被几个昔日同窗拉到我们读书时常去的一家sports bar里看球喝酒,闹了一晚上。一贯节制的我居然有些醉了,到现在还有些隐隐的脑涨。
我让司机把车停在路边的计时器旁,让他在那里等我半小时,然后下车朝市中心步行,想要透透气,也再看一看这座我久违了的城市。
巴尔蒂莫,一座奇怪的城市。它拥有霍普金斯这样举世闻名的学府,却也存在着全美最多的城市贫民和最高的犯罪率。它破旧,脏乱,但又充满生机。我在这里居住了七年,但仍读不懂它。
我慢慢步行至主干道时,发现街道上设了横木,不让车辆通行。原来今天碰巧是一年一度的同性恋大游行,熙熙攘攘的观众们已拥簇在街边,翘首企盼。
我往前走了一段,找到一家小咖啡店,要了一杯espresso,坐在二楼露台的的咖啡桌旁,正好面对着游行队伍要经过的街道。
九月的巴尔蒂莫,阴沉潮湿。刚下过一场小雨,太阳还藏在云层背后,原本就不太光鲜的街道和建筑更显得阴晦陈旧。
但这些许的沉郁很快被一阵欢快的乐声打破。一只装扮得五彩鲜艳的游行队伍出现在远处,并顺着街道慢慢前行。
队伍中有男有女,有同性恋,也有他们的支持者。他们丝毫未受这令人心情沮丧的天气的影响,挥动着绘有彩虹的旗帜,涂着厚重的化妆,穿着亮丽怪异的服饰,奏着乐,骑着摩托,且走且舞着,不时地向围观的人群飞吻,或者散发糖果和小玩具。
一个年轻女子抱着一个头戴彩虹帽的两三岁小男孩儿。孩子乐呵呵地抓着一只大气球,上面写着“我爱我的同性恋婶婶Sherry”。
一个化装成女子的高大男人推着一辆轮椅,里面坐着一位瘦小的老妇人。她手里举着一个横幅,上面写着“基督徒母亲支持她的同性恋儿子”。她布满皱纹的脸上一派平静温和的笑容。在基督徒眼中,同性恋是罪恶的,该下地狱。想必这位母亲初闻自己儿子异于常人的取向时,也是无法接受的。从当初的震惊心伤到如今大方微笑地和儿子一起游行,她经历了多少痛苦挣扎?那历经岁月沧桑的瘦弱外表下该有一颗怎样勇敢坚强的心?
“嗨,帅哥!”有人在楼下叫我。
我从坐着的露台上探出头去,只见一个化装成马戏团小丑的男人在向我招手,见我看到了他,便将手中一个小包朝我抛上来。
我接稳了一看,小包放着一只避孕套和一本安全□的小册子。
“谢谢,我会记住的。”我笑着朝他挥挥手。
他咧开画得夸张的大嘴,对我笑着眨眨眼睛:“安全第一!”然后快乐地朝前蹦跶着,继续分发他手里的小包。
在这个对同性恋并不友好的城市里,他们勇敢地,甚至是有些嚣张地展示着他们不为多数人所认同的情感。
他们在跟随自己的心。
我呢?我清楚自己的心吗?
你真的是作为一个长辈在爱她吗?
为什么从看她第一眼,你就不停告诫自己你是她的舅舅?难道从那一刻起,你潜意识里就知道你对她有超乎伦理辈分的感情?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你一直戴着她幼时送你的那枚玉观音,连洗澡时都不曾解下来?只是因为不忍拂了一个孩子的好意吗?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