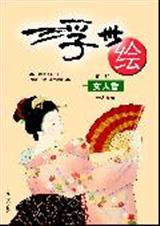皇的女人:失踪的新婚宠妃-第13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我也跟小景一道,喊你阿卿好了。”裴玉白举杯而笑。
青璃各自看了他二人一眼,唇边的笑容略有沉重,拂袖仰头,喝下杯中美酒。
……
酒入愁肠烧,相思愁更愁。
一杯酒下肚,脑海中,又浮现出方才被打断的回忆……
那日,她体内的毒发作,七孔流血,临死之际却听得山涧中响起嘹亮笛子声。
雨后的山涧云雾缭绕,她听见马蹄声,恍恍惚惚见有一老一小朝她而来。
……
“咦,师叔公,这儿躺着个死人啊……”
“七窍流血,中毒不浅,啧啧,惨呐……”
“师叔公,走吧走吧,这一趟出来半月,再不回去师傅还不定怎么罚我……”
“等等……”
“师叔公,您又要多管闲事……”
“怎么是多管闲事,你这臭小子,你没看到这姑娘她拉住了我的裤管不让走!”
“啊,她没死?不过也活不了多久,反正横竖是要死的,师叔公,不如给她个痛快。”
“啐!混小子,亏得你还是学医的!没良心的小混蛋!”
“师叔公你也不见得多有良心,你八成还不是,还不是想看她中的什么毒……”
“嘿嘿,这都被你看穿了……”
☆、
耳旁的交谈声传到她耳中,她攀住那老叟的裤脚,“前辈,救救我……”
老叟蹲下来,把她从头到尾打量了一番,“怪,真是怪,这女娃娃怎地有几分面熟?”
“救救我……”
“也好,你我也算有缘,不过,要我老头子救你也成,你得答应我一个事!”
“好……”只要能活,什么都愿意。
“嘿,女娃娃,我老头子要是救活了你,你可就得一辈子当我徒弟咯!”
再醒来,她却置身在满山满谷都开着紫迭花的山谷里。
原来真的有四季常开的紫迭花,真的有紫情谷!
后来才知道,那老叟居然会是治好慕言眼疾的那个高句丽太医!
不,如今,她该唤老叟一声师傅了。
更想不到,她会在紫情谷,再看到翘儿!
……
唐景的大嗓门又一次拉回她的思绪,“诶?阿卿,你怎么哭了?”唐景纳闷。
“没。”青璃又递出杯子斟酒,“来,喝酒。”
裴玉白细心的望了她一眼,淡淡一笑,并未道破她的谎言。
唐景又嘻笑着嚷开了,菜已上了桌,三人把酒言谈,吃得很畅。
……
朝歌的夜降临,正是三月梨花白惢的季节,雾色寒露,客栈外的街道上喧哗正盛。
青璃躺在床上,看着窗外树梢间一轮清冷的缺月,静静的想着。
她在紫情谷呆了整整五年多,一步都不得出谷。
这次能出来,乃是过了师傅的三道难题,才得以出得谷来。
五年的谷中生涯,上千个日夜的心灵煎熬。
是恨是痛,也是爱,支撑着她一步一步艰辛的熬下来。
这一场姐妹恩怨未了,她知道自己无法回到南诏,无法回到凤倾夜的身边。
当年是她将她们带出来,就让这恨,在她手中了解。
若要让辛姝偿还这段孽债,她便需替慕言先行解开身上的情蛊之毒。
否则辛姝一旦死,慕言受情蛊纠缠,唯有以死殉情。
东商太医院每年三月都要举行一次会考,各地举荐而来的学子若能通过太医院的考试,就能入太医院为医。师傅说,情蛊乃是百蛊之王,从来无解开之法,就是下蛊的人也没有办法解开。但翘儿的丈夫紫蠡说,这情蛊之毒,并非没有解开之法。但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也许几个月,也许半载,也许要一年两年。
☆、相思血泪(1)
回想往事种种,青璃只觉得心中疲惫,人渐渐的睡了去。
街道外的喧哗褪尽,响起三道更漏声,昏昏沉沉中闻得耳旁有呼噜呼噜的鼾睡声,青璃警觉,手中银针毕现,人已翻坐而起。“谁!”没有人回答,但借着窗外月光,她一眼看见地上睡着一个人,正睡得香甜。青璃披上一件衣裳下了床,脚踢了踢唐景,“醒醒!”
唐景睡得很沉,鼻端里打着鼾声,抱着薄薄的被子满足的蜷缩在地上,青璃望一眼门口,看来唐景是用刀把门栓挑开了,而她居然没有半点察觉,想到这,青璃心中微微一凉,就蹲下来,手里银针刺下,唐景哎哟一声跳起来,“有虫子!有虫子!”
“虫子没有,贼却有一个。”青璃盯着唐景。
“嘿嘿,哪里有贼呢,要真有贼,那我更不能走了,得保护你不是!”唐景挠了挠头,嘿嘿一笑,“阿卿,你看你这间房这么大,就借我一角地方睡上一宿,就一宿!我连考了三年,要是今年还不能进太医院,我就只好三尺白绫自行了断了,你忍心看我死吗!阿卿!阿卿!”唐景死皮赖脸的抓住青璃的手不放,装起可怜来。
“小景,我还在想你半夜是否梦游了,原来是跑到阿卿的房间来了。”这时候隔壁房的裴玉白闻了动静也过来看看。
“玉白兄来得正好,把他领回去。”青璃从唐景手里拉出衣袖。
“小景,这夜凉,被褥单薄,你睡地上岂不知是要生病的?”裴玉白好心道。
“诶?是有点,大好人,不如你把你的被子都拿来,咱今晚就一起睡阿卿的房间,我们两个睡地上,彼此取暖,这不就好了!”唐景摸着下巴,一脸的顽皮坏笑。一副打死也不出三号房的架势!
青璃冷淡如风的看着唐景。
谁知裴玉白淡笑:“那……好吧。”
“慢。”青璃各自盯了他们一眼,“我睡隔壁房。”
裴玉白不紧不慢的道:“哦,阿卿,我的房间,还有两个仆从。”
“……”青璃捏了捏手里的银针。“我换房。”
☆、相思血泪(2)
唐景拍了拍裴玉白的胸:“大好人,好像咱们晚饭的时候,就听掌柜的说房间已经满了?”
裴玉白点点头:“嗯,大多是明日赴考的子弟。”
两人说完,就盯着青璃阴沉的脸无辜的望着。
……
青璃坐在床上,看着裴玉白让仆从把被褥抱过来,他两个大男人就睡在了她房间的地上,唐景长腿长手的一捞,就满足的抱着裴玉白取暖,继续他香甜的酣梦。青璃摇摇头,放下帐幔躺回床上。罢了,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况她现在的样子,绝无人会怀疑她原是个女子,也就不必担心被人轻薄。出紫情谷之前,她已易容成男子,又喝了变声的药。因她本身骨架清瘦,皮肤白皙,而易容的面皮需要紧附她原本的骨架,又需贴合原本的肤色,于是这一张易容后的‘男子’容貌也就生得俊俏清朗,如玉净白了。不过再如何俊俏,她此时此刻,在外人看来也都是个十足的男子。除了被裹住的胸部和身体。
清早的晨雾从窗户透了进来,黎明的阳光通亮照进来。
青璃仆一睁开眼,就见面前有两张放大的脸。
“阿卿,一个大男人,做噩梦就做噩梦,你怎么还哭了?”唐景说完还伸手在青璃脸上抹了一滴泪。“你还真是个奇奇怪怪的人!”
“阿卿,你昨天夜里一直在喊些什么?”裴玉白蹙着眉头也在打量。
青璃从容于床上坐起,“喊什么?”望了一眼裴玉白。
裴玉白蹙眉纠结道:“倾什么夜什么,倒没听得仔细,想来是你紧张今天的考试,所以做噩梦了?”
“嗯。”青璃道:“天明了,你们该回房洗簌,用完早饭,我们就该上太医院赴考了。”
裴玉白和唐景这才抱起被褥,回到隔壁四号房换衣洗簌。
青璃从怀中掏出那缕青丝,眼眸瞬间涌出痴痴的思念,“倾夜,等着我。”
清晨里的风,带着一丝露水的冰凉,卷走了她深情的呼喊,卷走了她苦苦的思念……
就一直随风而荡……飞跃万水千山……
飞到了沧山之下……
飞进了美丽的璃宫……
飞入了他的梦中……
☆、相思血泪(3)
淡淡的清阳洒在璃宫碧色的琉璃瓦上,寝殿里,却一片悲凉。
层层的明黄色纱帘随风轻拂,他仿佛听到她的呼唤,于梦中醒来,辗转之间,龙榻上只他一个人,又是一个孤枕夜凉,又是一个梦的破灭,她还是没有回来,上千个日夜期盼,春去了秋又来,花谢了花又开,她还没回,没有回,没有回家来……
床头飘着淡淡的花香,每天一束从百花族快马送来的合欢花。
从不间断,他想要让她回来就看得到。
床头架上,摆着堆放不下的盒子,每一只盒子里,都放着两根丁丁糖,刻着莫离两个字。
“倾夜……”一声呼唤,他回眸望去。
晨光中,她着一身素雅的烟罗裙,如清丽动人的合欢花,立在那明媚而笑。
“阿璃!”他如狂的将她揉进怀中,“你回了!你回了!”
“陛下,奴婢穿这身衣裳,好看吗,陛下,让奴婢来安慰您的心吧……”陌生的女音拉回他的心神。
“是谁允你穿着阿璃的衣裳!”他修长的手,瞬间狠佞的掐住那大胆宫女的脖子!
“陛下,奴婢……奴婢只是心疼陛下,才想要来安慰陛下……”
“脱下!”他的声音饮血般狂冷。
宫女颤颤巍巍的慌忙将裙子脱下。
侍卫早已闻声闯进来。
“拉下去,凌迟处死!”绝冷暴虐的呵斥。那宫女便惊恐的被人拉走。
哗!又是一室的寂静和孤独。
晨风轻吹着他如墨的长发,那一刻的狂喜化成一地的悲凉和狂痛。
他跌坐在地,捧着那一身烟罗裙,裙上仿佛还残留着她的气息和温暖,他紧紧的捧着罗裙,揉在心口,就像抱着她在怀中,只是,听不到她的呼唤,只有满室的落寞和昏昏惨惨的黑白,揪着那烟罗裙,痛哭出声,“阿璃,回来……,阿璃,回来吧……”
回来吧……
……回来吧……
一声声呼喊,带着他如山高如海深的痴狂相思,飞出了璃宫……
霜儿端着水盆,阿金拿着龙袍,身后还有些小宫女,静静的站在圆柱后。
阿金无声落着泪,看殿内跌坐在地上,捧着裙子痴痴落泪的陛下。
☆、相思血泪(4)
霜儿心酸如潮涌,泪流两行,“阿金姐,陛下他越来越消瘦了,再这样下去……”
“阿金,研磨……”殿内,传来凤倾夜低沉的声音。
她们收了泪,走进来,放下托盘,阿金走到案前研墨,霜儿铺纸。凤倾夜持笔,凤眸幽暗,再无半分光彩,黑色的墨迹,力透纸背。阿金跟霜儿静静立在一旁,看他下笔,写的却是那一阙绝泪之词:——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阿金见他写了一张又一张,泪水滴于纸面,化开了字迹,仿佛是他心里难以言语的痛和无尽的思念。阿金猛捂着唇,眼眶灼热,泪就忍不住的掉下来。霜儿已经哭肿了双眼,晨光越来越亮,一地的相思纸张,纷纷飘在金丝红毯上……风轻吹来,沙沙作响……
手在颤抖,紧紧的握着笔杆,他的泪就一颗颗湿了墨迹。
十年生死两茫茫,阿璃,你到底在何方……
你可知,我一直在等你回来……
“阿金,你让总管于太和城请来所有的歌姬,将这一阙词奏为琵琶曲,孤要让它传遍整个南诏,孤要让阿璃知道,孤一直在等她回来。”
“陛下、”阿金跪下来,“陛下,五年多了,娘娘她已经死了!”
他握着笔的手僵硬着,“十年之期,朕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