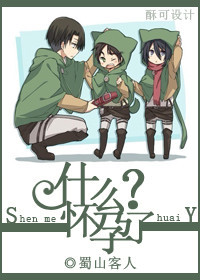弟,我怀孕了-第3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夏宝心下念叨,他是怎么样都不会相信这个禽兽的!但是这句话他未有说出口,只是紧紧抿住唇闭口不谈。
这时,夏瑜桐含着饱满的怒气冲进包间,‘啪!’房门被毫不留情的重重撞开,夏瑜桐一进来先确认了夏宝的平安再冷冷地望向叶臣逸,沉住心底的怒气:“你到底想怎么样?”
叶臣逸懒懒的勾起唇角,做回皮革沙发中,笑容多了那么一丝不羁:“父亲陪儿子吃饭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夏瑜桐顿时语塞。夏宝扯了扯她,仰头眼廓深邃的眼瞳里掩藏着水汽:“瑜桐,那个人不是我爸爸对吧?他跟我说,我不信他,瑜桐你跟我说好不好?”夏宝语中哽塞:“别人都有爸爸就我没有,瑜桐跟我说爸爸是外太空的人,可是我知道爸爸根本不是外太空的人,但是……但是宝儿觉得有瑜桐就很好了,所以,他不是我爸爸对吗?……他不是我爸爸。”夏宝说着眼中的泪花就哗啦啦往下掉。
瑜桐蹲下身搂住他,轻轻拍抚他的背:“别哭了,宝儿。”
夏宝在她怀里一边踌躇一边道:“瑜桐……瑜桐,呜……我们回家好不好?宝儿不想呆在这里……我们回家好不好!”
“好。”夏瑜桐擦拭着他满布泪痕的脸:“我们回家!”
却在刚要转身间,一只冰冰凉凉薄汗涔涔的手掌死死地握住她的手腕,清冽却又沙哑的声音在耳畔响起:“别走,给我一次照顾你们的机会,可以吗?”
夏瑜桐幽幽地回头,面前那双眸含着类似苦涩的东西,傲气、嚣张、狂傲在这一瞬间消失殆尽,徒留深深的浓浓的,仿佛墨汁融水般在他的眼底慢慢化开,那种感觉让人绕梁三尺百转千回遗留着刻骨铭心的疼。
好疼呐,真的真的……
“给我一次机会让我照顾你们,过去的事情我不会再计较我不会在意了,只要你,只要你回到我身边。”他的手在颤抖,涔涔的颤抖让她的心更如翻搅的痛!
但,那又如何呢……
如果台风来袭能不带走世界的生命,如果洪水猛兽能不伤害天地的灵性,如果世界末日能来了又走,然而这一切都不可能的,无论多小的灾难它来过了总是会给世界留下疮痍,而她的心也留下了疮痍,证明了那些痕迹的疮痍,所以不可能。
慢慢,慢慢她抽回自己的手。
“不可能的。因为我只要看到你的脸就会想起过去的创伤,你也一样吧?而现在,我有杜木轩,你有你的生活,何必硬要将原本不同海岸的沙子混合在一起呢。”
那双紫眸溢满了不甘、怒意、痛楚,那是夏瑜桐第二次见到那样的目光,就如院子里的花骨朵悄然绽放,而那少年强吻了她的那夜,也是这样的目光……
***
月光朦朦胧胧的逼仄在昏暗的房间里,洁白的天花板勾勒了窗外树丛的绰影。夏瑜桐躺在床上,静望着高高的天花板,耳内没有一丝声音,世界静谧的有些不可思议。她倦了,倦乏了面对熟悉的人以及凌乱的回忆,阖上眼时,她看见了十六岁那年的自己……
彼时,房内的夏瑜桐并未了解到有一人影正鬼鬼祟祟的潜入了公寓了,如今正值秋夜那人知道此时房内的窗棂定会阖上,他溜进屋子便轻手轻脚的关起客厅内的所有窗户,最后将厨房内的媒气管剪开,刺激浓烈的煤气味顿时弥漫开去!
夜很沉,床头的夏瑜桐愈来愈感疲惫,身子疲软的使不上劲来,迷迷糊糊的醒来她的意识越来越涣散,为什么空气中飘着浓稠的煤气味?
赫然惊觉!煤气泄露?!
她忍住愈渐涣散的意识,强撑着疲倦晕乏的身子从床上摔到了地上,然双腿却使不上任何力气,全靠她的意识在努力挪动!她拼了命趴至客厅,想呼周怡,忽然惊觉周怡今夜彻夜加班不会回来。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她只能靠自己,夏宝,夏宝还在房间!她撑着无力的身子向厨房挪动,然越靠近厨房那种气味却愈加浓烈,浓得她的脑海似要炸开的疼!
屏住呼吸,尽力不去吸气,双腿渐渐从无力转换为颤抖,浓郁的煤气味不断地摩挲着她的神经,那些神经渐渐的无感无知,然后渐渐地她开始失去了自己的意识……
天地浑浊,她的眼前漆黑混沌成一片!
chapter 59
半醒半寐,浑浑噩噩,仿佛做了一个冗长且遥不可及的梦……她倏地从梦靥中悚然醒来!薄薄的月华透过窗棂映景而来,窗外是母亲栽种的芦荟,用以制作成廉价的保养品去夜市上卖钱。芦荟并不好看的绰影映在灰蒙蒙的天花板上,凌乱肆意的,却是她最喜欢的。
‘碰——!’院子生锈的铁门传来一声沉重辽响的开阖音。她浑然睁大眼睛,黑白分明如雾顾盼的双眸在昏暗的光影里惊慌失措,待得外头传来那人踉跄沉重的步子带着破口大骂滚滚袭来,房外便响起母亲的啜泣还有那人的嫌弃的辱骂,她赫然从床头跳起躲进自己脏乱形小的书桌下。
果不其然,那人猛力的推开了她的房门,光线霎时强烈的逼进房内。她蜷缩在桌下害怕的打颤。伴随着浓重扑鼻的酒精味,那人手持酒瓶,脸颊如火烧的红,步子踉跄蹒跚却饱满有力的将她从桌底下狠狠拽出来,随即一顿暴打,口中反复呢喃:“你个没用的小贱种,老子生你养你做什么啊?”
她蜷缩着身子任凭那人的羞辱打骂却是不吭一声,漆黑的眼瞳在光影里飘散着幽幽的雾气,是她这个年纪不该有的目光。
母亲在一旁劝阻抽泣:“别打了,孩子都快被你打死了!”然而,那人却浑然不听母亲的劝诫,反将母亲推到在地。
屋子里徘徊着母亲久久的哭泣。
还有她凌厉冷淡的目光。
不知过了多久,她咬紧牙关已经不知道全身上下那里在传来痛楚,酒鬼似乎疲倦了猛灌了几口酒啧了几声踉踉跄跄的转头回房了。*
她冷漠吃痛的从地上站起,忍住全身的疼痛扶起地上的母亲,母亲那苍老的容颜上满面泪痕,语音沙哑:“你没出生就好了,我为什么要生下你让你来受苦?”哭腔愈浓,消瘦的手抚摸着她冰冰凉凉的脸:“孩子啊,你如果受不了就结束自己的生命吧!你这样,我看得好心疼。”
目光依旧淡漠如霜,她安抚母亲回了房间。
昏暗幽小的房间内又恢复如常的静谧,天花板上芦荟的影子错落层叠,她打开桌上那份文件夹,那里面全是她设计的珠宝设计图,一笔一笔精心勾勒满满用心,而设计的作品落落大方款款有致,她那么那么热爱珠宝设计,她甚至觉得自己是有天赋的,所有她才不会去死!她才不会同她那位懦弱胆小的母亲一样,每天只想着死!
是的,那位只会哭泣的妇女是她的母亲,她爱她的母亲也讨厌她的懦弱,母亲每每面临崩溃的时候总会让她去死,但是死绝对不是解脱!所以她要活着,努力的活着,骄傲的活着。
眼瞳逐渐幽深,而那位醉酒打人的酒鬼就是她的父亲‘夏声’。夏声原本生于富裕的家庭以至养成挥霍无度的个性,然花无百日红,夏家惨遭金融危机的覆灭家道中落,不喝酒时的夏声还是很温柔很稳重的,他从未吃过苦却愿意为了家计毅然当保安赚钱,但是每当他心情不好喝了酒回到家总是要打她和她的母亲。
清冷的月光照在她冷漠如雾的脸颊。
那是她的十五岁,青葱岁月却不再郁郁葱葱,花好年华却只能空待落寞,岁月静好不过指尖匆匆——那就是她本该幸福却要饱含酸涩的十五岁。
夏音在一家师资落后的名工子弟学校念书,她的成绩并不出众然而她的绘画功底却是另老师都自愧不如。她常常在夏天穿着高领的衬衫为了遮挡自己被父亲虐打的伤痕。她每天中午都要为父亲送去便当,因为家里拮据容不得在外花钱用餐。
某种程度来说,她很幸运,因为父亲在杜氏企业当保安,而杜氏里有优秀的珠宝设计团队,每次她在门口等待父亲的时候总能看到那些在跟报摊老板借来的杂志中看到的优秀设计师,那时候的她认为杜氏的珠宝设计部便是遥不可及的天堂。
那天下了很大很大的雨,密密麻麻的雨丝蹉跎着地面溅起无数苍凉的水花。她撑着一把老式的黑色大伞,怀揣着父亲的便当还有自己的画架蜷缩在伞下。她不能走进杜氏,因为她没有资格,所以每每在外头百般寥赖等待父亲的时候她总喜欢带上自己的画架幸福的勾勒几笔,然而今天天不从人愿,下了这么大的雨怕是不能画画了。
无聊的看着雨丝扑籁籁的从黑色大伞的边缘滑落,蒙蒙雨雾婆娑间,一辆黑色房车从雾气腾腾的水雾中跃然而出,缓缓地停驻在杜氏门前。她认得那辆车,每个礼拜天那辆车总会在同一时间来到杜氏,而那辆车的主人是一位眉目清俊恍如贵族的少年。
司机率先下车撑起金柄的大伞打开了后车门,先是一条修长的腿跃入眼帘,然后那个少年优雅的跨出车内,清远冷峻的眉目,悠然清淡的双唇,五官轮廓在雨雾间略显飘渺像极了画里走出的王子令人神往。司机将伞打在少年的头顶,自己却宁愿在外淋雨,护送着少年走进杜氏大楼。
不知是否为错觉,她似乎感觉到少年那种睿智却又带着淡漠疏离的眼神从她身上缓缓掠过,惊得她瞬间低下了头不敢去看。
又是等了很久,雨越下越大,雨丝滂沱在风中模糊了视野。父亲迟迟未有出来拿便当,她哀哀叹气或许父亲是吃过了,于是抱紧画架和便当撑着伞准备离去。然而不知是否是雨雾太过密浓,一辆车悄无声息驶来,等她瞧见时来不及闪躲就那样跌在了*的路面,黑伞画稿散落一地,便当盒也打翻在地。
幸好司机急忙刹车才不至于酿成惨祸。
雨水灌湿她的身子,一瞬间便淋得跟落汤鸡似的,狼狈的她跌坐在水潭中,看着眼前散乱满地的便当盒眼中一阵酸,回去定要挨母亲的厉叱了,她觉得今天是她最倒霉的日子了。
车门打开,司机连忙紧张地询问她:“你没事吧?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始终在惋惜地上打翻的便当盒的她,吃痛的站起面色淡漠的理了理地上的东西又撑起黑色大伞,淡淡地说:“没事。”雨雾中,她片刻都不想停留,狼狈的她转身就走。
司机赫然发现地上还遗留了几张画稿想唤刚才那个女孩儿时,水汽弥漫间却已不见那个女孩儿的影子了。
父亲失业了!
当那晚夏声回到家中时,这个犹如晴天霹雳般的噩耗顿时破碎的整个家庭,原本便拮据到不堪重负的家庭在此刻面临着支离破碎的威胁。父亲喝的烂醉如泥回来便是对她以及母亲一顿拳打脚踢,那一次显现要了她的命,母亲差点喝下了储藏了已久的老鼠药。
自此父亲酗酒更甚,脾气也变得暴躁喜怒无常,打骂也比从前更甚。母亲整天以泪洗面,而这样下去可能家里连填饱肚子的钱都没有了。
她第一感到生命是如此脆弱,生活是如此的艰辛,然而她绝对不想死,她要骄傲的活下去!不知为脑海中竟然迸出了那个眉目清俊表情疏远的少年,她也不知为何竟然在这样无助得快要崩溃的时候竟然想起了一个陌生人,然而这个人或许是她的一线生机,或许只有这个人才能帮她度过困苦的境地。
于是,她做出了一个决定,哪怕是要堕落沉沦,哪怕要浸满污秽不堪,都无所谓了。因为当一个人连生存下去都变得艰难时就不会再去计较那可笑的自尊与良知。
在父亲被辞退后的一个礼拜,她又来到了杜氏云楼前,瘦弱的她特意换上了一身短袖毫不避忌

![[封神英雄榜]师弟,你别跑封面](http://www.xntxt2.com/cover/19/1969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