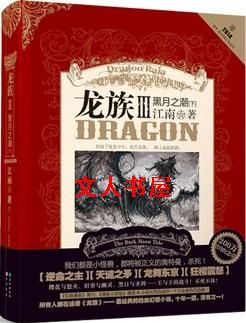狼亲狈友·下部-第6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白左寒扯住他的耳朵晃了晃,“发什么呆呢?嫌我给你找的工作不好啊?”
“不呢,我很高兴,谢谢。”杨小空心酸地蹭蹭白左寒的颈窝,责怪自己还是太没有本事,才会让白左寒如此操心。
计划完美无瑕,等毕业生答辩工作结束,杨小空带上所有材料到校部去签上合同就一锤定音了,数数时间不过一个多礼拜,白左寒好像看到杨小空已经是他的同事而非学生,沾沾自喜地说:“面团,等你签了合同,我带你去见见我爸妈。”
杨小空眼睛一亮,又黯淡下去,“为什么一定要签合同后?”
白左寒啐道:“我是不在乎什么师生恋,这都什么世道了!只是老头老太思想停留在旧社会,让他们接受我喜欢男人就抗争了十几年,又冒出个师生恋,这不是要死么?”
杨小空乖顺地应道:“我都听你的。”
杨小空毕业答辩这一天早上,白左寒比他还紧张,先是把黑猪关进厕所里,免得那畜生把杨小空干净利落的白衬衫和米色便裤拱得乱糟糟,接着又在他耳后喷了点古龙水。
杨小空哭笑不得:“你干什么呀?”
白左寒耙了耙杨小空的头发,欣赏得几近陶醉:当初傻乎乎的男孩子,由自己一手培养成沉稳自信的好男人,这可不是一般的成就感。
杨小空捧着他的脸,唇边勾起淡淡的自负:“过了今天,以后我和你平起平坐。”
白左寒皱眉:“我什么时候让你比我低一等了?”
杨小空在他皱起的眉间落下一个吻,笑而不言。
整场答辩没有出任何差池,美术学院只有杨小空一个人是研二毕业,而且他一直是个踏实肯干的孩子,没有任何人想非难他。答辩进行到一半时,后门钻进来一个人,刺溜窜到最后排坐下,无声地挥手向主席台致意。
站在主席台上的杨小空抬眼看到他,发自肺腑地绽开一个暖心的笑容。
杨小空答辩结束后,悄声溜到后排在柏为屿身边坐下,柏为屿轻轻捶了他一拳,“以前你看着我毕业,现在我看着你毕业。”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杨小空一摸贴在柏为屿脑门上的纱布,“你怎么了?”
柏为屿挠头:“没事,走路不长眼,撞到电线杆了。”
前排有一个老师喝道:“请同学们不要说话,保持会场安静。”
杨小空握住柏为屿手搁在自己腿上,两人对视一眼,嘿嘿笑。杨小空掏出笔在他手掌上写字,柏为屿抢过笔,不甘示弱地写在杨小空手背上。
你写一句,我写一句,手上写不下,写到手腕上,又对视一眼,你笑我傻,我笑你傻。
后来的每一年毕业生答辩,杨小空都会坐在这个位置上,想起那一年两个傻瓜为争论去哪家店海吞一顿来庆祝毕业而在双方的手上写满密密麻麻的字。
逝去的青春美好而纯粹,每当缅怀往事,细细回味他们的喜与悲,有伤感却没有遗憾,有暧昧却不是爱情,唯有这一页回忆是他心里永久的伤,一旦翻开则痛心不已。
欠债还钱
柏为屿威胁段杀在没还清赔款之前不得在外留宿,晚上九点前段杀没有回来他就到武甲家去放火。
段杀没有表示异议,安分地睡在沙发上,把床让给柏为屿。
第二天下班,段杀在食堂吃过饭回来,柏为屿不在家,他习惯性地掏出手机拨柏为屿的号码,电话那一头马上传来一连串粗俗的痛骂:“你妈了个X的死贱人,打屁打啊?老子不认识你!再打你大爷我操你祖宗十八代!”
段杀只好掐了电话,自嘲地摇摇头:打电话干什么?真是手贱!
和柏为屿一起吃饭的杨小空等几个人目瞪口呆:“为屿,你骂谁呀?”
柏为屿关了手机:“一个不认识的王八婊 子,三天两头打错电话。”
夏威咋舌:“那也不至于骂得这么狠啊。”
“唉,不提那些个贱种!”柏为屿豪爽地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来来来,今天小空毕业,是个大好日子,我先干为敬!”
其余几人皆面面相觑,没有心思动杯。
毕业又不是什么非得大请特请不可的大喜事,柏为屿拍胸脯喊着要请客,本来到大排档去吃就行了,可他偏偏选了个相当高档的饭店花两千多请了一餐,五个人围着硕大的圆桌面对铺张浪费的满汉全席干瞪眼,连乐正七都没胃口吃喝,迷惑地看着柏为屿。
段和在桌子下踢踢夏威:“为屿好像不太对劲。”
夏威满不在乎:“他就那样,人来疯。”
段和嘀咕:“靠,他刷的是我哥的工资卡,我哥一个月的工资给他刷两次就没了。”
柏为屿敬完杨小空敬乐正七,敬完乐正七敬夏威,敬完夏威要敬段和,段和捂着酒杯,“留一个人开车吧。”
柏为屿嘿嘿傻笑:“也对也对,来来来,段和留着开车,小的们给我接着喝!”
杨小空搁下筷子,用湿毛巾擦擦手,起身扯住柏为屿:“为屿,陪我去上个洗手间。”
柏为屿一脸鄙视:“小学生啊你?自己去。”
杨小空不由分说,拖着他就走。
柏为屿一路骂骂咧咧:“没用的东西,撒尿还要人陪?长不大的咩咩……”
杨小空把他拽进洗手间推到单间里,反手关上门:“你怎么了?”
“我怎么了?”柏为屿纳闷。
杨小空点起一支烟,眯眼对上他的眸子,“还没动筷就不要命的喝酒,这么想醉死?”
柏为屿渐渐地收敛笑容,“我才喝了半瓶红酒,你别神经过敏。”
杨小空呼出一口烟雾,扳过柏为屿的脑袋,额头顶着他的额头,“为屿,不管发生什么事,喝酒不能让你高兴起来的,和我说吧。”
一种昏天暗地的剧痛骤然涌上心头,柏为屿怕自己会当场掉下眼泪,赶紧偏开脸,泄愤似的狂踹一顿门板,而后一屁股坐在马桶上,两手抱着脑袋,使劲忍住在眼眶中打转的泪水,忍得额上青筋微跳,缓了几分钟后,闷声闷气地说:“我和他分手了。”
“为什么?”
“他和别人好了。”
“谁?”
“武甲。”
杨小空咬了咬牙,睫下恍惚有水光闪动,毫无意识地把剩下半截子烟捏碎了,他单手揽过柏为屿的肩,另一手拢进对方潮湿又柔软的短发之间,有一下没一下地摸着,眼神空洞地望向前方,“别伤心,谁缺了谁都照样活,你还怕找不到更好的吗?”
柏为屿用手背一擦鼻子,逞强装的很不屑,啐道:“我才不伤心!”
段杀陪武甲去诊所挂吊瓶,因为前一晚撕开了这十几年的薄纱,两个人都很不习惯,能搭上的话越发少了。休息室里照样没有人,电视的声音聒噪不休,段杀盯着电视发呆,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尤其是过了八点半后,隔几分钟就看看时间,武甲问:“你有事?”
“没。”
“急着走?”
“没。”段杀又看了眼时间。
武甲好笑,故意把输液器调慢些,“挂完这瓶大概要十点半了,既然不急就陪我等着吧。”
“嗯。”段杀焦躁之情难以掩盖,踱到门外去抽了支烟,再一看时间,九点多了!他倒是不怕柏为屿真的会去放火,谅那小子喊得嚣张也没胆量干,但到底顾忌什么,不得而知。思来想去,他回到休息室,硬着头皮撒谎:“我单位有点事……”
武甲看透了他,追问道:“什么事?”
“那什么……呃……”
“今天看到你就想问了,头上的伤怎么弄的?”武甲唇边带着戏谑的笑意。
“走路撞到电线杆。”段杀想也不想。
“自己撞的?”武甲玩味地拉长尾音。
段杀被看得发毛,忽地坐下来轻轻握住他的指尖,酝酿片刻,说:“我和柏为屿谈分手了。”
“然后?”
“还有些事没弄清楚。”
“然后?”
段杀答不出个所以然来,扪心自问,他真庆幸自己掏不出六十几万赔给柏为屿,巴不得永远赔不起,永远不要断干净。可他现在和武甲算什么?朋友不是朋友,恋人不是恋人,他对这个人没有任何龌龊的欲望,哪怕这样暧昧地拉着对方的手都心虚。
武甲等了很久也没得到答复,谅解地一笑:“有事就赶紧去吧,别耽误了。”
段杀惭愧地点了点头,风风火火往回赶。
到家已经快九点半,柏为屿没有闹事,他喝了不少酒,打个赤膊靠墙呼呼大睡。
家里保持着昨晚的一片狼藉,沙发新泼上了牛奶,完全不能睡人了。
段杀洗漱完,静悄悄躺在床的另一侧。柏为屿蜷成一团,只露了一个后背在他面前,笼在清冷凉薄的月光之下显得异常寂寞而无助。他侧身看着,心里一抽一抽地疼,遭了催眠一般抬手轻握对方的肩膀,顺着那赤 裸的脊梁从上往下抚摸,掌心触及到熟悉且美好的肌肤,一寸一寸他都吻过,一寸一寸都曾留下粉红的印记。
他撑起身偷偷地看柏为屿沉睡的侧脸,柏为屿把额头上的纱布扯掉了,明显是扯得太粗心,刚结的嫩痂被扯下一小块,往外冒出几颗血珠。
段杀用指尖触了触那血珠,发现已经干了,他吻吻柏为屿的眼角,唇下的睫毛有些潮湿,正想再吻吻对方的脸颊,骤然清醒:我在干什么呢?
仅存的一丝可怜的理智勒住他想拥抱对方的冲动,他的鼻尖莫名地酸涩难抑,收回手,逼迫自己闭上眼睛进入睡眠状态。
就这么安安稳稳地睡了一晚,天亮后柏为屿醒了,两个人面面相觑了几秒,柏为屿一拳捶向段杀眼眶,段杀瘁不及防,咕咚一下栽下床,还没缓过神来,柏为屿又操起床头灯劈头盖脸地给了他几下:“我操你祖宗十八代,你个贱种,欠了老子一大兜钱没还清,你他妈就是一欠了嫖资的穷光蛋,别以为自己是情圣!离我远点!”
柏为屿泄完愤,将七零八落的床头灯一丢,“钱凑齐没有?”
“……”
“说话!你大爷的!哑巴了?”
“没。”
“去借去抢去偷!快把老子的卖身钱还来!”柏为屿狂踹他几脚,还不解恨,又比了两个中指,然后自顾自刷牙洗脸,顺手把段杀的刮胡刀牙刷丢进垃圾桶,拎上钥匙出门去吃早餐。
家里已经乱无可乱,再怎么打砸摔也不会比目前更糟糕了,段杀动手稍微收拾收拾屋子,冲了个冷水澡,没有刮脸便照常去上班。
遗憾,等他下班回家,早上才收拾好的地方又遭殃了,更要命的是,床也不能睡了——柏为屿用油性签字笔在床单上划了一条三八线,然后往段杀睡的那一半撒了一泡尿。
段杀本来不知道那是什么,摸了一把水渍,闻了闻,确定是尿后,想发火发不出来,倒是有点想笑。
白左寒的姐姐这天突然心血来潮打电话给弟弟,说想借十万买一支股票,这一点小钱白左寒完全没放在心上,想也不想便应允了,打算趁上课间隙到校门外的柜员机上办理自助转账,可恨的是,刚走出校门就看到了方雾阴魂不散地靠在车门边抽烟。
方雾一见他就死皮赖脸地缠上来,满脸堆笑。
对待无处不在的蟑螂:
A:照死了打
B:无视
白左寒做了三秒选择题,最后选B,绕过他就走。
方雾跟在他身后问:“左寒,你今天怎么没开车?这是准备去哪?我送你吧。”
白左寒加快脚步拐进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