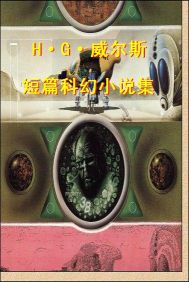乔治·奥威尔 1984-第4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些老鼠都很大,都到了鼠须硬挺、毛色发棕的年龄。
“老鼠,”奥勃良仍向看不见的听众说,“是啮齿动物,但是也食肉。这一点你想必知道。你一定也听到过本市贫民区发生的事情。在有些街道,做妈妈的不敢把孩子单独留在家里,哪怕只有五分钟,老鼠就会出动,不需多久就会把孩子皮肉啃光。只剩几根小骨头。它们也咬病人和快死的人。他们能知道谁没有还手之力,智力真是惊人。”
铁笼子里传来一阵吱吱的叫声。温斯顿听着好象是从远处传来一样。原来老鼠在打架,它们要想钻过隔开它们的格子到对面去。他也听到一声绝望的呻吟。这,似乎也是从他身外什么地方传来的。
奥勃良提起铁笼子,他在提起来的时候,按了一下里面的什么东西,温斯顿听到咔嚓一声,他拼命想挣脱开他绑在上面的椅子。但一点也没有用。他身上的每一部分,甚至他的脑袋都给绑得一动也不能动。奥勃良把铁笼子移得更近一些,距离温斯顿的眼前不到一公尺了。
“我已经按了一下第一键,”奥勃良说。“这个笼子的构造你是知道的。面罩正好合你的脑袋,不留空隙。我一按第二键,笼门就拉开。这些饿慌了的小畜牲就会象万箭齐发一样窜出来。你以前看到过老鼠窜跳没有?它们会直扑你的脸孔,一口咬住不放。有时它们先咬眼睛。有时它们先咬面颊,再吃舌头。”
铁笼子又移近了一些。越来越近了。温斯顿听见一阵阵尖叫。好象就在他的头上。但是他拼命克制自已,不要惊慌。要用脑筋想,哪怕只有半秒钟,这也是唯一的希望。突然,他的鼻尖闻到了老鼠的霉臭味。他感到一阵猛烈的恶心,几乎晕了过去。眼前漆黑一片。他刹那间丧失了神志,成了一头尖叫的畜生。但是他紧紧抱住一个念头,终于在黑暗中挣扎出来。只有一个办法,唯一的办法,可以救自己。
那就是必须在他和老鼠之间插进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的身体来挡开。
面罩的圈子大小正好把别的一切东西排除于他的视野之外。铁笼门距他的脸只有一两个巴掌远。老鼠已经知道可以大嚼一顿了,有一只在上窜下跳,另外一只老得掉了毛,后腿支地站了起来,前爪抓住铁丝,鼻子到处在嗅。温斯顿可以看到它的胡须和黄牙。黑色的恐怖又袭上心来。他眼前一片昏暗,束手无策,脑里一片空白。
“这是古代中华帝国的常用惩罚,”奥勃良一如既往地训诲道。
面罩挨到了他的脸上。铁丝碰在他的面颊上。接着——
唉,不,这并不能免除,这只是希望,小小的一线希望。太迟了,也许太迟了。但是他突然明白,在整个世界上,他只有一个人可以把惩罚转嫁上去——只有一个人的身体他可以把她插在他和老鼠之间。他一遍又一遍地拼命大叫:
“咬裘莉亚!咬裘莉亚!别咬我!裘莉亚!你们怎样咬她都行。把她的脸咬下来,啃她的骨头。别咬我!裘莉亚!
别咬我!”
他往后倒了下去,掉到了深渊里,离开了老鼠。他的身体仍绑在椅子上,但是他连人带椅掉下了地板,掉过了大楼的墙壁,掉过了地球,掉过了海洋,掉过了大气层,掉进了太空,掉进了星际——远远地,远远地,远远地离开了老鼠。
他已在光年的距离之外,但是奥勃良仍站在他旁边。他的脸上仍冷冰冰地贴着一根铁丝。但是从四周的一片漆黑中,他听到咔嚓一声,他知道笼门已经关上,没有打开。
第6节
栗树咖啡馆里阒无一人。一道阳光从窗口斜照进来,照在积了灰尘的桌面上有些发黄。这是寂寞的十五点。电幕上传来一阵轻微的音乐声。
温斯顿坐在他惯常坐的角落里,对着一只空杯子发呆。他过一阵子就抬起头来看一眼对面墙上的那张大脸。下面的文字说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服务员不等招呼就上来为他斟满了一杯胜利牌杜松子酒,从另外一只瓶子里倒几粒有丁香味的糖精在里面,这是栗树咖啡馆的特殊风味。
温斯顿在听着电幕的广播。目前只有音乐,但很可能随时会广播和平部的特别公报。非洲前线的消息极其令人不安。他一整天总是为此感到担心。欧亚国的一支军队(大洋国在同欧亚国打仗;大洋国一直在和欧亚国打仗)南进神速。中午的公报没有说具体的地点,但很可能战场已移到刚果河口。布拉柴维尔和利奥彼德维尔已危在旦夕。不用看地图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不仅是丧失中非问题,而且在整个战争中,大洋国本土第一次受到了威胁。
他心中忽然感到一阵激动,很难说是恐惧,这是一种莫名的激动,但马上又平息下去了。他不再去想战争。这些日子里,他对任何事情,都无法集中思想到几分钟以上。他拿起酒杯一饮而尽。象往常一样,他感到一阵哆嗦,甚至有些恶心。这玩意儿可够呛。丁香油和糖精本来就已够令人恶心的,更盖不过杜松子酒的油味儿。最糟糕的是杜松子酒味在他身上日夜不散,使他感到同那——臭味不可分解地混合在一起。
即使在他思想里,他也从来不指明那——是什么,只要能办到,他就尽量不去想它们的形状。它们是他隐隐约约想起的东西,在他面前上窜下跳,臭味刺鼻。他的肚子里,杜松子翻起了胃,他张开发紫的嘴唇打个嗝。他们放他出来后,他就发胖了,恢复了原来的脸色——说实话比原来还好。他的线条粗了起来,鼻子上和脸颊上的皮肤发红,甚至秃光瓢也太红了一些。服务员又没有等他招呼就送上棋盘和当天的《泰晤士报》来,还把刊登棋艺栏的一页打开。看到温斯顿酒杯已空,又端瓶斟满。不需要叫酒。他们知道他的习惯。棋盘总是等着他,他这角落的桌子总是给他留着;甚至座上客满时,他这桌子也只有他一位客人,因为没有人愿意挨着他太近。他甚至从来不记一下喝了几杯。过一会儿,他们就送一张脏纸条来,他们说是帐单,但是他觉得他们总是少算了帐。即使倒过来多算了帐也无所谓。他如今总不缺钱花。他甚至还有一个工作,一个挂名差使,比他原来的工作的待遇要好多了。
电幕上乐声中断,有人说话。温斯顿抬起头来听。不过不是前线来的公报,不过是富裕部的一则简短公告。原来上一季度第十个三中计划鞋带产量超额完成百分之九十八。
他看了一下报纸上的那局难棋,就把棋子摆了开来。这局棋结局很巧妙,关键在两只相。“白子先走,两步将死。”
温斯顿抬头一看老大哥的画像。白子总将死对方,他带着一种模模糊糊的神秘感觉这么想。总是毫无例外地这样安排好棋局的。自开天辟地以来,任何难棋中从来没有黑子取胜的。
这是不是象征善永远战胜恶?那张庞大的脸看着他,神情安详,充满力量。白子总是将死对方。
电幕上的声音停了一下,又用一种严肃得多的不同口气说:“十五点三十分有重要公告,请注意收听。十五点三十分有重要消息,请注意收听,不要错过。十五点三十分。”丁当的音乐声又起。
温斯顿心中一阵乱。这是前线来的公报;他根据本能知道这一定是坏消息。他这一整天时断时续地想到在非洲可能吃了大败仗,这就感到一阵兴奋。他好象真的看到了欧亚国的军队蜂拥而过从来没有突破过的边界,象一队蚂蚁似的拥到了非洲的下端。为什么没有办法从侧翼包抄他们呢?他的脑海里清晰地出现了西非海岸的轮廓。他拣起白色的相朝前走了一步。这一着走的是地方。甚至在他看到黑色的大军往南疾驰的时候,他也看到另外一支大军,不知在什么地方集合起来,突然出现在他们的后方,割断了他们的陆海交通。他觉得由于自已主观这样愿望,另一支大军在实际上出现了。
但是必须立刻行动。如果让他们控制了整个非洲,让他们取得好望角的机场和潜艇基地,大洋国就要切成两半。可能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战败、崩溃、重新划分世界、党的毁灭!
他深深地吸一口气。一种奇怪的交杂的感情——不过不完全是复杂的,而是层层的感情,只是不知道最底下一层是什么——在他的内心中斗争着。
这一阵心乱如麻过去了。他把白色的相又放回来。不过这时他无法安定下来认真考虑难局问题。他的思想又开了小差。他不自觉地在桌上的尘埃上用手指涂抹:
2+2=5。
她说过,“他们不能钻到你体内去。”但是他们能够。奥勃良说过,“你在这里碰到的事情是永远不灭的。”这话不错。
有些事情,你自己的行为,是无法挽回的。你的心胸里有什么东西已经给掐死了,烧死了,腐蚀掉了。
他看到过她;他甚至同她说过话。已经不再有什么危险了。他凭本能知道,他们现在对他的所作所为已几乎不发生兴趣。如果他们两人有谁愿意,他可以安排同她再碰头一次。他们那次碰到是偶然的事。那是在公园里,三月间有一天天气很不好,冷得彻骨,地上冻成铁块一样,草都死了,到处都没有新芽,只有一些藏红花露头,但被寒风都吹刮跑了。他们交臂而过,视同陌路人。但是他却转过身来跟着她,不过并不很热心。他知道没有危险,谁都对他们不发生兴趣。她没有说话。她在草地上斜穿过去,好象是要想甩开他,可是后来见到甩不开,就让他走到身旁来。他们走着走着就走到掉光了叶子的枯丛中间,这个枯丛既不能躲人又不能防风。他们却停下步来。这一天冷得厉害。寒风穿过枯枝,有时把发脏的藏红花吹刮跑了。他把胳膊搂住了她的腰。
周围没有电幕,但很可能有隐藏的话筒,而且,他们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但是这没有关系,什么事情都已没有关系了。如果他们愿意,也可以在地上躺下来干那个。一想到这点,他的肌肉就吓得发僵。她对他的搂抱毫无任何反应。她甚至连摆脱也不想摆脱。他现在知道了她发生了什么变化。
她的脸瘦了,还有一条长疤,从前额一直到太阳穴,有一半给头发遮住了;不过所谓变化,指的不是这个。是她的腰比以前粗了,而且很奇怪,比以前僵硬。他记得有一次,在火箭弹爆炸以后,他帮助别人从废墟里拖出一具尸体来,他很吃惊地发现,不仅尸体沉重得令人难以相信,而且僵硬得不象人体而象石块,很不好抬。她的身体也使你感到那样。他不禁想到她的皮肤一定没有以前那么细腻了。
他没有想去吻她,他们俩也没有说话。他们后来往回走过大门时,她这才第一次正视他。这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瞥,充满了轻蔑和憎恶。他不知道这种憎恶完全出诸过去,还是也由于他的浮肿的脸和风刮得眼睛流泪而引起的。他们在两把铁椅上并肩坐了下来,但没有挨得太近。他看到她张口要说话。她把她的笨重的鞋子移动几毫米,有意踩断了一根小树枝。他注意到她的脚似乎比以前宽了。
“我出卖了你,”她若无其事地说。
“我出卖了你,”他说。
她又很快地憎恶的看了他一眼。
“有时候,”她说,“他们用什么东西来威胁你,这东西你无法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