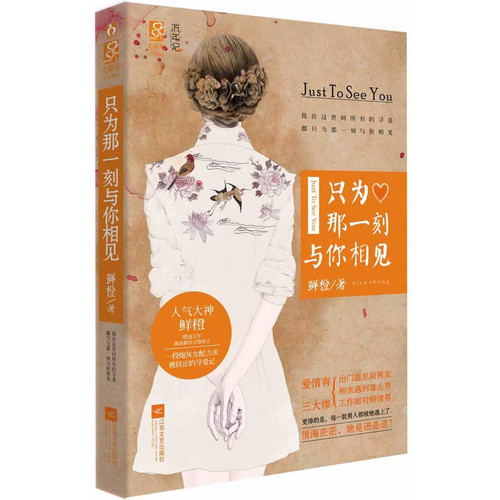那一泓薄荷色的浪漫-第1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叫水凝,我说,就是冰,水凝滞了就是冰。
他依旧不注视我,但笑了:照你这样说,天塌下来就该叫做地,而火星灿烂了就可以叫太阳?
我没有料到他会笑,偷偷看了看他的侧面,觉得他笑的时候嘴角微微上翘,很好看。于是我大胆地跟他斗口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永恒的规律,就是物及必返,这正如好的尽头是孬而善的尽头是恶,所以水凝就是冰。
你这是禅机还是哲理?他仍旧笑着说,那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如何能够记忘我?
首先,我说,你不要曲解我的信仰,我并不喜欢追究禅机,甚至不信仰任何宗教,因为我觉得卡尔?马克思的说法很有道理: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有情。我虽然叹息但不是因为压抑,我生活在一个充满温情的世界,我还不需要用什么来置换无情,我只不过以为天地间万物都有可借鉴的一面,因此我喜欢宗教。
既然你说宗教是一种叹息,那么,也就是说,所有信仰宗教的人都是因为叹息喽?古净尘说,他好象有些逗弄我的意思,仿佛我是个小孩子。
你又在曲解我,我争辩说,我只是说宗教在那种氛围里产生,并不是说,它的存在永远用于医治那些叹息,其实在今天,有挺多人在汲取宗教美好的精神来加强自己的修为。
噢,他点点头:那么现在你可以告诉我,怎样忘我了吧?
你需要宇宙的哪位真主的教诲呢?
佛主吧,佛跟我们中国人比较亲近。
好吧,先给你讲一个关于佛的故事,我正色说:
很久以前,一个和尚很想寻求佛道的最高境界,于是呢,他穿越万水千山,四处化缘。但是一年很快过去了,他发现他收获的篮子里空空如也,就有些失望。归途上,他见到一对孤单无依的老夫妻,因为他们孤苦,又不健康,他就教他们每天除却一切杂念地诵念“阿米托佛”,老两口如法炮制。
又一年过去了,和尚依然两手空空,他再度返回老两口的住处,远远地,他就发现老两口的屋顶上佛光璀灿,显然道行已深。于是,和尚登门拜望:原来,老两口正是按着他的教法,诵了一年的‘阿米托佛’。但是,由于地方音的羁绊,他们把‘佛’念成‘发’了。‘阿米托发’……他们诵着。咳!错了错了!是‘佛’不是‘发’,和尚纠正说。噢,佛,老两口纠正着。
和尚再度出游。
第三年,和尚依旧没有收获,回到老两口的住处时,发现屋顶的佛光不见了,老两口仍在不停地念‘阿米托佛’,但是他们总也免不了把佛读成‘发’,于是,再纠正过来,和尚恍然大悟:只要心中有佛,‘阿米托佛’和‘阿米托发’有什么不同呢?于是和尚再不出游,后来,他成为一名有道高僧。
你听懂这个故事了吗?我说,这是一本《小小说》上的故事,我感觉忘我是一种境界,也不是用什么公式套出来的。
嗯,我懂了,古净尘笑着正视着我说,你知道不,我比你至少大三四岁,你倒是挺善于,也挺敢教训人的。
我看得出,他目光中流溢的是赞赏而不是批评,就继续跟他谈起来。
从海边到我家有很长一段路,身外就是狂风大雨,但是我和古净尘似乎都浑然忘我。我们谈雪莱,谈荻金森,谈普希金,泰戈尔和勃朗特三姐妹……我们共同的感觉就是西方文学提供给人类的是驰骋的想象力,是浪漫,洒脱无羁、丰富多姿的浪漫;而中国文学提供给人类的是博、大、精、深。西方文学是浪漫的现实,中国文学是现实的浪漫……不觉间,我已经到家了。
古净尘冲我挥别说,水凝,希望还有机会跟你谈文学。
那是一定的,我快活地说。我也不清楚为什么对他的要求我会这样乐于接受。也许是他身上那种莫可违逆的气度吧?总之我很快乐,前所未有的欢畅!我整个的身心因为回味这次偶然的邂逅而震颤不已!出门前那些压抑和不快乐,都在这浓厚的兴奋中阵风一样消失掉了!
更使我惊奇的是:我和古净尘从来没有彼此邀约,却往往相会在海边,有时清早,有时午后。
于是许多个日子,我和古净尘一道看海,一道倾听海浪声,品味大自然的喧嚣被海包容的景象。
古净尘告诉我,他现在正搞文学翻译工作,算是自由职业者,因为伤残了右腿,实在不能再从事正常工作。听他的口气,他不久前是健康的,可能是一场意外致残的。但是我从来没问过他从前种种,没问过他现在看起来完好无缺的右腿是不是假肢,怕使他陷入感伤的回忆,而且,有必要问吗?我和他往来是心与心的邀约。不过,古净尘也陆续地告诉我一些有关他过去的故事:他说他是我的校友,他毕业之后因为拥有双学士文凭(法律和中文),就选择了某大城市一家律师事务所,辗转之后,又获得了律师资格证书,腿部受伤以前,他就一直在那座城市里搞经济案子的有关事宜。文学是他的爱好,没料到有一天文学倒成了他的衣食父母。至于他为什么会受伤致残,古净尘却没透露,他说我年纪还太小,有些事以后再说给我听。
我太小吗?我时常在和古净尘别离之后,对镜子自鉴:我除了样子比较单纯之外,分明是个大女孩子嘛!我的头发又黑又长(可惜发尾有点卷曲,那些卷曲任性地不肯听我的摆步,致使我外表看起来那么不驯服),我的眉毛细细弯弯的,眼睛亮亮的……总之我并不小啊,可是转而我又不得对自己说:是的,水凝,你在他的面前是有些和你平日风范有所不同,平日里你果断、干脆,做起事来象一阵风,男孩子们不了解你的都对你敬而远之,女孩子们老在暗地里跟你比才气、比气质、比风格,你应该是那种雷厉风行的人物,可在他面前你竟忽尔轻愁,忽尔柔情万缕——你真的很‘小’呢。
陆游说‘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不知为什么,总觉海边象一块磁石,吸附着我和古净尘这两块铁器。如果哪一天我有事没去海边,我整个的心都不安宁,仿佛做借事的孩子,我会在再见面时,很小心、很殷勤地问候古净尘,并注视他的脸色,直到那张脸上浮出笑意为止。
先前,我一直以为只我一个人再乎彼此的是否如期相遇,可后来我发现,古净尘似乎也很再意。有一次,他为别人翻译一个稿件而错过了相遇,第二天他就有意无意地对我说,他如何熬了通宵才译完稿子,所以今天才来海边。感觉他的歉意之后,我就有心捉弄他,我说是不是你的故事中有了小小的波纹?因为我昨天来的时候,海风很大,海鸟们吟咏的调子不怎么欢畅。我想是它们用灵犀感受到了你内心的故事,所以才向我暗示的。
噢,海鸟们一定错怪我了,它们一定以为我是和风们一样的制造波浪者,使它们平静的日子不平静。
当然,古净尘也会因为我的‘缺席’而置疑。他会问我:是不是校园里丁香花开得太浓艳,当有人好心地送你一朵时,你不得不收受,或者,本来就执迷于花香?
而我也是一朵小花,一朵没有名字,虽然可能也芳香,但是不欢迎庸俗的蜂蝶的小花。我这样打消他的忧虑。
我们彼此间说的都仿佛是偈语,但我相信我们都听得懂对方。我和古净尘的灵魂已经彼此走近,虽然我还不敢料定这就是足令苍天变老的爱情。但是我敢说她不是友情那么简约,也不是亲情那么平凡,特别每当我不小心瞥见他的目光,看见他那么深邃的目光注视着我时,我总预感到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在半惊半喜中,我的心就象打起了鼓点,久久没法平静。
可是,我一直不敢对家人说,我在结交古净尘。因为我想父母会紧张地认为我在和一个残疾人谈恋爱(虽然我们还没有涉猎俗人的方式,只是柏拉图似地彼此经意,但不希望我的感情受到任何人的干涉)。'2
我的家事本来就多,再加上生活的担子日夜扛在父母的心头,如果我的事再掺杂进去,就会令家人更加不能轻松,就这样,我每每不声不响地走向海边,把和古净尘在的时光一分一秒地盛装起来,再回到我的氛围中一点一滴地回味,以疗救我那颗爱伤感的心。有的时候,我甚至把我的恬静传染给家人。对他们说,不要沉眠于苦境,一切都会过去的,毕竟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到后来,我和古净尘间已经不再需要任何阐释了,我们已经彼此相信。
似乎所有的欢愉都是有脚的精灵,和古净尘同在的短暂的释然,因为一件事中断了——水澄收到了一所师范大学的自费专业录取通知书。学费近八千元!这对于负债累累又没有足够能力偿还债务的家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妈妈的忧虑和爸爸的愁绪交织在家中的气氛中,使我也不能够有心情去海边。
而我的父母毕竟是天底下最伟大的父母!虽然债台已树,他们依然咬咬牙,去向亲月们东揶东凑那七八千无钱准备送走水澄。可是,亲戚们都不肯借了,并且刻薄地对妈妈说,别以为孩子长大了,就一定会感激你们今天的努力,除非他们是真正的人才。可是,你们都这么平常,他们又怎么成材呢?
后来,妈妈的一位同学答应借给母子八千元钱,妈妈就在约定的时间,穿上她以为最干净、体面的衣服,手里拎着一个可以装现金的防雨绸包,步履重浊地去见那个人。为了减轻妈妈的心灵重负,我跟着妈妈,尽管她不让我去。因为我觉得我已经长大了,我应该帮父母分担一切忧虑。
于是我看见了一个我永生难忘的场面:妈妈的大学同学头不抬,眼不睁地问候了妈妈,之后坐在老板椅上拨了一个电话,就有一个男人走了进来。大学同学对那男人说:你去带她们取八千块钱,要有收据和欠条。男人点头说好。大学同学又对妈妈“语重心长”地说,我现在赚钱也不容易,要不是觉得你挺可怜,我也不会帮你,这样吧,我这儿也挺忙,你拿了钱就别来找我了,免得我老婆见了不高兴。两年后我连本带利收回这笔钱,你看行吗?妈妈感恩戴德,不住地点头说是。这时候我在一边始终冷冷地看着这一切,一方面我为妈妈的委曲求全感觉丢脸,另一方面我又恨这个帮我们的人,他的神情分明是在同情一个讨债鬼。然而我又很心痛,母子这样有文化有素养的人,竟然为了儿女如此委屈!这些都是我们儿女的无能所致啊!
但是妈妈在回来的路上却一直很感激那位大学同学,以致于我觉得她回家路上的步履都轻盈了。妈妈说,一个同学能给我这样的帮助,已足见他是个有良心的人了,他会因为帮助我们而得到福泽的。是的,都说,血浓于水,但从亲戚们的表现来看,有时,血未必是浓于水的。
爸爸妈妈很开心,他们看来,也许委屈远不如儿子的学费有着落了重要,他们的想法是:水澄是一个优秀的男孩子,应该让他有机会深造。只要他最终能有一个好的前途,在文学上有所成就,真正象他的老师们说的那样,成为一个大文豪,他们不在乎这短暂的困苦和覆压。
在现实生活中,没有钱看起来事小,事实是难煞人,我深深地懂,所以此后每当念及父母的窘迫我都会哭,我暗暗发誓一定要走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