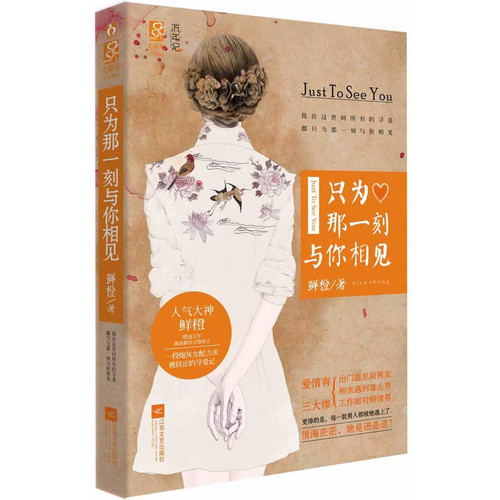那一泓薄荷色的浪漫-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月亮公公而不是婆婆。
噢,那么说,我奶奶说的故事没错喽,的确是日、月这两兄妹是妹妹白天见,哥哥晚上来?我有意逗她开心,模仿奶奶的口吻说,嗯,妹妹是女孩子嘛,你知道,神仙都不喜欢花钱买衣服,所以妹妹别怕‘张三’(狼的讳称)追赶她,就让哥哥夜晚出来。
你奶奶说的?章忆荷忍不住笑了:你奶奶真逗,神仙会没有衣服穿?会怕黑?
奶奶就那么说得嘛,叫她找出科学根据来,她竟搬出她的奶奶来证实这个说法死去的人都认可了。无论我怎样告诉她,人家神仙是无所不有的,不花钱是因为人家视它们如粪土,可她总说月亮兄妹很穷。
章忆荷笑得更厉害:三儿,你真会惹人开心。转尔她说,你是不是找我有事?
没事啊,我说,我本想找月亮公公唠嗑,可我刚一张嘴就发现他老人家正忙着,原来是被二姐找去唠嗑了,我想啊,月亮公公年纪大了,一个晚上只能听一个人倾诉,既然你先说了,我就等等吧。
你想说什么?章忆荷说,我来听。
我想说,我家住在乡下的时候,那头猪因为‘屋子’太小了,动辙就揭杆起义,不是用嘴巴掀翻食物槽,就是用嘴巴拆墙,以破坏一个旧世界的办法威胁我放它出去,然后呢,它就前爪趴在墙上,向我示威——好可怕啊。现在,这样的日子总算过去了。我家进城多年了,可好想乡下的日子,乡下的猪。由此我悟出一个道理:人在某种程度上,有喜欢被虐的倾向,这就好比我们明知爱很多时候与痛苦并在,可我们都从没停止过追寻她。
三儿,忆荷忍住笑说:你能不能说句真心话,比如你爱上你的白马王子之类的,好让姐姐我也换个心情?
No,二姐,我说,我不喜欢白马,它白得寒冷,我喜欢红马。
好吧,那么就说你的红马王子。红马王——子——哎呀!我故意看看表:二姐,已经十点了,我们得跟月亮公公说Good…by了,因为再晚些时候回去,吴大爷一定又说‘一个女孩子,晚上不知道回宿舍,真不象话’啦 。
可是三儿,我今天好闷,我想找个方式发泄。章忆荷不肯离开。
发泄吗?我拉起她:跟我来!
我从宿舍门口偷偷骑车傅筝的自行车,让章忆荷坐在我背后,夜风呼呼地吹着。我们围着校门切近的巨鹰雕像,飞快地旋转。路灯已经淡灭了,唯有星光灿烂。我带头唱起《春水流》:春水流,春水流,别把春天悄悄地带走。想你在心里头,想你在心里头,别让风把梦带走……春水流啊流,往事不回头,跟我走!
开始的时候,是我的声音较高,可到了后来,我只能作和声。
三儿,太快乐了!章忆荷兴奋地说,真棒!我的心情象小鸟一样飞起来了!
那么,我们还要不要再来一曲?我问。
别了,章忆荷说,你都冒汗了。
那有什么?阿B唱得好: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就受不了!我开玩笑说。
什么?!你就受不了?章忆荷笑拍我:那么,我们再来!
当我们终于疲惫地靠在鹰塑旁大口地喘着粗气时,表针已经指向十点半了。我对忆荷说,今晚我们两个象是吉卜寨女郎在舞蹈,好疯狂,记住,明天一定三缄其口,不然,我们一定被当作‘精神病’了。
章忆荷不服气地说,‘精神病’多好?那是人类的最高境界。因为已经可以不为世俗所扰。
去你的二姐,我可想正常点,我指指表针说,这下该回了吧?不然,狼的同类会吃我们的。
但是,你难道不想听我的故事?章忆荷并不急于回招待所。
我们先上楼再说,我催促她,不想听才怪呢。
于是,我和忆荷打开一楼的窗子(这扇窗子我们做过手脚,为了方便晚上出吃夜宵),蹑手蹑脚地跳进楼里去,再偷偷上楼。还好,吴大爷上了年纪,什么也没听到。
不料,我们在二楼的少发上才坐稳 ,吴大爷就跟了上来,一道刺眼的手电筒的光就象如来的照妖镜,把我和章忆荷团团笼住了。
干什么去了?吴大爷粗声粗气地。
我灵机一动,说,她刚打完吊针。
噢,他不信任地扫了我们一眼,说,还不上楼睡觉去?
你先休息吧,我和章忆荷讨好地,我们待会儿上去。
总之,你们别捣乱,吴大爷说。之后,他下楼了。我暗自庆幸他没有追问我们怎样进门的。
原来,章忆荷 早在这学期开始。就跟苏楠提出分手了,她是觉得葛矜太柔弱,更需要苏楠而已。可就在她想方设法疏远过去的时候,她撞见了苏楠和葛矜的对话。那天下午,苏楠和葛矜在屋里,从外边归来的章忆荷走到门口,就听苏楠说,葛矜,期望这一次别后,我们是绝好的朋友,因为我不能再伤害章忆荷,我看得出她还无法走出伤心,再说,她的病……于是,葛矜伤心地哭了,扑在苏楠怀里良久,才说,好吧,不过,我会等你。
他们以为我很可怜,三儿。章忆荷生气地说,我本来同情葛矜,才牺牲我的恋情,退出这个故事,可她呢?她等待苏楠,今生今世,也就是说,我死的时候,她仍然是苏楠的恋人。她把我这个垂死的病人看成了什么?乞丐吗?为了获得苏楠的爱情,我求她把苏楠让给我?
二姐,我打断她:大宝贝也很关心你啊,刚才,她几乎找启蒙了所有的休息室,为了想和你好如初。再说,你哪里生命垂危了?
是吗?章忆荷有些吃惊。
我知道你不会怪大宝贝儿,我说,你只是旧情难忘,是不是?
咳,初恋是美丽的,三儿,有一天你会知道。你见过一朵花的初绽吗?那时候,一切妙悟都在其中,真的……章忆荷叹息着说。
哎呀,我不耐烦地说,我可不明白你说的那些,爱情是谁家燕子我都搞不清楚呢。但是,往事既已成追忆,就不要苦苦纠缠你那有限的精力,开心起来吧。
我一辈子也忘不掉他。章忆荷喃喃地。
你一辈子遇见的男孩子不只他自己。
而我仍然忘不了他。
想另一个人就忘了。我说。
谁?章忆荷惊诧地抬起头。
朱杨啊,我说。
马达?章忆荷一个劲儿地摇头:你饶了我吧,三儿,他简直是半截木头!
木头有木头的好。于是,我把我所了解的朱杨描绘了一番。末了又说,你会爱上他的二姐,他将是你的永恒磁场,专吸你这块顽铁。
瞧你的样子像是一个先知,章忆荷若有所思地说。
是啊,在你的这件事上,我就是一个先知,相信我,没错的。
章忆荷不作声了。
夜很深了,我和章忆荷才上楼休息。
第二天早晨,我和章忆荷正红肿着惺松睡眼下楼吃早饭时,吴大爷拦住了我们:你们两个昨天是怎么进门的?
我和章忆荷互换了眼色,心想:完了,不招不行了,他只记得昨晚上我们回来得晚,却忘了我们是在关门前回来的。
您忘了吗?我曾告诉过您,我留在一楼为他们开门的,葛矜走过来说。
吴大爷白了我们几个一眼,回到他的值班室了。
又逃过了一次围剿,红军真不容易!我夸张地拥住葛矜说,谢了谢了!今天早上我请你?
算了吧!葛矜说,你们两个脸也没有洗过,牙也没刷,是不是真的醒明白了都很难说,谁敢吃你们请的饭,一旦你们吃完了忘记付帐的事,我们不是很不划算!
我们没有洗脸吗?我问章忆荷。
嗯,章忆荷‘老实’地点点头,又对葛矜很不完美地笑笑。
哎呀!我捂上脸孔说,我的脸丢了!
在这儿呢,章忆荷忍住笑说,我的手帕醮了水。
上课的时候,章忆荷有心跟葛矜同行,我在她们周围转了几圈,发现她们把我当成了花蝴蝶,应该说的话却没有出口。
大宝贝儿,二宝贝儿想跟你说句悄悄话!我打开局面说。
章忆荷的面孔立即红了,但是她随即说,是的,大宝贝儿,我想告诉你,医院那群医生真是笨得四脚朝天,他们竟误诊我是白血病。
这是真的?葛矜乐不可支。
真的。章忆荷说。
今天的天特别好,是不是?我钻到他们中间,各挎住她们一只胳膊说。
好什么好?有雨点呢!章忆荷用手指戳了一下我的额。
是老天感动了嘛!我找借口说。
天上真的飘起了雨丝。4
目睹着一天乌云散去,葛矜、苏楠深情款款的样子,我感觉很快乐。虽然,章忆荷不免会伤怀,但是我已经私下里告诉朱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如果此后章忆荷有忧伤而你不能设法抚平,你就不要来见我。实在有事找我,就戴面具,因为我实在不喜欢看一张失败的脸。
可是,她太滑不溜手了,朱杨向我无奈地叹息说。和我们处久了,他也变得幽默多了。
我不管,总之你只能胜不能败。我说。
那天我是在水房里跟他这样说的,当时,朱杨在水房里待了很长时间才上楼,我认为他是在痛下决心,要把章忆荷追到手。
他的确丰富了章忆荷的生活,看得出来:章忆荷的心在慢慢疏朗,就象一条冰封的河,经过春天的浸润,它终于水流汤汤了。
在欢乐的人群中,我始终是一个游历者和旁观者,我沉重,但不悲哀,我平静但不是没有波澜。我也总会寻找路径释放一下愁绪,当然,我每每都会去海边。可是,我发现古净尘似乎距离我越来越远,我时常被一个人搁置在海滩,孤独地品味和注视着海,甚至触摸不到他的思想。因为有时候,他根本不来海边;有时候他对我的话敷衍塞责,完全没有从前的默契了。我试着问他是否家里有变故?他说:‘没有’。那么是你的腿……我小心地。别管我!他忽尔就恼怒地说。看到我万分委屈地伫立一旁,他又会伸出有力的手,把我小小的手掌合在掌心说,水凝,别怪我,我心情很乱。
但是,我们相识这么久,有什么事情,我至少会帮你分忧,为什么你不肯把它分一半给我呢?我为他的道歉软化,遂温柔地说。不,他坚决地说,你已经使我很安慰,每天都这样耐心地陪我散心,我不应该再让你烦忧。我正要说,我不是单纯体恤你才来海边的,我也需要你的了解和关怀,释放我心底的那些尘埃。他就打断我的话,象许多时候一样,评价一朵云或者一只海鸟。
这些事在无形中都增添了我心灵的重量。在这种心情的指引下,我根本无心去理会很多。所以,当傅筝突然哭着来找我时,我几乎惊呆了,不知道在平静的日子里,还有不平静的事发生,犹其是发生在傅筝的身上。傅筝哭得很伤心,她告诉我:她跟父母吵架了,妈妈还打了她。这是生以来她第一次打我啊,她感觉相当心痛。
吵架的原因是令我意外的——傅筝和燕善茁在谈感情,就在第一串香椿坠落的时候开始的。因为傅筝单纯无邪,总对妈妈无话不说,谈论燕善茁如何会哄女孩子开心,他的周围女孩子如何花蝴蝶一样穿梭,所以妈妈认定他是个花心男孩子。犹其听说燕善茁家住在乡下,父母无权无势,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而且,他学电力,将来工作、住房问题、生活问题都是棘手问题时,傅筝的妈妈下了最后通碟:从此以后绝不许跟这样一个前途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