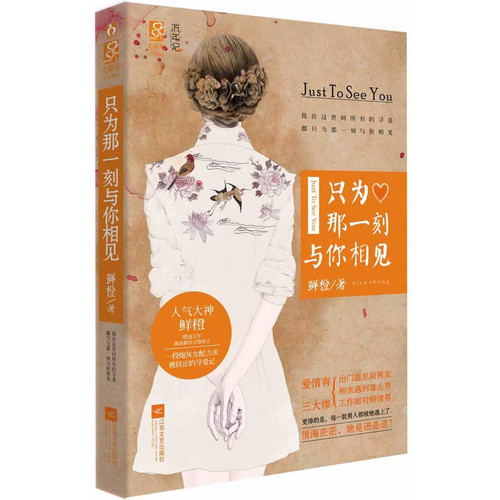那一泓薄荷色的浪漫-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好办了!我灵机一动:让倪捷、苏楠和那男孩子猜拳决定谁选择跟忆荷、我和葛矜一组。
趁他们猜拳的时候,我想起和倪捷一起进来的男孩子是朱杨,元旦晚会苏楠曾经请过他,他跟燕善茁跳的踢踏舞曾经让全场哗然。据说,朱杨的绝活是交谊舞,曾获得过上届滨城交谊舞大赛冠军。也读大三年级,也即说,他跟我们一块毕业。
猜的结果是忆荷和朱杨,葛矜和苏楠,我和倪捷。
由于我个子矮小又纤瘦,而倪捷高大威猛,所以很快,我们就第一个被罚了。
我说,我不会唱歌,钻桌子吧。倪捷立即举手反对说,男子汉大丈夫,绝不钻桌子,他宁愿唱歌。于是不由分说,他唱起了《明明白白我的心》。无奈,我只好跟他合唱。他的歌喉是富有磁性的那种,我长到二十岁还从未听到这么动听的歌,老实说,我几乎是着迷了。
歌声才住韵脚,倪捷忽地低头对我小声说,有一天你会知道我心有多么明亮地期待你。我莫名其妙地注视了他,他却若无其事地催促第二对被罚者忆荷和朱杨表演西班牙‘斗牛士’。大家都认为他们被罚的原因是忆荷是‘重量级’,而朱杨属于‘轻量级’。一看到朱杨就知道世界闹饥荒,而一看到忆荷就明白饥荒的原因在哪儿了。这是燕善茁的阐释。
真是绝佳拍当!忆荷和朱杨的表演淋漓尽至,我们的掌声雨点一样落下来。但是,我被倪捷的话搅扰得心绪不宁。
燕善茁他们四个也相继表演了绝活。
看得出,葛矜对苏楠也已经达到了如影随形的境地,而苏楠却似乎别有情衷,他时常从葛矜身边走到忆荷的面前小声低语片刻,并同她合奏一曲《梁祝》。于是,忆荷的面孔便忽尔快慰,忽尔阴郁。
热烈过后,大家便三三两两坐在宿舍里闲聊。傅筝和燕善茁却坐在床上下起了跳棋,看他们专心致志的样子,我想就是敌人的大炮来了他们也不知道。
全国都解放了,你往哪儿跑?燕善茁举起一枚棋子说。
之后,就见傅筝一下子搅乱了棋局,挥起拳头捶打燕善茁。你欺负人!她撒娇似地。
别呀,燕善茁握住她的手‘委屈’地:你体格这么差,打坏了我没关系,累坏了你我岂不是罪大恶极?
你该下十八层地狱,傅恨恨地说,对了,最好是阿鼻地狱。
哎哟,女孩子说话这么狠可不好,不过,有人说我是天堂飞来的一只鸟,燕善茁笑嘻嘻地审视着她:你到底相中了我身上的哪根骨头?除了肋骨,我身上的骨胳随你选,因为我死了,上帝还可以用肋骨再造一个我。
好,你骂我是疯狗,看我收拾你!傅筝亮起一支毛刷子:你真以为你是亚当?
救命啊!燕善茁说,夏娃打亚当了!然后,他冲出屋子,于是,傅筝也追了出去。
朱杨捧着一本凡尔纳的《地心游记》,目不斜视地品读着。忆荷怀中抱着吉它,若有所思,只爆发性地弹奏几个音符,她近来形成了一个习惯,没事就调音,那种感觉就像在想什么事,偶尔想通了,偶尔又迷惑了。
倪捷这时靠近我说,我们出去走走好吗?你听到窗外的鸟声了吗?还有花香,它们引诱我们走到旷野去。我犹豫了片刻,因为长这么大,还从没有和男孩散步过,何况是这个神秘兮兮的校园歌手?
走吧,他忽然拉了我的手,不由分说加足力气,在他的臂力下,我只好随行。
我们没有走出校园,因为我说在我眼里,没有一处比校园更美,而且我们的年轻心灵也是春天,许多个心灵之春同大自然的春天交响,就是美的极至,我们干吗不坐下来倾听这和谐美妙的乐章或者,散步在花与春日的世界里?
在校园的东南有有一个长廊,廊柱上缀满了藤生植物的枯叶和刚刚复苏的长茎。风儿一吹,枯叶就会稀疏地坠落,发出悦耳的轻响。廊的尽头有一个巨大石菇,石菇周围是草坪。草坪绿得逼人的眼,而在石菇的下面,则安放着四个小小的石凳。
我和倪捷坐下来,空气清新极了。
你听到春虫的低鸣了吗?我说,我听到了,我还看见我们不远处的一座山峰在微茫的雾气中垂下长长的绿衣,到处是小鸟,和小鸟们的和歌,还有一些蝶,它们是春天的使臣。真是太动人啦!
倪捷只是低头看脚下的一枚石子,听到我的话,他说,水凝,如果我要你从你的梦幻世界走出来,和我分享阳光,或者,滩贝什么的,你愿不愿意呢?
那可不行,我不假思索地说,阳光和海都是大家的,我怎么能和你共享?转尔,当我抬头注视倪捷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目光中有一抹很深很深的期待,我慌忙左顾而言它,我说,倪捷,刚才我一直很为难该怎样分组,没想到你帮了我,我该怎样谢你呢?
说什么谢?倪捷有些生气地说,你明知道我是有意输给他们而选择跟你一组的。
我吃惊地注视了一会儿倪捷,后者正目不措睛地观察我。
‘304’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四人组,他说,而你是她们中最优秀的。
是吗?我心不在焉地点点头,示意他可以说下去,说为什么,心里却想,他可千万不要诱惑我什么,我可不要这么小的年纪就和谁堕入情网。
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当我把你的散文《家乡的月亮》送到大赛组委会时,我就想认识你,因为我从没有见到一个人能把散文写到那种境界,倪捷谦恭地说。
我说,那天知道得奖时我就很奇怪,按照时间规定,我的稿子已经算迟到了,而组委会那时也应该开始评奖了,可我最后送的稿却能获得大赛的青睐!
是啊,倪捷说,当时我想,这么美的文章如果不能被重视多可惜啊,所以我通过组委会里的一位关系很好的老师把它推荐给大赛的组委会,于是你就没被漏掉。
我为这件事,一直不知道该怎样感谢倪捷,于是说,你帮了我,我也会找机会帮你的。
倪捷笑了笑说,过去属于死神,雪莱说过的,你还是说说你的历程吧,读你的文字总觉你很忧郁,说出来也许我会懂,因为我也心扛忧郁。
我忧伤吗?我反问他:我难道不是拥有着早春的浪漫吗,要不怎么跟一个并不谙熟的男孩子出门散步、聊天?
不,他说,你的浪漫是不轻易释放的,我知道你绝不比谁轻松。
我对倪捷的说法很感兴趣,的确,我从来没有过无羁的快乐,因为我的经历使我没有机会做一朵温室中的花朵。
我出生在一个大风雪的夜晚,我的第一声啼哭是携着早春的清寒降临父母寄居的小屋的。那天雪花大得象鹅毛。静谧的雪花梦一样围绕着我的小村庄。那时,正是‘文革’的后期。
就在我出生后不久,爷爷奶奶决定把父母逐出家门,把房产留给尚未娶妻的四叔。据说,父母那天是两手空空地抱着我,含泪走出家门的,因为爷爷奶奶不肯给他们一粒米。当然,陈年老事已成虚空,我也没必要来详述上一辈的恩恩怨怨,总之,那是些个说不清理还乱的事。而且奶奶因为当年的事,也曾留下很重的疑心病,在四婶和她闹得没有回旋余地时,她认为唯一可以给她养老的爸爸也在记恨她,所以她主动要求住进乡里的养老院。有儿有女的奶奶却在养老院里生活,这是我的父母长辈人乃至弟弟妹妹们永远的尴尬。
我们一家三口成为流浪人的时候,是早上四点钟多一点。爸爸、妈妈担心我生病,赶了五里的山路,找到一位同事家才安顿了我。此后,父母租了房子住下来。另一方面,爸爸找了一班朋友,在一处山水萦绕的地带,建起我们的新家园。等到我周岁时,我才终于坐在家园的土炕上,抓起一本书和一支笔。妈妈说:今天我所以爱写写画画,就是因为当初我还不知道我是谁的时候,上苍导引我的缘故。
可是不久(大约是一九七五年),在水渊出世后,爸爸就因为一场揪斗事件中死亡了一个人而被那些心怀鬼胎的人污陷,和妈妈躲藏在家中不敢随意出门,因为房子的周围布满了持枪的‘红卫兵’。这样的环境是不利于我幼小的身心成长的,父妈妈决定送我去另一个村子,我的外婆家寄居。外公早逝,外婆家只有患有小儿麻痹症的二姨和待嫁的小姨。在那里, 我一住就是四年。据说,我常常因为一只小麻雀的死而大哭不已。外婆说,是因为爸爸、妈妈离得太远,此外,又忙于工作不能来看我,我的心太孤单无助,所以总是伤怀。
直到我七岁那年腊月二十九日,爸爸才来到外婆家,说我已经长大,再不回家,就会成为外婆家的燕子,不肯飞走了。于是,我告别了同处四年,亲昵无比的外婆和小姨,在同样风雪交加的天气里,听着爸爸脚踏着积雪的咯吱声,一边想象着家的样子。也许是我太少不更事,那时候,我并没觉得离开外婆有多么难过,看到外婆和小姨不舍的泪,我还劝她们不要那样,我说我还会回来的。直到后来亲爱的外婆离我而去,我才真正地觉出生死离别的味道,要不,怎么会有句话叫失去时方知可贵?人之于一事物的体验,直到真正亲临了,才会有明晰的感悟,否则是无法剔透的,无论这个人多么聪明。
我对妈妈已经很陌生,几乎记不清她的样子了,这四年中因为忙碌因为怕我吵着不让她走,她很难得会看我一次,印象中,只有爸爸时常会赶一段遥远的路,把他打井时捉到的田鸡烧好了送给我吃,或者,爸爸带我去打麻雀。麻雀我是不忍心吃的,我从小就对那些小生灵有种心脉相牵的感觉,看不得它们被人类残害。弟弟们在我印象里更是空白,因为父妈妈每次看我都不曾带着他们。所以当我踏上院中那小小的丘岭,走向迎面而来的亲人时,我的心灵怯怯的,茫然地注视着妈妈温柔的脸颜和弟弟们好奇而陌生的注目,我突然感觉我是那么那么想念外婆和小姨,想念那些呵护备至,平静如水的日子。
在我小小的心怀里,我也早就听外婆告诉我:一旦回家了,我就是姐姐,就不可以耍小性子,不可以常抱着大公鸡坐在门边胡思乱想。父妈妈都很忙,我应该学习操持家务,象妈妈身边的小助手一样。
以后的日子里,我的确成了妈妈的助手,我每天按时喂食家禽、家畜,做饭、洗衣,并且照顾年幼的水澄和水渊。当然,现在水澄和水渊是绝计不承认我曾照料他们的,他们有许多次向爸爸和妈妈告我的状说,爸,妈,你们当初上班都蒙在古里啊,我姐表面上忠厚老实,其实她股子里有狼性啊,那时候,她经常拎着火剪子,满院子追打我们,直到我们服了为止。我们那时简直是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咳,说起来都是眼泪啊!有一次,她丢下灶坑里的火不管,还害得我和哥成了救火勇士,只可惜是没有谁为我们授予勋章。
其实是那时候弟弟们都特别调皮,我这个天上掉下的姐姐让他们感觉太神奇了,所以,变着法儿来逗我,因为我要干家务,我就特别烦他们捣乱,所以有时候我急了会去反击他们的挑衅。那一次我去追他们时,忘了把灶坑收拾好,结果火苗一下子串出来,把灶房里其它的可燃物都点着了,看着有一人多高的火苗,当时我们姐弟三人都傻了,幸亏我们三个人都比较聪明,有的拿铁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