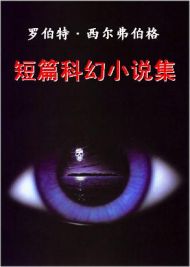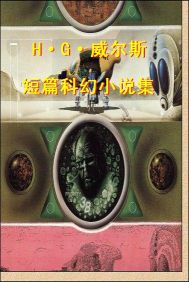外国中短篇科幻小说1000篇 (第八辑)-第15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起来,“你有那个晶体吗?”她问。我从口袋里掏出晶体给她看。她拿到手里,握住它,然后睡着了。
整整一夜,我不停地擦着她的脸,握着她的手。黎明时,我脑子里传来了通讯杆的声音,我打开通道,一个图象出现在我的脑子里:一个披着长长的黑发,宽鼻子的黑色男人坐在沙发,他穿着一身联合海军陆战队的制服。
“我是上将爱米尔·杰弗勒,”他说“我知道你有属于我的东西。”他的声音烦躁不成语调,缺乏节奏感。他的图象是计算机生成的。
我把手伸进口袋里摸着晶体,“我认为你搞错了。”我回答说。
“让我直说吧,”他说,“我想让那个女人回来。”他的话使我大吃一惊,我失控了。“我向你提个建议:派一个人去带回她,要花去我20万元,如果你能亲自把她送还给我,这对我们俩都容易。我必须要她。接受20万吧,把它作为我的酬谢。”
“你要对她怎么样?”我问。上将注视着我,没有回答。我感到这样问他显得我太傻了。
“她病了,”我说,“这几天搬动她是有危险的。”
“这几个月她让我做了徒劳的搜索,必须停止了,你要在日落之前把她带到克隆机场,你明白吗?”
“是的,我懂。”
他似乎审视了我一会,好像他能看到我。“你不会做出任何荒谬的事情吧,是吗?你不是想逃跑吧?”
“不。”我说。
“你知道吗,你是跑不了的。逃走不是办法。”
我说:“我明白。”我不能确定是否要相信他。
尽管他在情报机构工作,但联合地球海军陆战队在地球上活动是不合法的。但我知道这不能阻止他。作为靠机械维持生命的情报机构司令,他能左右军队的联合会,也有晶体脑的来源。这种晶体脑集聚了比一个生物脑能处理亿万次更多的信息。我没有其他方法使我的银行存款达到我需要的数目。打个电话吧,穿过边界,躲过警察的监视。
“好,”杰弗勒说。“我会善待她的,是为她好,我也是人类的一员。”
“我将不会跑的。”我说。杰弗勒切断了通话。我坐在沙发上,感到自己是封闭在盒子里。我仔细考虑着他的每一句话,研究每句话的含意。他最后的一句话还算带点感情。或者说,至少有点感情。我给塔玛拉擦脸上的汗,直到我筋疲力尽为止。
天亮两个小时了,弗兰克从屋里出来,“哎,安吉洛”,他说“可能黑天使来找我了。我拥抱了他。我经常希望我的祖父真的发明了一种酒,一种能让人醉而又没有危险!”
花个小钱而得到更大的欢乐。我随意地哼着过了时的歌曲。弗兰克坐在床上,我用手抚摩着塔玛拉的头发。寻找着受伤的地方——没有任何外部痕迹,她已经成了一个脑移植者。没有伤,并不是没有什么。一个好的芭蕾舞演员不会留下这样一个形象。我说:“你必须为我看好塔玛拉。”然后去安排早饭了。我用油炸了一些法国斑豆。一种用褐色豆子做的。还有炒饭。打开好多香喷喷的炸面饼圈。还有调好的咖啡。
不一会,弗兰克走进厨房。“她和天使们在睡觉。”他说。
“好吧。”我递给他一个盘子。他装满了食物,坐在桌子旁吃起来。有好长时间我们谁也没有讲话。
“我能知道你的想法吗?”我还没有醉到连在哪个饭店接的电话都记不起来的程度。也许我们应该把这个女人转移到我家去。
“不,如果他呼叫你,他就知道你住的地方了。”
“那么我们把她转移到某个其他地方吧。我们把她藏在香蕉园里。”
“去果园,那太好了,”我说。
我默不做声地吃起饭来。我拿不准是否我应该告诉弗兰克关于从杰弗勒那接到的电话。弗兰克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一个好人。但他的内心里是一个贼。也许他能把塔玛拉卖了作为报酬。
“什么事使你烦恼?”弗兰克问,“你害怕把她藏在香蕉园吗?”
我的手在桌子上的旧塑料上不停地划来划去。塔玛拉起来了,去了浴室。我听到她洗脸的水声。
“不,”我昨天给她作了抗体治疗,那很危险。她可能因它而死。“怎么可能呢?”
“我不知道,可能是她发高烧。”
“我有点担心这件事。看上去不那么乐观。有人从你脸上就能想到,你是一个狂妄自负的人,你的主人就要快饿死了。”我笑了一会。“看,事情不那么太坏”弗兰克能将每件事情都办好。当塔玛拉进来时,我打算试探她,看她是不是一个避难者。弗兰克给我递了一个眼色,什么也不让我说。
塔玛拉摇摇晃晃走进厨房,他低着头,“我要离开了。”她宣布说。
“我们知道,”弗兰克说,“我将和你一起走。我们和那些避难者一起藏到果园里。没有人会找到你。”
“你们不知道我从谁那逃出来的,你们不知道他们的厉害。”
“那不算回事!”弗兰克说。没有人监视果园——避难者来去都很方便。成千上万的人住在那里,而且不检查身份证明。
塔玛拉说:“我不能肯定……”
“啊,但你可混在避难者中。”弗兰克说,“像我一样,你恶狠狠地盯着周围。”
塔玛拉凝视了他一会,好像在想这个笑话的某种深刻含义。然后苦笑了一下说“行了。”就开始吃饭了。“说到避难者,猜一猜,我昨天看见了谁?”弗兰克说:“伯纳多梅兹教授。”我听过这个名子,但记不得在哪听过的。我看了一眼塔玛拉,我们俩都耸了耸肩膀。“你认识伯纳多梅兹?”他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工程师。他在智利于了许多好事。他指出在三代之内利用遗传学工程在人工繁殖过程中消除贪梦的特性!我在弗尔亚的大街上见过他。他带着他的想法去了哥伦比亚,那里的人给他做了脑切除手术,并且把他作为避难者的典型驱逐出边界。他们不喜欢他的狂暴主义思想。因此,他们切掉了他的大半个脑子。现在他在大街上闲逛,傻呆呆地往裤子里撒尿,偷东西吃。”
塔玛拉停下不吃了,转过她那苍白的脸说“也许他是一个梦幻享乐主义者”,我说:“也许他们给他做了脑切除手术造成的。”
“啊,不!”弗兰克说,“那是一个哥伦比亚人,我有一个朋友知道的更确切。”
塔玛拉说:“没有人能肯定什么。”
弗兰克对我眨了眨眼睛。得了得了,玩世不恭够了。这只是早饭时间!看到一个伟大的人变成这个样子是一种耻辱。现在他还不如一只鬣狗和一只鸭子好看。”
塔玛拉说:“我们不谈这个吧。”她默不做声地吃完饭。我们打点一些食品和衣物去果园。后面没有人跟踪我们。我们走了很长时间没看到一顶帐篷。突然,我们找到一串帐篷像个小村子。这些帐篷没有一顶是属于游击队的。他们离东边还远着呢。弗兰克走进一个帐篷,这是仅有的四顶紧挨着的帐篷里的一间。这些帐篷既脏又有霉味。有两顶帐篷上有白色的废物,夜里小鸡在上面过夜。一顶帐篷外面有一个光着身子的小男孩坐在洗衣盆里,盆里只有一点点水。这个小孩还没长牙。嘴里有一块碎布他正津津有味地嚼着,嗡嗡的苍蝇在他头上飞来飞去有的爬他的脸上。弗兰克叫着一个帐篷的门,一个年轻的智利女人出来了,她散开的衣服正在给一婴儿喂奶。弗兰克问她,塔玛拉是否可以在那个地方搭个帐篷。这个女人告诉他,一周前一顶住人的帐篷不见了,因此他可以住在那里,通常这些失踪的帐篷——很多避难者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当找到时就被害死了。警察漠不关心。对此也不做任何处理。弗兰克和塔玛拉把帐篷搭得很好看。因此,我又回到费尔亚去工作了。
费尔亚那天很拥挤。我喜欢这样子,一大堆密密麻麻的人群——有朝鲜的海员,也有印度商人和南美游击队员,都到这个地方。我站在人山人海的大街前,看着他们身着不同的服饰,没完没了地在街上转悠。空气里充满了汗味,尘土味和食品的香味。有人高声喊着进行着易货贸易。我非常喜欢费尔亚的这番景象。所有进城里的人行道都只有一条挤满人的路。如果行人要去街对面的商店,就得跟着行人一起走过去,然后再往回走到要去的商店。所有的人都朝一个方向走,使我很厌烦。如果给他们都套上钩环,我也决不会发现他们有什么不方便。我想起了我第一次来巴拿马的情景。正是这些无精打采乱转圈的人们吸引了我。我一直在想:我喜欢缺乏秩序的巴拿马。当想起前天晚上弗兰克说的话。我奇怪我不是享受能够转身的简单自由。而是要和人群对着走。也许这就是我能自由的一种方法。
中午,弗兰克来了从街上的铺子里买了一个水壶。他停下来和我说了几句话,他说:“当我告诉她关于伯纳多的事时你看见她脸上的表情了吗?”“是的她很难受。”我说。
“肯定她是一个避难者,不是吗?”“是的,她看上去很难过。”我说。弗兰克笑着对我说晚上来,买点水果。我答应了他。我把晶体交给了他。让他把晶体卖掉。他说他试试看。我的生意不错:我卖了一个生命延伸的药。一个多月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所以我一直在店里待到天黑,希望有更好的运气。
弗兰克的帐篷是在运河的快车道南面114排。大约在克隆西边3公里处。我摸着黑走到那,提着从费尔亚买来的一篮子水果和矿泉水。香蕉树和温暖的土地闪着足以看得见的光亮。我来到帐篷时,看见一个身材宽大的黑色男人在离弗兰克50米远的地方,微微弯着身子好像在撒尿。我想别吓着他,悄悄地走过去看一看。但当我走近时,看见他弯个身子正在移动弗兰克,原来他正在解一个套在弗兰克脖子上的绳索。他勒死了弗兰克。我叫喊起来。这个人看见我,转过身子向我扑来,我跳起来,闪到一边。他跑了,我摸了摸弗兰克的脉搏,他已经没有脉搏了,我给他做人工呼吸,他咯了一声,血从他的喉头下的一个洞里泪泊地流出来,我把两个手指伸进洞里看有多深。我的手指够到他的脖子后面,触到了他受伤最重的脊椎骨。我慢慢地站起来,要呕吐。然后大声呼救起来。
智利女人从帐篷里出来。塔玛拉也出来了。这个女人看到弗兰克死了又奇怪又害怕。她嘴里不停地嘟噜着,用手在胸前画着十字架。塔玛拉一动不动地眼睛呆呆地看着弗兰克,由于恐惧嘴张得特别大。
我非常气愤,跳起来追赶杀害弗兰克的凶手。我跑了大约五百米就看到他藏在香蕉树后。我一直向他跑去,他从树后跳出来挥舞着一把刀,向我冲来。我拼力照着他的膝盖骨重重地踢了一下。
刀掉了,他跑开了。我捡起刀,紧追不放。他没跑多远——手一直摸着他的膝盖。一瘸一拐地走。这时我感到心里轻松些。我呼吸也有节奏了。我想:扑向那个男人,把他从大腿处,一撕两半,那一定很容易。他可能过低地估计了我。以为我老了,软弱无力。但是,我感到我像一头刚刚被发现的老狮子,他还有一颗用来杀人的牙。因为,我喜欢这个时刻。我不慌不急,想让他对我产生恐惧。我想让他知道,他死到临头了,他必须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