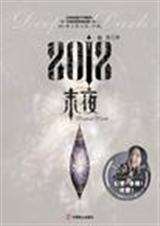2004年第01期-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一夜,还很漫长,欢乐才刚刚开了头,等我们的汽车冲出围困驶进城里之后,整个柳林城都在舞蹈着,整个柳林城都在“跑秧歌”。只有我们置身于欢乐之外,只有我们这一行人是这小城的外人。欢乐挤得我们几乎没有立锥之地了,不一会儿工夫我们就已经在“跑秧歌”的队伍之中了。我们笨手笨脚地碍着人家的事,可是人家不计较,人家这不计较之中有着对一个局外人的宽宏大量。我们混杂其间,扭着,跑着,可是不顶用,我们仍然是人家生活之外的旁观者。
这就是真实的生活和旅游制造出的生活假象的不同,在一个旅游地,一切欢乐都是为你而设计的,都是为了取悦你袋中叮当作响的金钱。但这里不是,这里的欢乐还未被开发和利用,可我也清楚地知道,请我们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一切,把这没有被污染的宝藏,盘子、跑秧歌等等,“开发”成旅游的“资源”。
我手里有了一把彩扇,不知是谁塞给我的,彩扇是我的伪装,“迷彩服”一般,使我能够混迹于人家的队伍里不再那么显眼。可这彩扇在我手里比兵器还要笨重,人家一个个彩蝶翩跹,我的彩蝶则没有翅膀,。可别小瞧这“跑秧歌”哟,起初,我也以为我是会“跑”的,中国人,50年代生人,谁不会扭秧歌呢?哦哟哟,大错特错,在这里,跑秧歌;讲究大着呢。你听听那队伍的名称:十二连城、蛇盘九颗蛋、天地牌、龙摆尾,真是气吞山河,还有那小小一柄花扇,撒、抖、推、拉、挽、操,无数的花式啊!那花扇是会说话的,会笑,飞着媚眼,特别是,在男人们的手里,一柄花扇使平时看上去呆头呆脑的汉子风情万种!花扇和花扇,心有灵犀,传着情,漂亮极了,说不尽的缠绵、亲爱、性感。我猛醒这原来是男人们的舞蹈啊,真是把我看呆了。
对了对了,黄河岸边的秧歌,原来是,最性感的男人的舞蹈。
露天的舞台上,有人在唱小戏。不是小戏,应该叫“弹唱”。这是一个当红的“弹唱班”在演出。一男一女两个人,扭着,唱着。唱的是什么?一句也听不清,可那曲调高亢极了,尖锐极了,是一种女人般的假嗓。那男演员,小小的个头,五短身材,几乎没有脖子,原来是个残疾人,一个驼背,而且,不年轻了,他扭着各种舞步,耍着彩扇,手指上套着大金镏子,可他的声音,却能够穿云裂帛,那是任谁也阻挡不住的高亢和锐利,所向披靡,锐利得近于凄厉,可却是欢快的。彩扇在他手里,出神入化,翩翩如飞,他端着肩膀,两臂在胸前,小幅度地一摆一摆,扭着秧歌步,忽然觉得他如西门庆般风流倜傥。这残疾的唱手他脱胎换骨了,他陶醉在这幸福的感觉之中,台下的妇女,田野上的妇女,还不知有多少人为他失魂落魄呢!
他唱了大半夜,他的嗓子可真结实啊,在喇叭里,那高亢的声音更是尖脆凄厉得不 得了,整个柳林城都被他的歌声笼盖了。那曲调听上去十分简单,总是重复着,重复着,好像在重复着一句要紧的、要命的话,那是句什么话?我听了大半夜,仍然一无所知。
几十里外,沿黄河向北,在临县的地界,今夜,一定也是个狂欢夜,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城镇,到处是“跑秧歌”的队伍。不过,那里跑的是“伞头秧歌”,许凡的秧歌。伞头们打着伞,是秧歌队的灵魂,他载歌载舞,又扭又唱,他一张嘴,唱词就像小鸟一样飞出,全是即兴的唱词。只是,我晚来了一步,晚来了几年,那个叫许凡的伞头,八年前过世了。在他过世八年后的元宵节,我听说了他的名字。八年后的正月十六,2003年,在柳林,在这个驼背的残疾艺人身上,我好像看到了许凡的影子。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奇异的光芒,让我痴迷。
二、回到多年前
这个叫许凡的一开口就把人惊呆了,他这么唱,他说:
姓许名凡实不凡,
范丹老祖把家业传,
天下欠账要不完,
我不上门他不还。
范丹老祖是何许人?据传,他是东汉时的一名学者,有官不做,为赈济饥民而散尽了家财,最后连祖上遗留下的外欠账目也散了出去,让饥民们上门去讨账,后来,这范丹先生就被天下的乞丐尊为——老祖。
现在,我们知道了,原来,伞头许凡是个乞丐,叫花子。
在伞头秧歌的发源地,“伞头”是备受尊敬的人物,他们在地方上都有一定的地位,或是在乡间有口碑和德行的人。著名伞头中,有旧时代前清时的县太爷,也有新时代人民政府的县长,叫花子做“伞头”的,许凡是第一人。
叫花子做了伞头,做了挑伞人,一点不避讳自己卑贱的出身,他笑呵呵地告诉人家:
落盘菜,摇壶酒,
天南海北任我走,
盘龙大棍挽在手,
打遍天下咬人狗。
这真叫人欢喜啊,还以为是走进了金庸古龙们武侠小说的世界,走进了那个侠客仗剑走天下的“江湖”。这个挑着伞一路扭来的叫花子,快乐的乞丐,若是活在那个虚构的“江湖”一定比活在真实的卑微的生活中容易。
他为什么这么快乐?
是啊他为什么这么快乐?
有这么多不快乐的人,一个快乐的人,一个没理由快乐却偏偏快乐着的人就变得十分突兀和醒目,甚至,蛮横不讲理。
我永不会知道这个快乐的流浪汉他内心的秘密了,我想像他沿着黄河一路向南,那时他还是一个少年,也许只有十六,也许只有十五。这个少年人埋葬了亲娘就离开了家乡,离开了那个叫许家峪的村庄。在那个村庄,许家并不算穷,有田产,有房,门楣上刻着“耕读传家”的古训,大热天,他和父亲在地里给桃黍锄二遍苗,毒日头没遮没挡地顶在头上,把人和苗都要烤熟了。从前,日本鬼子没来之前,许家农忙时还雇得起一个半个短工,可如今家境一天不如一天。父亲锄在他前面,土布汗衫早已被汗水湿透了,紧贴在弓起的背上。父亲就这么锄啊锄啊锄了一辈子。他撂下了锄头,事情就这么决定了。
他不喜爱土地,他不喜爱把人捆绑在土地上的生活,他不要他爹这样弯腰曲背的一生。
这个少年人,像青桃黍一样刚刚长成,国字脸,眼睛干净明亮,又大又黑,下巴翘着,总是抿着嘴角,这使他看上去有一点少女般的羞涩。他来到了碛口,投奔亲戚。亲戚在碛口城里有买卖,开着货栈。店堂里黑乎乎的,一股熟皮子的臭味儿,亲戚做的是羊毛和羊皮的生意,这你只要走进后院一眼就看得出来,羊毛堆成了小山,一口一口大铁锅里,石灰水也许是火碱水浸泡着还没有熟好的皮子。这一晚,他睡在货栈里,又热又闷,虼蚤滚成了蛋,皮毛腥膻的臭味熏得他一阵一阵反胃。天刚蒙蒙亮,他悄悄溜出了货栈的大门,在还没有醒来的小城游荡。后来他来到了码头,他看到了船、油筏还有河水。河水是那么新鲜,被一点一点升起的太阳慢慢涂成浓郁艳情的金色。他喜爱这动荡艳情的河水。他掏出盘缠在刚开张的小饭铺里买了几个“油旋”,“油旋”很香,他一口咬下去一下子涌出泪水,自娘去世后他还没吃过这么香的饭食呢。他快乐地享受着他的美味跳上了一条木船,他问船老大:“这船去哪儿?”这个少年人他不知道,这是一个决定了他一生命运的早晨。
几年过去了,有一天,许家峪来了一个衣衫褴褛的叫花子,一进村,狗就冲着他汪汪叫。他愣了一愣,心想,“狗都不认识我了。”他手里拖着一根打狗棍,可这棍子说什么也打不得自家乡亲们的狗啊!一个老人盯住他打量了半晌,突然走上前去,“啪”地甩了他个大嘴巴,老人啐了一口说:
“你个鳖骨子小子你还知道回来呀!你害得你爹死也没闭住眼啊!”
说完老人就蹲在了地上,抱头痛哭。他认出了这是他叔伯大爷,他愣怔了半晌,像是没听明白老人的话,忽然这叫花子撒腿就朝家门跑,一群狗追着他狂咬,裤腿被咬下来了,狗嘴里叼着破布片跟在他身后飞跑着——可他就是跑得再快也追不上他爹了。
爹坟头上早已长了草,和他娘的坟紧挨在一起。许凡在他爹娘的坟前长跪了一夜。他想起最后一次和他爹锄桃黍,一人两行,爹锄到头总是返回来不声不响接应他。他号啕大哭,那一夜,全村人都听见了村外这锥心的长嚎。许家门里的上人们,听着听着也流下了泪,他们想,得把这鳖骨子的腿给拴住了,也好让他爹娘九泉之下安心瞑目。
那是许凡此生最后一次酣畅的痛哭,他把一辈子的哭一口气给哭完了。几天之后,他走出家门,剃了头,洗了脸,换了干净衣裳,哟嗬,好一个光眉鲜眼的俊青年!村里的年轻人,从前的小伙伴们呼啦啦围上来了,都想听他的故事,他们叫着他的小名,说:
“三儿,这些年你到哪达浪去了?:
他笑而不答,再问,问急了,他忽然冲口唱起了秧歌:
三尺短杖手中拿,
浪迹江湖走天涯,
嗨啦啦啦嗨啦啦,
活到哪达算哪达。
后生们愣住了。他唱得字正腔圆,多么好听啊。他的声音,明亮,高亢,微微颤抖,还有点懒洋洋,明亮得就像蓝天上的一朵云,山坡上的一群羊,后生们被他唱软和了,他们望着他,心想,这鳖骨子是见过世面的人了。
“许凡,这些年,你在外面一定遭了不少罪吧?”有人试探着问。
“咳,”他笑了,说道,“这些年,在家的人,莫非就不遭罪?”说着他眉毛一挑又唱起来:
日本鬼,坏心锤,
谁晓得造下多少罪?
贺家坳把人糟害,
龟峁村开过一赤屎会。
后生们不言语了,原来他出门在外,家乡的事倒也知道得不少啊。贺家坳、龟峁村都是本乡本土的村庄,那里的人谁也没有迈出家门一步,贺家坳全村二百号人,躲进地道里,被扫荡的鬼子用柴草、烟叶,拌上辣椒面点火熏烤,男女老幼,二百多号人,活活熏死在了里面。二百多生灵啊,有的“戏咪”①,还在娘怀里吃奶,还是个人芽,有的老人,活了一辈子不知道县城的门朝哪边开。还有龟峁村的老百姓,被鬼子逼到了场院里,人人脱光了衣服,一丝不挂,赤条条开会。光天化日之下,全村几百号人,公公媳妇,爷爷孙女,刚过门的新娘子,十七八岁花朵般干净的大姑娘,人人赤身露体,女人用手捂着自己的私处,老人闭上了眼,鬼子上来一刺刀就把闭眼睛的老人给捅穿了。
“嘿嘿,说点高兴的事吧,”后生们说话了,大家都不愿意去想这伤心的往事。天瓦蓝瓦蓝,干净极了,村庄也显得很干净,没有被庄稼覆盖的土地,一片鲜黄,那鲜黄撞得人眼疼。“许凡,你和女人睡过觉吗?”女人总是能叫人高兴的。
“当然睡过。”许凡懒洋洋回答。
“是城里窑子里的女人不是?”
“猜!”
他们顺嘴瞎猜一气,说东说西,猜不着。
“啊哈,”许凡双手朝脑后一枕,躺在了阳坡上,阳光晃得他睁不开眼,他就闭上了眼睛唱起来:
钻神堂,睡古庙,
女娲和我常睡觉,
身挨身,脚相靠,
黑间全凭她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