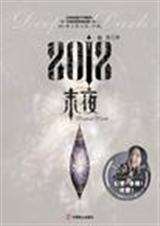2005年第06期-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陈世玉书记的死讯让老王感觉有些恍惚,多少有些万念俱灰,不过这种万念俱灰只闪了一下,只灰了一下,很快就过去了。老王走到了县委的门口。他走到这里根本是一种不知不觉。在退休之后,老王依然常到县委这边来,不过他从未再进去过,只是在外面远远地看着。那天,得知老陈书记已经去世的那天,熟悉的县委在老王的眼里竟然显出了一些陌生。砖墙早就拆了。时不时漏雨的平房也已盖成了楼房,这楼房高大华丽,是全县最高的建筑。门口多了两个穿灰制服的警卫。路两旁那些高大的槐树、柳树也早就没了,现在,那里建的是花坛,种的是怪模怪样的龙爪槐。这些,太让老王陌生了。
他突然又想到了那个骑车的人,他是谁?在什么单位?是秘书?去省城办事……怎么就是想不起来呢?
四
回到家里时他看见自己的老伴儿已经回来了,她一边切着洋葱一边揉着自己的眼睛:刚才他赵叔叔来过,想叫你下午过去打牌。
老王嗯了一声就进了里屋。他感觉有点累了。他感觉,老陈书记的死毫无缘由地带走了他身体里的一些力气。阳光落在茶几上,窗外的石榴树的影子在那些光的里面晃动,它们有些狰狞。坐在沙发上的老王又开始犯困,那些乱七八糟的梦又从四面八方聚集来了。老王不想睡。他只好离开了沙发,倚在门边:陈世玉死了。
老伴儿继续切着那些敏感的洋葱,她的眼泪又流下来了。见老伴儿根本无动于衷,老王只好又重新说了一遍,陈书记死了,癌症。
“我知道。他是昨天晚上死的。”老伴儿终于把洋葱收进了盘子里。
——比我还小五岁。老王摇了摇头,他这个病应当是从气上得的,这个人心小,有点儿事就想不开。顿了顿,老王给自己倒了一杯水:那些年,他什么事也不敢做,什么事也做不好。要不是我帮着他,他早就……
老伴儿里里外外地忙碌着,老王的那些话可能根本就没有进入她的耳朵。
想想,人这一辈子多快。老王重新回到了沙发上。那些早就聚集在沙发周围的梦一下子扑了过来,老王无力地抵抗了一下,很快就放弃了,梦把他拉进了梦中。
下午的牌运开始很顺,然而不知老王是不是出错了哪张牌,牌运一下子就下来了,一片昏暗。最让老王受不了的是齐老太太,没完没了地说话,还摔牌。牌运正好的时候老王还能原谅她的这些毛病,然而牌运下来了,她这些毛病也就更加突出了,老王按了按自己的火气,又按了按自己的火气,然而他最终没有能按住。
——以后谁再叫我打牌,无论是谁,你都说我不去!站在门口,老王就冲着屋里面嚷,老伴急急地冲着他使了几个眼色,“不打就不打,不是想让你消遣吗?”她指了指里屋,“老陈局长来了,坐了有一刽L了。”她说,“你们说着,我去看看咱父亲去,中午他没怎么吃饭。”
老王站在门口。他感觉那股怨气还在他胸口以上的位置死死地堵着,让他的呼吸有些困难。
——老陈,你早来了?他的声音还有些干涩,有些不够平坦,于是他又轻轻地咳了一下。这时,邻居家那个刚刚换声的孩子声嘶力竭地狂吼:我要从南走到北,也要从白走到黑,假如你要认识我,就请你给我一碗水,假如你要是爱上我,就请你吻我的嘴……
老王渐渐地和邮局的两个小女孩熟悉了起
来,其中—个微胖的女孩一见他来就微笑一下,王书记,来了。他是来了,可信还没来,都已经半个多月了,要不是那个胖女孩总是“王书记”“王书记”地叫着,老王的尴尬不知会增加多少。现在,每次去邮局他都觉得有些艰难了,他感觉那里的光线总比别处略略地暗一些。可是,澳洲的信却一直不来。
等待已经让老王感到烦躁。
等待让老王坐卧不安。他有了一张很不顺心的床,有了一把很不顺心的椅子,有了一杯很不顺心的茶。
等待让老王噩梦连连,已经几天他从噩梦中惊醒,醒来的时候他的头上、身上和手心里满是汗水。他悄悄地朝老伴儿身边挪动一下,让自己的手搭在她的手上或者身上,然而这并不会使他身上和心里的凉气降低多少。他的耳朵里是妻子奇怪的鼾声,时断时续的抽泣,磨牙的声音,窗外树叶的声音和风的声音,风吹过树叶的声音,有时还会有邻家那个男孩尖声尖气的歌声。从噩梦中醒来老王就很难再进入睡眠,而夜晚却又让人惊讶的漫长。
几天来,老王感觉一股灰色的气不断在他的胸口以下的部位悄悄地聚集成一个核桃的形状,一个鸡蛋的形状,一个苹果的形状,并且有继续增长的可能。“女儿怎么就是不来信呢?她不会出什么事儿吧?”老伴儿显得比老王更为焦急,“你要不打个电话写封信问问,都这么长时间了。”
老伴儿的焦急反而使老王镇定了下来,他端起那个不顺心的杯子,把里面的茶水一点点地喝了下去。——你瞎想什么,又瞎想了吧?你以为澳洲政府是给你女儿开的?手续能那么好办?再说,不管是水陆还是航空,这么远的路程怎么也得有段时间,你就等着吧。
“可她怎么就不来个电话?”
——她不是早给你说了吗?你又不是不知道她,她从上高中上大学给家里写过几封信打过几次电话?
“这还不是你的责任?她回趟家,打个电话,只要一让你逮着就横看不顺眼竖看不顺眼,没有个好脸色。她为什么不愿意回家?她不想看你的脸。”
老王知道,老伴儿接下来就是对他的指责了,这指责会从西瓜到芝麻,从芝麻到西瓜,于是他急急地岔开了话题:
——赵家的孩子是越来越不像话了。留那么长的头发。也总不见他学习,音箱开得倒是挺响。光学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孩子也是”,老伴似乎没有觉察老王的策略,她朝邻居那边看了看,音乐和孩子的吼叫正在源源不断地传过来,“晚上都吵得入睡不好。”
既然老王的感觉在老伴儿那里得到了认同,老王就有了些力气,他觉得自己是有过去找一找孩子的父母的必要了。——我去说说这孩子。
在那个十六七岁的孩子面前,老王尽量让自己和蔼,甚至,他还伸出手去摸了一下那个孩子的头。他头发的前半部分已全部染成了黄色。——你,你爸爸妈妈在家吗?
孩子摇了摇头,他说他的父母在外地开了一家药铺,一星期中顶多回来一两次。
——那你爸爸的工作呢?
辞了。孩子相当轻描淡写,屋里面的音乐急促而浑重,一个急促而浑重的男声在里面反复地唱着: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
——辞了?老王看得出来,这个孩子的客气里面透着一股冷漠,他急于摆脱自己。老王对自己说,你要和蔼,和蔼。于是,老王用了一种更为轻缓的声调:孩子,你看,我们老人吧就是怕吵,你的音箱能不能开小点声,晚上的时候……
可以,当然可以。那个孩子没等他说完就跑回了屋里,音乐立刻就小了下来。“这样行吧王伯伯,以后我不会再吵到你们了。”他回到了老王的面前。
这回轮到老王不好意思了。行,行。他的手再次伸向了男孩的长发:头也该理一理了。你的学习怎么样,你爸妈不在可不能松劲啊。
“嗯。”
——学习搞不上去,长大了会后悔的,不能光贪玩。现在可不是玩的时候。
“嗯。”
——再说这音乐,你多听听健康的向上的音乐,少听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孩子,王伯伯说你是为你好,你明白不?听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你的将来没好处。
“嗯”。
……老王推心置腹,神采飞扬,意犹未尽。他突然发现那个孩子有一副木木的表情,而眼睛也游离着,望着别处。——孩子,我说的你可别不愿意听,以后你会知道它是有用的。
“我没有不愿意听啊,”孩子坏坏地笑了笑,“您的这些话我都听过几遍了,老师啊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大姑大姨都这么讲。我承受得住。”一脸坏笑的孩子,他摇晃着,颤抖着,“王伯伯,要不您当书记呢,水平就是高,您可比我老师讲得好多了”。
老王有了一种挫败感,这种挫败以前也多多少少地有过,然而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让他恼火。他用尽了力气撞向的却是一块海绵。他来河边打水,提起来一看自己的手上只有一只竹篮。
五
——这个孩子算是完了。非成人渣不可。老王对着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说,他拿起茶杯的手竟有些抖。背影还是那个背影,她打开了火,在锅里倒入了油。 ——这个小赵也是,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做。一家人,眼里就是钱钱钱。孩子也不管了。都成什么样子了。
菜放进了锅里。还是洋葱。一天到晚的洋葱。
——这个孩子,一点儿好都不学,什么话也听不进去,说着,老王忽然有了一些激动:现在这些年轻人,真……
忽然,老王感觉自己再次遭受了挫败。老伴儿正在忙碌她的洋葱,她根本就没在意自己和她说了什么,她根本就没听!他用了太多的力气,撞向的却是一块厚厚的海绵。
——我说的你都听见了没有!老王一阵心痛。一阵荒凉。老伴儿这样对他这样对他的话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而是多年这样,一贯这样。只是,以前,他没有像今天这样察觉。原来自己的话都是说给木头听的,说给空气听的,说给门框和茶几听的。以后还是这样。
——我说的你都听见了没有!老王的声音提高了八度,他朝四下里看了看,随后抓起一个玻璃瓶在地上摔得粉碎。那个瓶里装的是花椒,它们散乱地分布在地上,分散或者聚拢。
“你闹什么,你今天吃什么了?”老伴儿眼泪婆娑地转过了脸,“每天什么活也不干你倒有功了,动不动就发火,你凭什么?……”锅里的莱噼噼啪啪地响着,一股焦煳的气味迎面扑来。老王觉得,自己的心凉透了。
老王的心凉透了。
和那个多事的齐老太太吵过之后,老王已经几天没有去打麻将了,而这些天里也真没有人来叫他,空闲下来的时间实在难以打发。尤其是和老伴儿生气之后,她那张阴沉着的,满是皱纹的脸老在眼前晃来晃去,她堵住了阳光也堵住了空气。电视里净是反反复复的广告,要不就是豪宅里的男男女女恩恩怨怨,好像中国已消除了贫穷进入了小康似的。要不就是悲惨得一塌糊涂的一家人。一看电视老王就开始犯困,仿佛在电视里聚集了一大群瞌睡虫,电源一开它们就飞出来了。
每天早晨的晨练倒成了老王的一大乐趣,
他总是早早地起来,换上白色的练功服,踏着露水在略显昏暗的早晨朝操场走去。只是他的学生有几个总是时来时不来,无论他如何威逼利诱还是老样子。这样,看上去他的学生就比老赵头那边少几个人,也不如那边整齐。那个很不上路的胖子倒是天天来,每次几个动作下来他就要歇一会儿,这很让老王暗暗生气,但又不好说什么。他们的动作已经比那边慢了,那边已经开始野马分鬃,而老王他们才刚刚金鸡独立。这种相对的缓慢多少使老王的乐趣有所降低。当然,这点失意还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