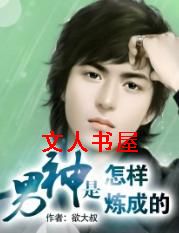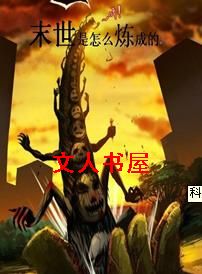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上)[苏联]尼. 奥斯特洛夫斯基-第3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斯坚突围的波军。亚基缅科在谢廖沙身边趴下来。他停止了猛烈的射击,好不容易才拉开灼热的枪机,然后把脑袋贴着地面,转过来对谢廖沙说:“步枪要缓口气,烫得像火一样。”
枪炮在轰鸣,谢廖沙勉强才听到他说的话。 后来枪炮声小了一点,亚基缅科像是顺便提起似的说:“你的那位老乡在第聂伯河里淹死了。我没看清他是怎么掉到水里去的。”他说完,用手摸了摸枪机,从子弹带里拿出一排子弹,一丝不苟地压进了弹仓。
攻打别尔季切夫的第十一师,在城里遇到了波军的顽强抵抗。大街上正在浴血苦战。 敌人用密集的机枪子弹阻挡红骑兵的前进。 但是这个城市还是被红军占领了。 波军已经溃不成军,残兵狼狈逃窜。 车站上截获了敌人的许多列火车。 但
231
422尼。 奥斯特洛夫斯基
是对波军来说,最可怕的打击还是军火库爆炸,供全军用的一百万发炮弹一下子全毁了。 全城的玻璃震得粉碎,房屋好像是纸糊的,在爆炸声中直摇晃。红军攻克日托米尔和别尔季切夫以后,波军腹背受敌,只好分作两股,撤出基辅,仓皇逃遁。 他们拼命想为自己杀出一条路,冲出钢铁包围圈。保尔已经完全忘却了他自己。 这些日子,每天都有激烈的战斗。 他,保尔,已经溶化在集体里了。 他和每个战士一样,已经忘记了“我”字,脑子里只有“我们”
:我们团、我们骑兵连、我们旅。战局的发展犹如狂飙,异常迅猛,天天都有新的消息传来。布琼尼的骑兵以排山倒海之势,不停顿地向前挺进,给敌人一个又一个沉重的打击,摧毁了波军的整个后方。 满怀胜利喜悦的各骑兵师,接二连三地向波军后方的心脏诺沃格勒—沃伦斯基发起猛烈的冲锋。他们像冲击峭壁的巨浪,冲上去,退回来,接着又杀声震天地冲上去。无论是密布的铁丝网,还是守城部队的拼命顽抗,都没能挽救波军的溃败。 六月二十七日早晨,布琼尼的骑兵队伍渡过斯卢奇河,冲进诺沃格勒—沃伦斯基城,并继续向科列茨镇方向追击溃逃的波军。 与此同时,亚基尔的第四十五师在新米罗波利附近渡过斯卢奇河,科托夫斯基骑兵旅则向柳巴尔镇发起了攻击。不久,骑兵第一集团军的无线电台接到战线司令的命令,
232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上)52
要他们全军出动,夺取罗夫诺。 红军各师发起强大攻势,把波军打得七零八落,他们只能化成小股部队,四散逃命。有一天,旅长派保尔到停在车站的铁甲列车上去送公文。在那里他竟遇见了一个根本没想到会碰见的人。 马跑上了路基。 到了前面一辆灰色车厢跟前,保尔勒住了马。 铁甲列车威风凛凛地停在那里,藏在炮塔里的大炮露出黑洞洞的炮口。列车旁边有几个满身油垢的人,正在揭开一块保护车轮的沉重的钢甲。“请问铁甲列车的指挥员在哪儿?”保尔问一个穿着皮上衣、提着一桶水的红军战士。“就在那儿。”红军战士把手朝火车头那边一指说。保尔跑到火车头跟前,又问:“哪一位是指挥员?”
一个脸上长着麻子、浑身穿戴都是皮制品的人转过身来,说:“我就是。”
保尔从口袋里掏出公文,交给了他。“这是旅长的命令,请您在公文袋上签个字。”
指挥员把公文袋放在膝盖上,开始签字。 火车头的中间车轮旁边,有一个人提着油壶在干活。 保尔只能看到他宽阔的后背和露在皮裤口袋外面的手枪柄。“签好了,拿去吧。”指挥员把公文袋还给了保尔。保尔抖抖缰绳,正要走,在火车头旁边干活的那个人突然站直身子,转过脸来。 就在这一瞬间,保尔好像被一阵风刮倒似的,跳下马来,喊道:
233
622尼。 奥斯特洛夫斯基
“阿尔焦姆,哥哥!”
满身油垢的火车司机立即放下油壶,像大熊一样,抱住年轻的红军战士。“保尔!小鬼!原来是你呀!”阿尔焦姆这样喊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铁甲列车指挥员用惊奇的目光看着这个场面。 车上的炮兵战士都笑了起来。“看见没有,兄弟俩喜相逢了。”
八月十九日,在利沃夫地区的一次战斗中,保尔丢掉了军帽。 他勒住马,但是前面的几个骑兵连已经冲进了波军的散兵线。杰米多夫从洼地的灌木丛中飞驰出来,向河岸冲去,一路上高喊:“师长牺牲了!”
保尔哆嗦了一下。 列图诺夫,他的英勇的师长,一个具有大无畏精神的好同志,竟牺牲了。 一种疯狂的愤怒攫住了保尔的心。他使劲用马刀背拍了一下已经十分疲惫、满嘴是血的战马格涅多克,向正在厮杀的、人群最密的地方冲了过去。“砍死这帮畜生!
砍死他们!
砍死这帮波兰贵族!
他们杀死了列图诺夫。“盛怒之下,他扬起马刀,连看也不看,向一个穿绿军服的人劈下去。 全连战士个个怒火中烧,誓为师长复仇,把一个排的波军全砍死了。他们追击逃敌,到了一片开阔地,这时候波军的大炮向他们开火了。
234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上)72
一团绿火像镁光一样,在保尔眼前闪了一下,耳边响起了一声巨雷,烧红的铁片灼伤了他的头。 大地可怕地、不可思议地旋转起来,向一边翻过去。保尔像一根稻草似的,被甩出了马鞍,翻过马头,沉重地摔在地上。黑夜立刻降临了。
235
822尼。 奥斯特洛夫斯基
第 九 章
章鱼的一只眼睛,鼓鼓的,有猫头大小,周围是暗红色,中间发绿,这只眼睛在闪闪发亮。章鱼的几十条长长的腕足,像一团小蛇似的,蜿蜒地蠕动着,上面的鳞发出讨厌的沙沙声。 章鱼在游动。 他看见章鱼差不多就贴着自己的眼睛。 那些腕足在他身上爬着,它们是冰凉的,像荨麻一样刺人。 章鱼伸出的刺针如同水蛭,死叮在他的头上,一下一下地收缩,吮吸着他的血液。 他感到他的血液正从自己身上流到已经膨胀起来的章鱼体内去。 刺针就这样吸个不停。 他头上被叮的地方,疼得难以忍受。从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传来了说话的声音:“现在他的脉搏怎么样?”
有个女人声音更轻地回答:“脉搏一百三十八,体温三十九度五。一直昏迷,说胡话。”
236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上)92
章鱼消失了,但是被它叮过的地方还很疼。 保尔觉得有人把手指按在他的手腕上。他想睁开眼睛,但是眼皮很重,怎么也抬不起来。 为什么这样热呢?大概是妈把炉子烧得太旺了。 又有人在什么地方说话了:“脉搏现在是一百二十二。”
他竭力想抬起眼皮。 可是,心里像有一团火,热得喘不上气来。想喝水,多么想喝水呀!他恨不得马上就爬起来,喝个够。 那为什么又起不来呢?他刚想挪动一下身子,但是,立刻觉得身体是别人的,不是自己的,根本不听使唤。 妈马上会拿水来的。 他要对她说:“我要喝水。”在他旁边,有个什么东西在动。 是不是章鱼又来了?就是它,看它那只红色的眼睛……
远处又传来了轻轻的说话声:“弗罗霞,拿点水来!”
“这是谁的名字呢?”保尔竭力在回想,但是一动脑子,便跌进了黑暗的深渊。 他从那深渊里浮上来,又想起:“我要喝水。”
他又听到了说话的声音:“他好像有点苏醒了。”
接着,那温和的声音显得更近、更清晰了:“伤员同志,您要喝水吗?”
“我怎么是伤员呢?
也许不是跟我说的吧?
对了,我不是得了伤寒吗!
怪不得叫我伤员呢!“于是,他第三次试着睁开眼睛,这回终于成功了。 从睁开的小缝里,他最先看到的是
237
032尼。 奥斯特洛夫斯基
他面前有一个红色的球,但是,这个球又让一个黑糊糊的东西挡住了。 这个黑糊糊的东西向他弯下来,于是,他的嘴唇触到了玻璃杯口和甘露般的液体。心头的那团火逐渐熄灭了。他心满意足地低声说:“现在可真舒服。”
“伤员同志,您看得见我吗?”
这问话就是向他弯下来的那个黑糊糊的东西发出来的。这时,他又要昏睡了,不过还来得及回答一句:“看不见,但是能听见……”
“谁能想到他还会活过来呢?
可是您看,他到底挣扎着活过来了。 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啊。 尼娜。 弗拉基米罗夫娜,您真可以骄傲。 这完全是因为您护理得好。“
一个女人的声音非常激动地回答:“啊,我太高兴了!”
昏迷了十三天之后,保尔终于恢复了知觉。他那年轻的身体不肯死去,精力在慢慢恢复。 这是他第二次获得生命,什么东西都像是很新鲜,很不平常。 只是他的头固定在石膏箱里,沉甸甸的,他也根本没有力量移动一下。 不过身体的感觉已经恢复,手指能屈能伸了。一间四四方方的小屋里,陆军医院的见习医生尼娜。 弗拉基米罗夫娜正坐在小桌子后边,翻看她那本厚厚的淡紫色封面的笔记本。 里面是她用纤巧的斜体字写的日记:
1920年8月26日
今天从救护列车上给我们送来一批重伤员。 一个头部受
238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上)132
重伤的红军战士被安置在病室角上靠窗的病床上。 他只有十七岁。 我收到一个口袋,里面除了病历,还有从他衣袋里找出来的几份证件。 他叫保尔。 安德列耶维奇。 柯察金。 证件有:一个磨破的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六七一号团证,上面记载的入团时间是一九一九年;一个弄破的红军战士证;还有一张摘抄的团部嘉奖令,上面写的是:对英勇完成侦察任务的红军战士柯察金予以嘉奖。 此外,还有一张看来是他亲笔写的条子:
如果我牺牲了,请同志们通知我的家属:舍佩托夫卡市铁路机车库钳工阿尔焦姆。 柯察金。
这个伤员从八月十九日被弹片打伤以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明天阿纳托利。 斯捷潘诺维奇要给他做检查。
8月27日
今天检查了柯察金的伤势。 伤口很深,颅骨被打穿,头部右侧麻痹。 右眼出血,眼睛肿胀。阿纳托利。 斯捷潘诺维奇打算摘除他的右眼,以免发炎,不过我劝他,只要还有希望消肿,就先不要做这个手术。 他同意了。我的主张完全是从审美观点出发的。 如果这个年轻人能活过来,为什么要摘除一只眼睛,让他破相呢?
他一直说胡话,折腾得很厉害,身边必须经常有人护理。我在他身上花了很多时间。 他这样年轻,我很可怜他。 只要
239
232尼。 奥斯特洛夫斯基
力所能及,我一定要把他从死神手里夺过来。昨天下班后,我在病房里又呆了几个小时。 他的伤势最重。 我注意听他在昏迷中说些什么。 有时候他说胡话就像讲故事一样。 我从中知道了他生活中的许多事情。 不过,有时候他骂人骂得很凶。 这些骂人话都是不堪入耳的。 我听了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感到很难过。 阿纳托利。 斯捷潘诺维奇说他救不活了。 这老头生气地咕哝说:“我真不懂,他差不多还是一个孩子,部队怎么能收他呢?真是岂有此理。”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