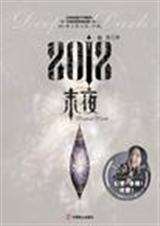2005年第5期-第4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吃罢午饭,肥原和王天香直奔吴志国的关押处。想到本来是铁证如山的,而自己居然被他一个牵强的说法所迷惑,把铁证丢了,弄出这么大一堆事情来,也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肥原既恨自己,也恨吴志国。但归根到底,恨都是要吴志国这杂种来承担的。这样吴志国不可避免地又遭毒打了。像昨天一样,肥原见了吴志国什么话不说,抓起鞭子,先发泄地抽了一通,出了气,然后才开始审问。
其实,肥原之所以这样,先打后审,并不是要威胁他,而就是要出气,解恨。还用威胁吗,只怕他“招得快”。肥原以为,以前只有物证,现在李宁育死了,等于又加了人证,人证物证都在,吴志国一定会招供的。等他招供了,他就没有机会出气了。
殊不知,吴志国在人证物证铁证面前,照样死活不招;用刑,还是不招;用重刑,还是不招;死了,还是不招,叫肥原简直觉得不可思议,亡国奴还有这么硬的骨头。
吴志国是被活活打死的,这似乎正应了唐一娜的话:王天香和他的手下都是毒手,打死人属于正常,不打死你才不正常呢。
死不承认!吴志国的死让肥原又怀疑起自己来,担心毒蛇“犹在人间”,犹在西楼。这简直乱套了,肥原觉得自己快要疯掉了,他半个脑袋想着两具死尸,半个脑袋想着三个大活人,人也觉得有一半死了,空了,黑了,碎了。他真想冲去西楼那边,挖出每个人的心,看看到底谁是毒蛇。可他没时间了,来接他进城的车已经停在楼前,他要去城里指挥晚上的抓捕行动。临走前,他命令哨兵把西楼锁了,不准任何人进,不准任何人出,一切等他回来再说。
肥原相信,不管怎么样,等晚上抓了人,他就知道谁是毒蛇了。
可晚上他没抓到人,一个都没有,影子都没有。文轩阁客栈坐落孤山,地处偏冷,素以清静、雅丽著称,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来此过夜生活,把酒,吟诗,狎昵,经常是灯火明暗有致,歌声随风飘散。而肥原看到的是一座既无声又无光的阴森可怖的黑屋子,打亮了灯火,发现人去楼空,清静犹在,雅丽犹在,就是看不到人影,找也找不见!
第二天一早,裘家大院的东西两楼也是人去楼空,他们消失得就像他们来的时候那样突然而神秘。至于这些人到哪儿去了,他们的结局如何,成了又一个谜……
这是个后记,因为有些事必须交代。在此,我要给大家介绍认识一位世纪老人,老人家姓潘,今年已经九十三岁高龄。我对这个故事的了解都来自于她的讲述,和她提供的资料,以及她介绍我认识的“知情者”。
潘老是这个故事至今唯一健在的见证者。六十几年前,潘老是我党一名地下工作者,代号叫“公牛”,主要负责杭州地下党与新四军总部之间的无线电联络。除此外,她也给毒蛇传送情报。潘老说,当时毒蛇发出的情报很多,急件一般由老鳖负责传递,因为他们随时可以见面,有暗号的,毒蛇只要在窗户上放个什么东西,老鳖就知道去哪里取情报了。如果不是急件,就由她负责传送。
那谁是毒蛇?潘老说,就是李宁育!而她则是李宁育在遗书中说的“小容吾妻”。
“不过,那是假的。”潘老回忆道,“我们只是同志关系,工作需要才假扮夫妻的。所以,当我看到老李在遗书中称我为‘小容吾妻’时,就知道这不是一份简单的遗书,而是一份‘密码’,在暗示我他身上有情报。”
可是,潘老在李宁育身上翻遍了也没有发现情报,连李宁育的佛珠也每一粒都细细看了,还是没有。但在查看佛珠时,潘老发现佛珠好像变短了,后来一数确实是短了:少了十一颗珠子!
潘老解释说:“我知道老李的佛珠有八十一颗,因为他曾经跟我说过,这是九九八十一的意思,是《易经》中最大的数字。秘密就在这十一颗珠子上!那么少掉的珠子会去哪里了呢?身上肯定没有的,后来我联想到遗言上的话——佛在我心中,我在西天等你……我想他这样说一定是在暗示我什么。最后,我推测那十一颗珠子可能就在他肚子里……”
果然是在肚子里!
潘老激动地说:“我简直不敢相信,十一颗珠子呐,每一颗珠子上都刻有一个字,连起来刚好是一句话——速告老虎,取消文轩阁行动!”
一条无价的情报!
潘老现已记不清具体日子,但由她在数年前口述,何大草教授编写,青城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七月出版的《地下的天空》一书记载,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日夜晚,即原订时间四天后,周恩来特使老K在杭州武林路108号一栋民宅里召开了相同的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的全体同志都脱帽向李宁育默哀一分钟,对他机智勇敢、视死如归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致以了崇高的敬意……
再来讲肥原。肥原当然不知道以上这一切,可以想象,当肥原站在人去楼空的文轩阁客栈前时,他一定无法相信眼前的事情:抓捕行动失败了!换言之,毒蛇已经把情报传出来了。但谁是毒蛇,情报是用什么方式传送的?此时的肥原已无兴趣探究,他的热情都在井田将军临行前给他的密信上。这也是“密码”,破译的密钥是时间,时间不到只能猜,现在时间到了,可以看了。肥原打开密信,看见上面只有一句话:
错杀小错,遗患大错
就是说,凡可疑者,格杀勿论。
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指证肥原究竟杀了谁,据王天香的一个手下留下的回忆资料说,这天夜里肥原撤掉了岗哨和所有执勤人员,安排他们连夜回了部队。在他们离开前,看见张司令匆匆赶来陪肥原吃夜宵。他回到部队后发现钱包不见了,怀疑是遗在了房间里,第二天一早赶回去,东西两栋楼竟都空无一人。后来,除了王天香又回到部队,提升为副参谋长,汪大洋、童副官、唐一娜三人再也没有回来,也没人知道他们的消息,好像是从人间蒸发了。他认为这些人都被肥原杀害了,进而他推测肥原后来被人暗杀,有可能是这些人的亲友们所为。
潘老承认她对肥原了解不多,但说到他遭人暗杀的事,老人闪烁着浑浊的目光对我说:“这年冬天,杭州城里经常传出有关肥原的小道消息,先是说有人出了十万块大洋请捉奸队去暗杀他,又有说出的是二十万块大洋。到了年关前不久的一天,杭州的所有报纸都登了,肥原遭人暗杀,身上戳了数刀,尸首被抛在大街上,真是大快人心啊。”
至于是谁杀的,说法很多,有说是我地下党的同志,有说是民间的除奸队,有说是重庆方面来的人,有说是唐一娜父亲找的杀手,总之众说纷纭,不一而足。所以,肥原被杀之事,因为过于生动离奇,变得像一个传说,穿过了世代,至今都还在杭州城里流传。
最后来讲题记中的“密码”。这其实是一份真正的密电码,是我用潘老当年与新四军总部联络的密码编写的。在常熟新四军纪念馆里,可以看到这部密码的副本,像如今所谓的口袋书一样的开本,封皮是厚油纸,内文是薄薄的蜡纸,共有三册,每一本都有一块砖头这么厚。我曾找人想借来看看的,但馆方坚决不从。后来,我一位从事密码研究的朋友仅根据潘老当时的代号“公牛”两字的密表,把整部密码的密表全推算了出来。我感到很神秘,朋友说其实那是非常初级的密码,就是在汉语拼音和数字之间构成一个替代关系,只要想到这点,再根据公牛两字已有的密表,任何一台电脑都可以破译这部密码。
现在,这部密码就存在我电脑里,占用的空间还没有我一张六百万像素的数码照片大,我用它把我的题记翻成电码,便成了现在题记中的那些数字。当然也可以用它译回来,译回来就是这样:
毋庸置疑,本文献给潘老
2005/7/29二稿于成都罗家碾
繁华
朱文颖
一
王莲生初来上海是个阴雨的下午。那天他坐的是二等舱,船不大,还刮着风,所以颠得很厉害。他对面躺了个瘦小的干瘪老头,一上船就开始吐。王莲生好不容易小睡一会儿,梦里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前些天他刚看过一场京戏,里面那个旦角受了委屈,咿咿呀呀的哭,但半天了,一滴眼泪还挂在水袖尖尖上——等到王莲生睁开眼睛,却是那老头抱着一只小罐,在床边半蹲着身子。他呕吐时眼睛半睁半闭,极为享受,让人怀疑那小罐里装着的,其实是很快就能烹饪上桌的一尾活鱼。
王莲生叹了口气,起身去了甲板。
雨倒是停了。还微微的起点太阳。在远处,几只白色的海鸥紧贴着水面飞,王莲生看了半天,觉得它们像要一头扎进水里自尽似的。
一个戴帽子的外国巡警冷漠地走过来。王莲生刚受尽那干瘪老头的折磨,心里对规则、清洁、秩序以及权威有关的事物多了几分亲近。他微笑着迎了上去。王莲生见过些世面,还不好不坏的能说上几句洋文。这多少让巡警灰蓝的眼珠子泛出了珍珠的光泽。
“还要多久能到上海?”王莲生问。
“天气不好,可能会迟点。”
“船颠得厉害呵——”
“听说……听说已经翻了两艘小船了。”这估计是上头关照要保密的消息,但蓝眼睛巡警一个犹疑还是说了出来。话一出口,他便有点后悔,眼睛里的珍珠光泽暗了暗,手顺带搭在了腰里的警棍上。
王莲生原本还想打听一些治安方面的事。听说上海是不太平的,石库门外的里弄,到了晚上九点钟就要上锁;还有呀,听说上海好吃的东西多,好看的人多,但是小偷、强盗、野鸡、骗子也多……正在这时,突然从船头那儿传来一阵嘈杂的人声,一个拉高了的嗓门在叫:“瘪三!真是瘪三呀!”停了一下,紧接着又传来了哭声:“那我该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我要跳海了呀——”
王莲生心头一紧。但并没听到类似于“扑通”的声响。人没有跳下去,好奇心倒是上来了。
蓝眼睛巡警在前,王莲生在后。蓝眼睛巡警用洋文说,王莲生再用中国话复述一遍。
一个穿绿衣服的身影正俯在船栏上哭。是个二十来岁的纤弱男孩,他给王莲生的第一印象,是白如玉色的脸上挂了满脸的泪珠子。倒像是剔透的珍珠,但给脸上的白冲淡了,越发显得凄清。
“你们别过来!我要跳了——我真的要跳了——”他哭得很凶,人和衣服都在剧烈地发抖。但他说话与喊叫的声音,却有着奇怪的女性化特点。这莫名其妙的悲剧因此变得有些滑稽起来,连王莲生都忍不住笑了。
“你多大了?”蓝眼睛巡警皱了皱眉。围观的人已经渐渐多了起来,带着晕船时微青或者发白的脸色。王莲生发现,和他同舱房的那个干瘪老头也出来了,人显得更小了,佝着。手里却还紧紧抱着那个小罐头。
“十九岁。”
“十九岁?才十九岁你就想跳海?”蓝眼睛巡警的眉毛皱得更紧了。
伴着海浪,四周有掩饰不住的窃笑声。这话虽然说得正义凛然,但听上去,仿佛二十岁跳海就要正当很多似的。
十九岁的小男人正沉浸在自己的悲恸中,自顾自地把话说下去:“那个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