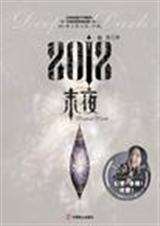2005年第5期-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以放。放完了只要补充说明一下就可以了:“哎,新米饭吃多了。”谁也不会笑话谁。庄稼人能够痛快放屁的日子可不多呢。
噩耗来了。从天而降。事先连一点点的预兆都没有,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庄稼人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他“没”了。人们不相信。这怎么可能呢?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个消息。哀乐响起来了。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一个多么晴朗的日子,下午三点十五分,噩耗破空而来。王家庄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样,一下子陷入了悲痛。还有惊慌。会发生什么呢?
所有的人都把手上的活计放下了,不约而同,来到了大队部的门口。人们聚集在这里,谁也不说话,谁也不敢弄出一点声音。不知道是谁第一个哭了,大伙儿都哭了。这是真心的悲痛,虽说毛主席他老人家一直生活在天安门,可他天天在王家庄,他的画像挂在每一个人的家里,钉在每一个人的心里。王家庄的每一个人都熟悉他父亲一样的目光,他的韭菜一样宽的双眼皮,他没有皱纹的额头,他下巴上的痣。他哪一天离开过王家庄?他哪一天离开过庄稼人?没有,从来没有。他是最亲最亲的人。吴蔓玲站在大队部的门口,望着大家,她的面颊上挂着泪水,有些失措,说不出一句话来。这时候人群里突然有人哭出了声音,是一个年老的妇女,她抱着一棵树,大声说:“新米刚刚下来,你怎么在这个时候走了哇!”这句话揪人的心了,老大娘说出了广大贫下中农的心里话。吴蔓玲被这句话感动了,“哇”的一声,扶在了门框上。
在悲痛的时刻王家庄的凝聚力体现出来了。这个时候不需要动员,是悲痛将王家庄团结起来的。悲痛是有凝聚力的,王家庄一下子就结成了一个统一战线,坚不可摧了。所有的人都站在一起,肩并着肩,人们在往前挪,在向吴蔓玲靠拢,虽然缓慢,却有了汹涌的势头。王家庄的社员体现出了高贵的自觉性,每个人都知道,这时候要集中起来,围绕在支部书记的周围。等真的靠在了一起,他们才发现,他们这样做不只是因为团结,骨子里是害怕,人也警惕起来了。总觉得会有什么意外,或者更大的不测。意外其实也不可怕,可一旦发生了意外,谁来指挥自己呢?这是一个现实而又迫切的问题。过去一直是毛主席,主席走了,谁来呢?这个问题怕人了。但越是害怕就越不应该守株待兔,就越是应该主动出击,干点什么。轰轰烈烈地,去干点什么。既然悲痛已经化成了力量,还等什么?一定要先下手,先摧毁什么。人们还在往前挤,所有的力量都汇聚在一起,风平浪静,广场上总体的态势是平静的,然而,骨子里悲壮了,洋溢着敢死的气概。现在,王家庄唯一缺少的就是方向,也就是命令。只要有了命令,刀山,火海,个个敢上,个个敢下。吴蔓玲再一次被感动了,她缓慢地举起胳膊,向下压了压,对大伙儿说:“大伙儿先回去,”她抬起头来,看了一眼树梢上的高音喇叭,说:“我们要听它的。”大伙儿侧过脑袋,齐刷刷地望着高音喇叭。高音喇叭现在不再是喇叭,是铁的战旗。
别看高音喇叭整天挂在那儿,不显山不露水的,在这样严重的时刻,它的绝对意义体现出来了。现在,它就是上级,它就是潜在的命令,它就是一切行动的指挥。为了保护高音喇叭的安全,吴曼玲提供了一个紧急方案,由吴蔓玲亲自挂帅的“特别行动队”就在当天晚上正式成立了。所谓的“特别行动队”,其实是由王家庄的全体社员组成的,四个生产队分成了四个组,王家庄立即变成了临时的、非正式的军队。这个军队实行包干制,每个生产队保护线路的一个段落,再把这个段落细分成若干的小段落,每个人一小块,这样,在高音喇叭的沿线上,真正做到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壁垒森严了。王家庄完全军事化了,真的像毛主席他老人家所说的那样,全民皆兵。军事化在任何时候都是最稳妥、最有力的办法。它是保障。眼下的吴蔓玲不仅是王家庄的村支书,同时也是王家庄的军事指挥官。
高音喇叭传来了上级的部署。依照上级的部署,王家庄在大队部设置了灵堂。王家庄的人全体发动起来了,写标语,扎纸花,做花圈。花圈沿着大队部的内侧摆子一圈又一圈,白花花的,中间夹杂着金箔和锡箔的光芒,还有赤、橙、黄、绿、青、蓝、紫,这一来就斑斓了,喧闹而又缤纷,把丧礼的气氛烘托出来了,是无限热烈的悲伤。高音喇叭里重复播送着北京的声音,还有哀乐。秋日里灿烂的阳光忧郁而又沉重。然而,不和谐的声音还是出现了,王瞎子,这个在地震的时候表现就不好的五保户,他的流氓无产者的习性还是暴露出来了,居然喝酒了。他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了一点酒,喝得满面通红,一身的酒气。这个问题严重了,相当的严重。高音喇叭早就发出了通知,九月十五号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追悼会,在此期间内,中国大地上的任何一块土地上都不允许开展娱乐活动。你王瞎子是个什么东西?三天吃六顿,你快活的哪一顿?这样的时刻你怎么可以喝酒?当即被王家庄发现了,告发了,捆了起来,拉到了大队部。
早在地震的时候吴蔓玲就打算“紧一紧”王瞎子的“骨头”了,出于大局,吴蔓玲放了他一马。对他宽大子。可王瞎子就是认识不到这一点。他那双看不见的眼睛硬是看不见一样东西,那就是宽大的限度。这一次吴蔓玲没有和他理论,直接叫人拿来了绳子,给他“紧骨头”了。王瞎子被捆得结结实实的,浑身都是麻绳,只留下了一颗脑袋,连两只脚都看不见了。“紧”好了,王瞎子被丢在了大队部主席台的下面。吴蔓玲发话了,“除了提审,十五天之内不许出来。”主席台的上面就是毛主席的遗像,王瞎子当然知道把他关押在这个地方意味着什么,噤若寒蝉,嚣张的气焰立即就下去了。
经过三十三人十一轮的严格审查,结论出来了,王瞎子的喝酒不是有组织的行动,不是有预谋的,完全是王瞎子个人的突发性的行为。说到底就是嘴馋。这就非常遗憾了。在这样的时刻,王家庄的人们其实渴望一次战斗,渴望一次真正的较量,渴望一次你死,或者我活。问题是,这是有前提的,得有敌人。王家庄多么渴望能够像挖山芋、挖花生那样,通过王瞎子这个突破口,一下子挖出一大溜子的敌人,发现一批,揪出一批,然后,再打倒一批。可惜了,没找到。
老渔叉的寻找和挖掘是在噩耗传来的那一刻停止的。他歪着脑袋,扶着大锹的把手,认认真真地听。听到后来,老渔叉便把手里的大锹放下了,一个人点上了烟锅,安安稳稳地蹲下了。当天夜里老渔叉没有折腾,整整一夜都老老实实地躺在床上,这个难得了。弄得兴隆反而警觉起来,不敢睡了,就觉得老渔叉的那一头要发生一点什么,一夜都在等。可直到天亮的时刻老渔叉都没有闹出什么动静。兴隆听到了麻雀的叫声,听到了公鸡的叫声,闭上眼,踏踏实实地睡了。
一觉醒来已经临近中午,兴隆来到院子里,老渔叉早已是一头的汗。他不是在挖,相反,在填。他用天井里的新土把一个又一个的窟窿给填上了。哀乐还在响,可兴隆的心里偷偷地乐了。这是一个好的迹象,父亲无端端地病了,眼下又无端端地好了,这是可能的。不管他的心里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起码,他的举止正常了,有了向好的方向发展的一面。兴隆拿起了一把大锹,开始帮他的父亲。只要能把院子填平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满院子的新土堆积在那里,那可是惊涛骇浪啊。兴隆说:“不挖了?”老渔叉说:“不挖了。”兴隆说:“不找了?”老渔叉说:“不找了。”兴隆说:“这样多好,多干净。”老渔叉说:“这样好,干净了。”
填好了天井里的坑,老渔叉搬出了一张凳子,坐下来了。在哀乐的伴奏下,老渔叉仰起头,开始看天。他对“天”一下子有了兴趣,着迷了,是那种强烈的迷恋,有了研究和探索的愿望。他就那么盯着,久久地盯着,一直盯着,仔仔细细地看。他的眼睛眯起来了,嘴巴也张大了,甚至,连口水都流出来了。他就这样一门心思,对着天,看哪,看。还寻思。因为他的眉头已经皱起来了。天空是“空”的,他在看什么呢?想什么呢?不知道了。老渔叉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没有提问,也没有答案。他就这样空洞洞地看。对了,天空其实也不是空的,有一样东西,那就是太阳了。可太阳是不能看的。太
阳从来就不是给人看的。可是,老渔叉犟了,偏要看。他盯上了太阳,只是一刹那,他的眼睛黑了,一抹黑,像一个瞎子。天空黑得像一个无底洞。老渔叉到底还是把目光挪开了,挪到他的三间大瓦房上来了。大瓦房也是黑的,仿佛一团墨,慢慢地,却又清晰起来了,有了跋扈而又富丽的轮廓。它巍然耸立,放射出青灰色的光。老渔叉这一回看定了,他的大瓦房就在苍天底下,天,大瓦房,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呢?没有了。老渔叉望着那些瓦楞子,他的目光顺着那些瓦楞子一条一条地往下捋,仿佛年轻的时候用手捋着女人的头发。瓦楞子凹凸有致,整整齐齐的,像新娘子的头发,滑溜溜地保持着梳子的齿痕。是的,梳齿的痕迹。兴隆他妈嫁过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头的水光,一头的梳齿,妖媚了。老渔叉还记得新婚的那一夜,他望着自己的新娘子,只用了一眼就把新娘子摁倒了。老渔叉拉开了她的棉裤,连上衣都没有来得及脱,他就把他的家伙塞了进去。老渔叉急死了。要知道身子底下的新娘子可不是一般的女人哪,她被王二虎睡过了,差一点就成了王二虎的“小”,只不过王二虎命短,没有来得及罢了。被王二虎睡过的新娘子给了老渔叉无限的欣喜,他喜欢的就是这个,着迷的就是这个,他最想睡的就是“被王二虎睡过的”。他一定要弄清楚,被王二虎睡过的女人究竟是怎样的滋味,他要尝尝。要是细说起来的话,自从给王二虎做帮工的那一天起,老渔叉就立下了一个宏伟的人生目标,他要做王二虎。这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他渴望像王二虎那样吐气、呼吸,他渴望像王二虎那样走路、说话,他更渴望像王二虎那样吃饭、睡觉。谁也没有想到,土改一到,生龙活虎的王二虎就“改”成了一具无头尸,他的三间大瓦房就“改”成自己的了,太简单了,太神奇了,都不敢相信。却是真的。现在,老渔叉又要睡王二虎睡过的女人了,他老渔叉不是王二虎又是什么?他老渔叉不是王二虎又是谁?上天有眼哪!新婚之夜老渔叉一夜都没有合眼,他在操王二虎睡过的女人,一遍又一遍地操。操累了,歇歇,再操;操渴了,喝点水,还操。这是怎样的滋味,怎样的酣畅,怎样的翻身与怎样的解放!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新郎好喜欢!他要天天操,月月操,年年操。老渔叉硬邦邦的,在新娘子的大腿之间迅速地摩擦,不停地进出。他气喘吁吁地问他的新娘:“他厉害,还是我厉害?”新娘子咬紧了牙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