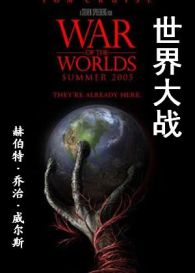102世界大战 [美] h·g·威尔斯-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牧师声嘶力竭的大叫着,站起身,伸出了双臂。“说吧,我在传达着上帝的话!”
他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来了厨房的门前。
“我要亲眼看见!我去了!我已经耽搁得太久了。”
我伸出手,摸到了挂在墙上的切肉刀。我一下子就追了上去。我既感到害怕又怒不可遏。我在厨房中间赶上了他。在最后一刻我发了慈悲,把刀刃转向后面,拿刀柄砸在他的头上。他头朝前倒在了地上。我在他身上绊了一下,站着直喘。牧师一动不动地躺着。
忽然间,我听见了外头的灰泥碎裂的声音,墙上的三角形破洞暗了下来。我抬起头,看见了修理机的腹部慢慢地在洞外滑过。它的一只触手弯曲着伸进了废墟;另一只触手在落在地上的房梁当中摸索着。我目瞪口呆地站着。然后我透过机器身体边缘上的一个玻璃窗看见一个火星人大大的黑眼睛,这双眼睛张望着,后来就有一根长长的金属触手从洞里慢慢伸了进来。
我费力地转过身,在牧师身上绊了一下,走道储藏室的门口停下了。现在触手已经伸进了房间一两码,以一种抽搐的动作,弯曲着转动着向各处探摸。有那么一阵子,我就呆呆地看着触手慢慢地,抽动着伸过来。然后,我轻轻地叫了一声,朝着储藏室退去。我浑身发抖;我几乎不能站直身子。我打开了煤窖的门,站在那里紧紧盯着通向厨房的门廊,门廊里的光线很暗,我仔仔细细地听着。火星人看见我了吗,他在干什么呢?
有什么东西在悄悄地前后移动着;它时不时地碰在墙上,或者又开始移动,发出微弱的金属振动声,就象是钥匙在钥匙环上滑动的声音。然后一个沉重的身体——我当然知道那是什么——给从厨房的地上朝外头拖了出去。我抗拒不了好奇心,爬向门边往厨房里张望着。从三角形的窟窿照进来的阳光下,我看见了火星人,坐在修理机里打量着牧师的脑袋。我立即想到,从牧师头上的伤口上,火星人可能会推测出我的存在。
我又爬回了煤窖,关上门,尽量把自己藏在木柴和煤堆里,并且避免弄出声音。我时不时地竖起耳朵,听听火星人是不是又把触手伸进来了。
那轻微的金属声又响起来了。我听见它从厨房里摸了过来。后来声音更近了,我猜触手已经进了储藏室。我想触手的长度可能够不到我了。我开始虔诚地祈祷。触手轻轻地从煤窖的门上擦了过去。又过了似乎好久;我听见它摸到了门拴!火星人知道怎么开门!
我时时刻刻担心给火星人抓住,然后,门开了。
我在黑暗中能看见这个东西——它更象一个大象的鼻子——朝我挥舞着,一边检查着墙壁,煤堆,木柴和天顶。它就象一个黑色的虫子前后摇晃着的头。
甚至有一次,它碰到了我靴子的后跟。我差点叫了起来;我咬住自己的手。触手安静了一会儿。我猜它退出去了。突然我听见咔喳一声,它抓住了什么东西——我以为它抓住了我!——然后就从煤窖里出去了。我疑惑了一分钟。显然它拿走了一块煤去检查了。
我趁机稍稍移动了一下位置,因为我藏身的地方很挤,又听了一会儿。我轻轻地为自己的安全祈祷着。
接着我又听见了那个触手缓缓地朝我伸过来了。它慢慢地越爬越近,在墙上蹭着,敲打着家俱。
我正在迷惑着的时候,它灵巧地从煤窖里抽了出来,关上了门。我听见它进了餐室,饼干桶哗啦哗啦响了起来,酒瓶也摔到了地上。接着从煤窖的门上传来了一声沉重的声音。然后就是无边的寂静。
它走了吗?
最后,我确信它走了。
它再没有到储藏室里来过;但是第十天我在黑暗里躺了整整一天,躲在木柴和煤堆中间。我甚至不敢爬出去喝水。直到第十一天,我才敢从藏身的地方走出来。
《世界大战》作者:'美' H·G·威尔斯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Xinty665 免费制作
第五章 寂静
我走进餐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厨房和储藏室间的门拴紧。但是餐室里已经空空如也,所有的食物都没有了。显然火星人已经在前一天把它们都给拿走了。看到这些,我第一次感到了绝望。第十一和第十二天,我既没有喝水,也没有吃任何东西。
一开始,我的嘴唇和喉咙发干,体力也大大下降了。我坐在漆黑的储藏室里,感到非常绝望。我的脑子里只想着要吃东西。我想象着自己变聋了,因为从坑里传来的听惯了的声音已经完全听不到了。我觉得自己没有力气爬到裂口那里去而不弄出一点声音,要不然我一定到那里去的。
到了第十二天,我的喉咙变得很疼。我冒着会给火星人听到的危险,砸裂了水槽边的雨水唧筒,弄了两玻璃杯发黑的,浑浊的雨水。我的精神振作得多了。而且胆子也壮了一些,因为没有火星人听到声音后把触手伸进来。
在这几天里,我模模糊糊地记起了牧师和他是怎么死的。
第十三天里,我喝了更多的水,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隐隐约约想起了吃东西和不可能实现的逃跑计划。只要我一打盹,就会梦见可怕的幽灵,牧师的死,还有想象当中的晚餐;但是,不管是睡着还是醒着,我总是感到嗓子很痛,这促使我不断地喝水。射进储藏室的光不再是灰色的,而是红色的了。在我混乱的想象当中,那象是血的颜色。
第十四天的时候,我走进了厨房,我惊奇地发现墙壁的裂口上长满了红草,把半明半暗的屋子里映成了模糊的血红色。
在第十五天的早上,我从厨房里听见一种奇怪的,熟悉的响声,我细听着,辨认出这是一只狗在嗅闻,抓挠的声音。我走进厨房,看见一条狗的鼻子从长满红草的墙上的裂缝里伸了进来。这叫我非常的吃惊。狗一看见我就急促地吠叫了一声。
我想如果能把它不出声地诱骗进来的话,我也许可以把它杀了吃掉;不管怎么说都应该把狗杀了,要不然它的行动会引起火星人的注意。
我向前爬过去,轻轻地说了声“好狗!”;但是它突然缩回头不见了。我听了听——我没聋——但是土坑那边的确没有声音。我听见好象是鸟翅膀的扑动的声音还有一声嘶哑的尖叫声,除此之外就什么也听不见了。
我在裂口那里躺等了很长时间,但是不敢把挡在前面的红草拨到一边去。有一两次我听见狗在下面的沙地上走来走去的声音,还有些鸟叫声,但只有这些声音。最后,外头的宁静让我鼓起了勇气,我朝外头看去。
在角落里,我看见一大群乌鸦在火星人吃剩的尸体骨骸上扑腾着,争抢着。除此之外,坑边没有一个人。
我环顾着四周,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所有的机器都走了。除了角落上一大堆蓝绿色的灰土,另一边有几条铝棒,黑色的乌鸦和死尸的骨架以外,整个地方只剩下沙地上圆形的大坑。
我慢慢地穿过红草,站到了一堆废墟上。我除了看不到身后的地方,也就是北面,我能看到四周的各个方向。我既看不到火星人,也看不到他们的任何痕迹。我脚边的坑壁很陡,但是沿着瓦砾上有一条斜坡通到废墟的上面。我逃跑的机会来了。我开始颤抖了起来。
我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我带着孤注一掷的决心,心脏狂跳着,爬到了废墟的顶上。我已经给这个废墟埋了好几天了。
我又向四周看了看。北面也看不到火星人的影子。
我最后一次看阳光下看到这一部分希恩的时候,它还是个由曲折蜿蜒的悦目白色街道和红色房子组成的小镇,茂密的树丛点缀在其间。现在我却站在一个碎砖烂瓦和砂石堆起的土堆上,上面蔓延着齐膝深的,红色仙人掌一样的植物,没有一株地球上的植物能跟它们竞争。我身边的树已经发黄,快要枯死了,而稍远的地方,红色的枝条仍然还缠在活着的树枝上。
附近的房子都给毁了,但是却没有一幢给火烧过;游戏楼房的墙还都立着,门和窗子全碎了。红草没有了房顶的房间里恣意生长着。我下面是那个土坑,乌鸦还在边上争食。还有几只鸟在废墟上跳着。远处,我看见一只瘦猫弓着身子在墙边走过。但是没有一个人影。
同我当时的禁闭相比,那一天看起来非常眩目,天空是明亮的蓝色。一阵微风吹得地上的红草轻轻摇动了起来。啊!多么清新的空气啊!
《世界大战》作者:'美' H·G·威尔斯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Xinty665 免费制作
第六章 十五天里造成的破坏
我在土堆上遥遥晃晃地站了一会儿,完全顾不上自己的危险。当我待在废墟里的时候,只考虑到我们眼前的安全。我完全没有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也没有预料到眼前这个陌生的景象。我曾经想象着希恩变成一片废墟——我发现四周的景色变得非常怪异,仿佛来到了另一个星球。
这个时候,我产生了一种人类所难以体会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是受我们人类控制的动物所熟知的。我觉得就象一只兔子回到了自己的窝里,突然发现十来个人在挖一座房子的地基。这种感觉在我的脑子里慢慢变得清晰,让我在以后的好几天里感到压抑,在火星人的脚下,我们给剥夺了主宰的地位,不再是万物之主,只是动物的一种。我们在火星人面前,就象动物在人的面前一样,只能悄悄窥探,四处奔逃,躲躲藏藏;人类的威严和统治权已经荡然无存。
然而我这个奇怪的想法很快就结束了,我唯一能感到的只有因为长期禁食所造成的饥饿。往土坑的另一边看过去,在红草覆盖的围墙后面有一个园子,园里的土地还没有长出红草。这给了我一个暗示,我迈步进了齐膝深的红草,有的地方的红草长到了我的脖子那么高。茂密的红草提供了很好的藏身之处,使我感到很安全。围墙大约有六英尺高,我试着想翻过围墙,可是两脚却跨不到墙头。于是我沿着墙跟走了一圈,在一个墙角那里,我踩着墙上露出来的石头爬上墙头,跳进了那个让我十分渴望的园子里。我在里面找到了一些小洋葱头,两个菊芋和几个生胡萝卜。我把它们收集起来,翻过一道破墙,在血红色的树丛里朝沃金走去——就象走在巨大的血滴铺成的大道上一样——我脑子里只有两个想法:多找些食物,要是我的体力允许的话,逃离土坑周围这个不象地球的该死的地方。
我又往远处走了一些,在一个长满野草的地方发现了一些蘑菇,我狼吞虎咽地把它们都吃了,然后我就来到了一片浅浅的,褐色水塘边,那里曾经是一片草地。我吃的那点东西反倒让我感到更加饥饿了。起先,我对在这么炎热的夏天看到流水感到很奇怪,后来我才明白这是由于红草到处蔓延的缘故。这种奇怪的植物一碰到水就长得又高又大,异常繁茂。红草的种子洒进了威河和泰晤士河,它迅速生长,富含水分的宽大叶子很快就把两条河给遮没了。
后来,我在彼尼看见一座桥几乎全给红草遮住了,在里士满也是如此,泰晤士河水形成宽广但却很浅的水面,把汉普顿和特维根汉的草地淹没了。红草跟着水面扩散,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