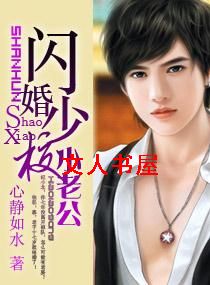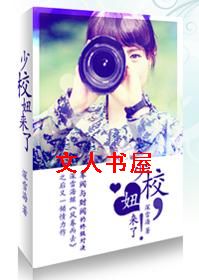旋风少校 作者:[苏] 尤里安·谢苗诺夫-第3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视着一个地方发呆,脑子里空落落的,只有一些毫无意义的只言片语在紊回──而且大多是一些词的后缀和动词的词尾。
最后,除了不同意审判战犯的条款外,他接受了美国人的全部提议。
“只存在一种犯罪形式,”他说,“那就是刑事罪。战争,正象我们的思想敌人断言的那样,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政治家是不受审判的,正如不能用监禁的办法惩办败北的棋手一样。”
希姆莱接受这些条件,使美国谍报人员证实了希特勒党内领导的分歧和瓦解──第一,证实了反对派将军们的实力;第二,存在着希姆莱这种能帮助实现政变的重要人物;第三,他竟能接受连‘保守的革命者’卡纳里斯在伊斯坦布尔与美国谍报人员谈判时都认为不能接受的条件。
所有这些与西方的谈判都是希姆莱的人在“摸敌人底细”的名义下进行的,即使元首知道了,希姆莱也会使他相信,这不过是在政治侦察中同敌人耍的普通把戏罢了。
但与此同时,希姆莱趁在希特勒那里的几次会晤的机会,特别留意观察那些参与反希特勒密谈的将军们的神色──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听过他们密谋的录音。
他注视的那位长一双微凸的蓝眼睛的将军显得局促不安,脸色红一阵白一阵,而后尴尬地笑了一下。希姆莱对他微微点了点头,也笑了笑。
这之后希姆莱得到了情报,说西方联络人、银行家瓦伦贝格对叛乱理论家格德莱尔说:“千万不要动希姆莱!只要整个矛头对准希特勒,他是不会妨碍你们的。”
在专门对方共产党人的盖世太保某处破获反对派中的急进组织与德国共产党代表建立的秘密联系之前,事情一直进行得很顺利。逮捕是在希姆莱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抓捕共产党人用不着高级领导人批准。但糟糕的是,盖世太保的人出乎意料地破获了那些与反对派中左派将领有联系的共产党人的秘密接头点。希姆莱知道的秘密逐渐为盖世太保知道了。整个组织的力量是可怕的,弄不好,该组织的这位创建者有被撤换的危险。此人在历届党代会上都站在元首身边,为元首的讲话鼓掌,并在自己的演说中赞美元首,但同时又在进行着交易,企图用元首的性命来换得他希姆莱自己的安乐。
个人专权的悲剧──尤其是在危急时刻──就在于它否定演化和发展的逻辑,在于不愿意重新认识僵死的教条,承认失败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方法的形式去寻找通向胜利的新途径。对此只有一条路可供选择──暴乱。希姆莱相信暴乱,认为这是保全他性命,保证他平安和自由的手段。所以他一直在等待。他可以一直等下去,直到盖世太保掌握了密谋分子中的青年派与共产党人建立的联系为止。希姆莱正处在十字路口上。一个软弱的人,即使他在银幕、照片上是强者的化身,只有在他诚心诚意地同他所信赖的人协商之后,他才能做出正确的抉择。在希特勒的这架机器中真可谓是一应俱全:党、政、军各种机关的密切配合,花言巧语的鼓动,蛊惑人心的宣传,青年和妇女的联盟,体育协会和杂技体育的庆典,盛大的检阅和民族意愿的演习──真是应有尽有,可惜只缺少一样东西:相互信任。父亲怕儿子,丈夫怕妻子,母亲怕女儿。
希姆莱在疑虑重重、心神不定的时候是孤独的。因此他表面上显得比任何时都更镇定,只是夹鼻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有些失神,而且他搓动双手的次数也比平常多了。
七月二十日见分晓。
希姆莱知道很多事情。可是他不知道,施陶芬贝格上校两次推延刺杀希特勒只是由于当时戈林和希姆莱都不在大本营。施陶芬贝格上校属于反对派中的左翼,他不认为除掉希特勒一人就可以消灭法西斯主义。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他从柏林军用机场起飞,去希特勒官邸商议组建新后备师一事。会议十二点三十分开始。豪辛格尔将军在一张铺在长形桌子上的大型地图前,一边从容地展示东线作战简略示意图,一边详细而又枯燥地分析大会中一些最复杂地段的形势。
施陶芬贝格在进军非洲期间失去了一条胳膊和一只眼睛,所以深得元首的敬重(元首格外珍视肉体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这时他在桌子下面拽掉英制迟发导火管上的栓头,把装着即将引爆的炸弹的深棕色皮包放到元首的身边,然后站起身,微微点了下头,对凯特尔小声说:“对不起,我有事必须同柏林取得联系。”
希特勒只是扫了上校一眼,脸上掠过一丝近似微笑的表情。凯特尔则不满地皱了皱眉头。他讨厌司令部要人作报告时秩序被打乱。
“俄国人,”豪辛格尔接着说,“继续以重大兵力在德维纳河以西向北推进。他们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迪纳堡西南。如果我们不把集团军调离楚德河,我们将遭到惨败。”
伟大与荒唐结合,悲壮与滑稽为伍──这也符合生活的逻辑。
豪辛格尔再也没有讲一句话:一团铅红色的火焰冲天而起,天花板塌了下来,平房的窗子被冲开了,上面的厚玻璃稀哩哗啦乱响,四处飞射──施陶芬贝格的炸弹发生了简单的和应有的化学反应。
希特勒从地板上跳了起来──蓝色的浓烟包围着他,浑身上下都是又苦又咸的烟黑。
“我的新裤子呀!”他用委屈的,略带嘶哑的声音大叫起来,“这是我昨天才换上的!”
接下来的一切很象是一位风格极为庸俗的幻想作家杜撰出来的一场闹剧:行刺后的五个小时内希特勒本来能够,也应该完蛋,但他并没有死。
如果从形式逻辑的观点分析密谋者们在夺权企图中的失败,那么显然,还应该作三点说明:第一,这与德国人的民族性格有关,对他们来说,命令即是宗教。已拟定好的“瓦尔基利亚”命令(该命令允许军队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尚未下达。第二,反对独裁者的密谋只有在所有参加者都准备为自己的理想献出生命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将军密谋的参加者们远不是每个人都象他们起来反对的那个人那样狂热。最后,第三,若要在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统治的国家里实现密谋,只有那些熟悉这一机构全部隐秘的人才能做到。但是将军们却认为:作为“国中之国”的军队可以决定一切。这是他们的失算。军队与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之间准备多年的厮杀是以军队的失败而告终的。
就在七月二十日当天,遵照戈培尔的命令,在宾德莱尔大街的一个庭院里枪毙了密谋的主要领导人。他们要求贝克和施陶芬贝格自杀。贝克开枪自杀,施陶芬贝格则拒绝了。
“有过失的人才用自杀结束生命。而我在人民面前没有丝毫的过错。”
他是在汽车马达的轰鸣声中被枪毙的。
希姆莱明白,在希特勒和戈林位于拉斯滕堡统帅部等候消息时,他只剩下有限的时间来消除那些最有影响的密谋者,这些人有可能猜到,他,党卫军首脑,是暴乱分子计划的知情人。他必须赶在党卫军的侦察人员逮捕所有密谋者之前,干掉能说出此事的人。
想消灭自己罪迹的刽子手是最可怕的。
希姆莱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恐怖活动。
对卡纳里斯,党卫军首脑既害怕,同时又完全不放在心上。他做出了正确的判断:这个狡诈的滑头知道──沉默是救命的保证。正因为如此,他才考虑是否值得舍弃他,尽管这位海军上将与那些被枪毙的将军以及盖世太保正在抓捕的人曾经关系密切;第一个被投如地牢的是那个曾在各种报纸上被称之为“帝国军事天才”的维茨勒本元帅。
希姆莱认为卡纳里斯只是与西方作赌的一枚辅币。
不过,幸好希姆莱没有来得及和元首谈起海军上将的命运这个谨慎的话题;元首倒是亲自发问了:“那个恶棍在囚室里表现如何?”
“您指的是谁?”希姆莱没有听明白,“这些坏蛋人数不少表现各不相同。”
“我指的是卡纳里斯。”
“他还没有被关进监狱,”希姆莱回答说,“明天我向您报告他的详细情况。”
就在戈培尔发表演讲,当众嘲笑说“这是一场电话暴乱”的同时,保安局政治侦察处处长瓦尔特·舍伦贝格逮捕了前军事情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卡纳里斯被撤职后,仍是卡尔登勃鲁纳的眼中钉。)
海军上将在同自己的爱犬告别后,擦去眼泪说:“舍伦贝格,爱狗吧,它们不会背叛。”
关于自己的老上司被捕的消息,贝格上校是半夜里得知的。当时克拉科夫盖世太保的头子把他叫了去。盖世太保长官没有抬眼看他,只是推给他一支笔和一叠纸。
“请把您和卡纳里斯,还有可耻的民族敌人施陶芬贝格一起工作时的情况写出来。”
贝格明白了: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卡纳里斯过去失宠,现在则到了穷途末路。他在柏林见过几次施陶芬贝格,过去他是民族英雄,现在成了民族敌人。
贝格机械地写起来,一行行的字象平时一样既均匀又工整。他列出了同卡纳里斯和施陶芬贝格见面的时间,不过他现在十分镇定,头脑象数学一样精确──这是他天生的习性。
“看来,这是上帝的安排。我跟俄国姑娘耍的那套把戏现在可能成为我的救命符了。我现在不能再耍把戏了,而是要真的为他们工作。显然,要想从我陷入的这场混乱中挣脱出来,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只是盖世太保别把我调离侦察工作。他们能把每个军事侦察人员都看成是潜伏下来的卡纳里斯的追随者。他们不想把卡纳里斯看作是企图用元首性命来拯救千百万德国人生命的爱国志士。他们永远也不敢放肆,因为他们内心有一种无形的禁令,他们连这种念头都不敢有。这既是他们的力量所在,又是他们悲剧的根源。如果我现在开始为红党工作,日后我就可以找到辩护的理由。以保卢斯为首的‘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当然取代不了希特勒,但这毕竟是某种力量。自然,若是他们现在把我关进监狱,那可就糟了。他们会的。应该为那姑娘做好逃跑的准备。放走她。要让她不是从我这里,而是从盖世太保的人手里逃走。千万别把我关进监狱,上帝保佑!那样我还得求助于盖世太保的同事。我要对上司说,在民族危难时期,应该用党的忠诚干部加强军队。我要把那个姑娘带到电台去,交个一个党卫军分子,等到那人对姑娘习惯了,我就给他找个娼妓,送给他白酒。党的工作人员被希特勒的清教徒式的道德训诫折磨得苦不堪言,党员不许喝白酒,女人不准涂口红,说‘这是向美国财阀挣扎的走狗出卖祖国的利益’,我相信,盖世太保的人也同样贪杯好色。在希特勒的禁令中,除了盲目崇拜、对正常生活的嫉妒或蒙昧无知还能有什么呢?难道他不知道禁果是甜的吗?国家内部生活中禁令越少,敌对的思想、经济、政治就越难于渗透,因为那些东西无机可乘。当人民什么都可以做──当然只限于理智范围之内,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不允许野蛮行为──那么象我这样的侦察员在那样的国家里也就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