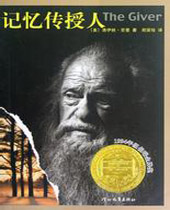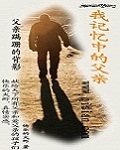记忆碎片 :让我们歌唱八十年代!-第2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够,根本不用看什么书。
大学毕业几年后,我的弟弟也考入同一所大学。我送他去学校报到,先在一家韩国烧烤店痛吃一顿。他像所有步入人生旅途的毛头小伙子一样踌躇满志,还向我讨教人生真谛。那天我高兴得喝多了,脑子格外好使,人生的一幕幕情景如电光火石般一一闪过,就对他说:“咱娘经常说,‘力气不用也是闲着’,‘少说两句,别人不会拿你当哑巴卖了’。这两句话,就够用了。”
家母只有小学四年级水平,她活得踏踏实实的,这两句话,也让我们兄弟受用不尽,比别的话都管用。
看许多读书多的人,那一肚子学问,只不过保证了他们说话写文章显得更漂亮更有理有据,做事情更能给自己找借口下台阶。他们的人生道理,并不是用来指导,只是用来解释自己的行为。事实上许多做出义薄云天之事的人,跟读书多否没什么干系。那些丧尽天良的人,也多不是文盲。
把几本书垫在脚下,确能显得比别人高些。但你真正的高度,还是取决于自己。
都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
1997年,我离开生活战斗六年之久的石家庄,来到北京,开始了职场漂泊。当时心中是很兴奋的,那种既冲破牢笼又投入熔炉的感觉。
进驻北京后的一段日子新鲜而刺激,干的活经常能传诵一时,口袋里的钱经常是厚厚的一摞,同饭局的吃货经常是名动天下的大佬,真的是既有里子又有面子。
但是,但是,缺了什么呢?
在那三年多的时间里,换了四五处住所,从地下室到合租户,也借宿过别人的办公室,必须在别人上班前离开及人家下班后潜入。这些并没什么值得夸耀的,但一个人扛着自己的小包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委实可怜,经常感到是个不完整的自己,像玩具风筝在空中飘来飘去。
为什么会有这种心里没底儿的感觉呢?像我这样的普通人,没有陈寅恪先生那样照相机般的记忆力,在读书的过程中,早已将一些思想、记忆、感觉甚至自我转移到了书内,好让脑子不致那么拥挤。那些读过的书也已经成为大脑沟回的延伸、小件行李寄存处、谋生手段的一部分。这时的我,已不单纯是一具身高一米七十体重六十六公斤的肉体,把那些读过的书、写过的字都算进来,才是整个的我。但那一部分,却被丢在了石家庄家里的书架上。
当那些书不在你身边,不能让你随时掰开引证一番时,你的思想是不完整的,记忆是不完整的,灵魂是不完整的,自己也是不完整的。于是那段北漂的日子里,我经常急得一脑门汗,把手伸出去,也是没抓没挠的。有人能身作浮云常傍日,有人能处处无家处处家,有人能将异乡当作故乡,有人能将流放当作远航,但我,却连那一堆书都离不开。
朋友,在我死后,如果是你来处理我的遗像,一定记着,除了这张肉包骨头的脸,还要把我身后的那个书架也取进画框。
用抽屉锁住自己的秘密
在喜爱的书上留下批语
信投进信箱,默默地站一会儿
风中打量着行人,毫无顾忌
留意着霓虹灯闪烁的橱窗
电话间里投进一枚硬币
向桥下钓鱼的老头要支香烟
河上的轮船拉响了空旷的汽笛
在剧场门口幽暗的穿衣镜前
透过烟雾凝视着自己
当窗帘隔绝了星海的喧嚣
灯下翻开褪色的照片和字迹
这首诗名叫《日子》,作者北岛,描募的正是我最愿意过的一种生活。当我一往无前地扎到北京怀抱里的时候,却完全没有想到,事实上自己就是在远离那样的状态。
如今流行用许多指数来量化一些东西,如恩格尔指数、GDP什么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指数来统计这样一个时间比重——在你一天醒着的时间里,有多少是为了温饱而奔波?姑且称为“温时指数”吧,我相信这是衡量一个人或一个城市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
北京无疑是全中国“温时指数”最高的城市。
在北京,每天醒着的时间至少有十三个小时——这首先是一个必须要保证的时间数,其中大约有三个小时需要耗在路上,交通问题是北京最可诅咒的地方;大约有三个小时需要安排各种饭局,饭店老板是北京最可羡慕的职业;大约需要跑三个地方来办各种事儿,这里净是些没多大必要但你又不得不办的事儿;大约能接到三个能挣钱的订单,最好一个也别推掉,因为打车吃饭租房喝酒买书看演出都需要钱,别人还羡慕你有这么多挣钱的机会呢;白天跑完了,晚上需要坐在电脑前处理接到的那些订单;一天跑完了,临睡前躺在床上,还需要拿出三分钟把第二天要做的事情和要走的路设计好……
坐在马桶上的时间大约是十三分钟,因为这是一天中惟一可以看会儿书的时间;偶尔有点儿闲空,会拿出三秒种的时间同情一下自己,看我像一个蚂蚁一样在骨灰盒般的高楼大厦中穿梭,这里居不易。
北京不是我想象的黄金天堂,都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
但我还是来到了北京,然后继续怀疑这样的生活。陈寅恪总结王国维的自杀,说是因为他已经被那种文化所化,我也已经被北京文化所化吧。
我为自己抵抗不住这种选择而沮丧。也许,我根本就不是一个坚定的人。
如果不是二十八岁那么年轻,我大概就不会选择漂泊北京了。
石家庄那样的中等城市,待着好舒服啊,“温时指数”好低啊。在那里,我发明了许多睡觉的方式,如“头碰头”,即从晚上十一点睡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或“头盖头”,可以从凌晨两点睡到第二天下午四点,直到睡得睡不着为止;兴之所至下,我可以半夜从床上爬起来,溜达到朋友家里找他聊会儿天(那个城市出租车的起步价是五元,两公里,我所需要的路程多在这个里程之内);在那里生活实在不需要许多钱的,哥几个去吃次火锅,饱得直哼哼,算下账来,七个人花了六十元,我那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交给单位不到六千元就算自己的了……在那样的一个城市里,每天只需拿出几个小时应付一下就可以满足自己的温饱,剩下的时间和空间全是自己的:用各种姿势躺在床上看书,跑遍整座城市去寻觅一张影碟,打麻将和拖拉机的战士更是随叫随到……
我们往往是抱着学以致用的态度来看书,在悠闲的地方读书,再去忙碌的城市里施展,被那里吸干你的精血后,然后无聊地老去。我就是这样甘心把自己交给了一个吸血鬼。
像我比较佩服的两个人,李皖(27)和三七。李皖在武汉,当年的一帮媒体精英纷纷到了北京或广州或外国,做成了一些看起来很大的成就,李皖还守望在武汉。这几年过去后,大家升官发财泡妞离婚买车买房,李皖却做成了许多事儿。几个当年的酒友聊起故事,比较一致的结论是,也只有武汉那种寂寞平静的生活,才能让李皖修炼成那样。
当然,不成就什么事业也行,就像三七那样,请允许我抄录一段写他的旧文:
我们在这世上活一遭,总是需要些证明的,有人用学问,有人用才气,有人用金钱,有人用不金钱,有人用某种级别,有人用某个类别,有人用发表的若干万字,有人用阴茎勃起的若干分钟。
但有一种人,活得很沉默,很市井,很没劲。
因为他实在懒得跟别人说些什么。
因为他实在不需要什么身份来装点门面。
因为他实在是提不起什么劲来跟这世界较真。
也只有在石家庄那样的城市,才能包容三七这样的活法。而在北京,哪怕你的不作为,都像是在作秀。
读书是世界上最不坏的事情
2000年的某一天,我从北京回到石家庄。尽管此前也是频繁往来于这两座城市,但这一次,却是怀揣若干份调动文件,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走。
下了大巴,再打车往家赶。出租车驰过的地方,育才街那个电线杆子还躺在路边,哥几个曾经穿着大裤衩坐在上面探讨人生,美女一个个地从身边滑过;科技馆礼堂如今改成了家具店,而此前这里周而复始地放着老电影,永远是固定的搭配,《罗马假日》配《鸳梦重温
》,《出水芙蓉》配《魂断蓝桥》,哦,还有我不朽的《野鹅敢死队》;梆子剧院门口烤羊肉串的小摊依然香烟缭绕,盛夏的傍晚,几个人将其包下来,躲在阿凯的吉普车后面,光着膀子,喝着冰凉的啤酒……那真是神仙般的日子。
流浪的脚步何时能停?我分明感到一种惆怅。
档案、户口、工资单、保险、住房公积金……一个个公章盖下来,一张张脸浮现在眼前,一顿酒接着下一顿酒。去保卫处退自行车存车牌(国家事业单位就有这种福利)时,和小李互道珍重。当年单位搬进新办公楼,淘汰下许多旧家具,我瞄上两个书架,就想随风潜入夜,运物细无声。那两个书架是六十年代产物——用《U…571》中美国兵的那句话夸一下它:“德国佬造的东西真他妈结实”,我根本移之不动,就去传达室叫了小李来帮忙(那时还不知道他姓什么),才搬到宿舍里。因为这次监守自盗,小李与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又去阅览室还书,有若干本实在不愿意还了,老着脸说扣我钱吧。钱倒是其次,像《宋诗选注》才七毛三,就是按照规定罚十倍也没多少——其实这本书已经出了新版的,但我一来喜欢那种小三十二便携式开本,二来重印次数多的书字体发虚——我是怕被别的借书人骂。但阅览室的人们说,不用罚钱了,去给我们买些雪糕吧,反正这些书搁回来也没人看。我忙不迭地下楼,心里哼着小曲。
拿着保卫处、总务处、阅览室等一大堆部门盖过的章,表示都结清了账,我才得以将调动手续办完。
再回来,这里也是异乡了。
石家庄有几家书店,几年来,我见证了他们的创业、兴盛或衰败,也与那些老板有了不大不小的交情。这次告别,也包括他们。
青园街一家小店,门脸不大,却颇有品相,老板下一手好围棋,是这个城市里众多读书人的经常光顾之地。几年前,我在这里发生过一段故事。
有天中午,我踱进书店,店中没有几个人。我注意到老板脸上的表情有些异样。注意一看,原来正在选书的顾客中有一个人是这个城市的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我们经常要在电视上见到的。
我挑了两本书,然后去结帐。由于我是常客,所以老板拿出计算器来算一下,要给我打一个折扣。这大概需要一段时间,我便在旁边等着,这时一只手伸过来,将几本书压在老板的计算器上:“来,先给算一下。”
我扭头一看,书记正往书店外面走,结帐的看样子是他的秘书或司机之类。
老板只好将我的帐目先销掉,然后开始打他们的帐。
大概是天热影响情绪,或是出于对秘书这一人种的天生反感,一贯被人加塞惯了的我这次爆脾气发作,用手拍了一下已经挤在我前面的这个人的肩膀:“唉,怎么回事?”
“怎么了?”那人很奇怪地看着我。
“有没有一点读书人的样子?”
“老赵有急事。”那人说。书记姓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