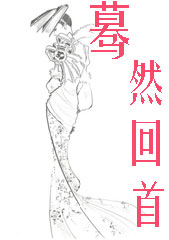不堪回首 -李梧龄1016-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不少便宜,就把表送给了乡下人。不料此人拿了表到处炫耀,其他人怂恿他去钟 表店估价。这一来可糟了。原来这表国内市场是没有的,便追查来历,当然礼品是允 许的,但不能出卖或转手,否则便作为走私。于是表被没收,还要付税金,他则受到 了警告处分。
不久,以这处分为由他被调离区政府,到龙华的一个精神病医院工作。有一天晚 上他值班,走过一个约束间前时,一个因发病而被关在里面的女病人通过小窗口向他 要水喝,他理应将水送去给她,但一时大意就把门开了让她自己去取水。不料等他一 个圈子走回办公室时却发现那个花痴女在他办公室等他,脱光了衣服要求他“帮忙解 决解决问题。”他被裸女抱得紧紧的也不免心动,然而终因胆怯而且年岁大了并未干 成什么事。却被女的臭骂了一顿“无能。”
又过了几天,这女的和一个男花痴双双逃走了,恰逢又是在他值班的晚上,来了 电话,说是在浦东某旅馆被查到了这两人在要求住店。于是他打电话公安局要了车去 把这两人接回来。女花痴一见到他勃然大怒说“黄某人!我叫你解决解决问题你不肯, 如今我和别人解决问题你倒竟敢来抓我了。”
这事当时被作为笑话传开了。不料后来却因此以违法乱纪被关了进来。在提审 时他当然就此事进行辩解,却不料提审员也不过把此事当笑话取笑他。然后令他从 头说自己的历史。这是他们的一贯手法,先不提具体问题,而要你无边无际地供述。 他们就是想套出你更多的“罪行”来。黄的历史可谓复杂了,故提审耗日持久。弄 到最后他才明白过来,原来是为了下面的两件事被关进来的:
在他失业时,有一次看见报上有个老太太招聘干儿子的广告。他就去应聘了。 其实那老太有一个侄儿,招干儿子的主意就是他出的,真正的想法是要找个生意上 的帮手,如成了干亲则可望靠得住些。那人见他老实就成了此事。有一次那兄长派 他去浦东高桥某地收购棉花,当地的乡下人问他姓名,他不愿说又不能不说,便随 口看着海边的黄沙说“我就叫黄沙”,上海话的“沙”和“所”同音,乡下人便开 玩笑叫他“黄所长”。
他这个干亲后来生意失败,他也不做干儿子了。然而多年以后,这个外号却是 他那时吃官司的原因之一,反反复创地盘问当过什么所长?因为他几次三番地说自 己的历史,都无当过官的痕迹,就多次要他重述,最后才拍桌子大骂“你当过所长 为什么不交代?他这才如梦初醒将此事说清楚。为了猜这个哑谜还上了手铐!这使 我想起以前听说有人因下象棋爱以当头炮开局被取了个炮兵司令的雅号而大倒其霉 的故事。
第二件也是他失业时的事,他在外滩碰见一个老朋友问他
“近来混得怎样?”
他答道“身上只剩二角钱,还不知明日吃什么呢。”
那朋友便拉他到十六铺一个海员工会去登记。原来他曾在一条去新加坡的船上 当过一个航次的理货。但因受不了晕船之苦而不干了,但也总算是个海员吧。他去 那工会是去混饭吃的,反正在你被某船招聘前,那儿每日三餐总有供应的。在那儿 混饭吃的人还真不少,每顿要开好几桌,而且每桌一般也坐不满,因为登记的人若 临时有处去吃饭还不一定来。
有一天,江亚轮(48年冬沉没在长江口)到上海,该船船长招待失业海员上船 吃了一顿饭,这原是常有之事。然而却被问得死去活来,问那顿饭时某人说了什么?
“谁还能记得呢,”老黄说“无非是说某个菜好之类应酬话而已。”
为了这两件事他就被关了一年以上,而前途还未卜呢。老黄说起他50年在区 政府拍的一张集体照,无限感慨地说那照片上的人十之八九都在历次运动中倒了下去。
小王从另一个号子里来时还带来一个故事。那是说的一位叫杨华亭的人。此 人毕业于延安抗日大学,被派往天津做地下工作,所做的是开设一家药铺,以为后 方搜集药品和电池,搜集到的东西是有单线联系的人来取的。天津沦陷时联系断了, 他不得已而携款逃难到了上海,但同样地找不到组织关系,便将资金在上海同样也开 了一家药店。
解放后,他到军管会说明情况,并上缴全部资金。但被告知这要算携款逃跑之罪。 不久被捕,以其自首从宽被判十年。
那时的上海市监狱还关着许多国民党时判刑的汉奸,而新关进来的反革命犯也还 象个反革命,也许有什么藏匿的武器、电台之类,而看守还都是留用的警察。政府并 不信任这些看守,所以当犯人写交代材料时是决不让看守经手的。他那时便在狱里当 “事务犯”即管杂事的犯人头,反到有时令他代不会写字的犯人写材料。
有一次关进来了一个犯贪污的未决犯,他是杜蔚然。杜情绪消沉,想自杀未遂。 杨就去劝他,他自恃老革命那里要听犯人的劝告?杨就亮出了自己在抗大等的革命经 历,于是两人有了共同语言,杜不再想自杀,交代了贪污受贿的事实。不久竟获释了。
过了不久,有一天忽然喊有人来接见他,那又不是接见的日子,接见还竟在监狱 的大会客室里进行。他疑惑地走进了会客室,只见沙发上坐着的两个人站起身迎了上 来,握手寒暄后杜蔚然说“我现在是公安局副局长了,”又指着身旁提着酱鸭、水果 的人介绍“这位是闸北分局的某局长。”他们慰问并问杨有何要求,杨答以希望能安 静一些,因为他经常代人写材料也已不耐其烦了。
不久,他被调到苏北大丰农场。他在那里仍是一个特殊犯人,每天只要吹哨管 其他犯人出工、收工即可。后来,杜局长又去视察农场,到了以后就对农场吵长嚷 着要找老杨,所以农场干部没有人敢得罪这个特殊犯人的。在苏北过了几年,他又 嫌生活单调通过杜局长回到了上海劳动被服厂。总之没几年他被以表现突出为名减 刑后成了上海青浦县的一个劳教农场,即青东农场的特殊场员,反正除无法改变身 份外他是不吃苦的,连农场吵长也要让他三分。象这样的特殊犯人青东农场还有好 几个,如当时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的岳丈就是一个,这老混账在无锡胡作非为调戏 女演员,实在闹得太过分了,被判了刑,但这个市委书记还是有办法把他从无锡弄 到了上海,安排在该农场。在文革中老混账惶惶不可终日,天天打听着陈的消息, 而随着杜蔚然在文革中的倒霉,杨也关进来受审查。杨说有一次杜去视察,见了他 问要不要带他去见见黄局长,他回答说我有你杜局长照顾已很够了就不必了吧,他 说幸亏未去见黄赤波,否则还要不得了。
再说到我自己,关了约一个月后便开始提审,第一审是他们八个所谓公、检、 法的人同时出场的,其中我认出一个叫姜百清的农场干部,当时是农场中的造反派人 物,从他的外号“讲不清”也可见其为人了。那年头公安、检察和法院三个理应相互 独立的机构竟然可由同一个人代表,其法制的荡然无存亦可想而知了。我在第一审中 重申了在放马场拘留所的话,断然否认有任何罪行。他们中的一个女的沉不住气大叫, 骂我嚣张。
后来主要由八个人中的两个为首的提审我,在当时的形势和制度下,任何人都无 法避免要说自己的历史,他要求你详谈过去的经历而算计着如何找出可害你的问题。 直到翻来覆去问得无可再问了才逼他们提问。这种审讯方法从前面黄某的故事中就可看 到。是和现代化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完全违背的。
最后他们摊牌问我的问题还是当年的老一套,什么逃国外、打游击、小集团之 类,而加出的一项是更莫名其妙的。
问:“你什么时候解除劳动教养的?”
答:“1966年初。”
问:“为什么你会解除劳动教养?”
答:“是你们给我解除的,我怎么知道为什么?”
问:“有什么人事前暗示你将要解除劳动教养?”
答:“不可能有此事。”
实际上我为什么会有机会在劳教期内探亲?为什么会解除劳教这帮人也不知 道。我从提审的问话中体会到这案件是农场中两派斗争的产物,造反派力图制造 “走资派”即原农场头儿们的罪状。构造出了当年白茅岭右派队中有一大反革命 集团案被“走资派”包庇的假案。如果我们挺不住而屈打成招,那末今天我也写 不成回忆了。
然后就诱我上当承认有反动言论,有一次居然煞有介事地拿着一叠纸说:
“这是黄建基检举你的材料,你不说也不行。”
我说:“我也许记不得了,但我相信黄不至于瞎说,那你们就拿来我签名 吧。”为此事,黄被戴了半个月手铐,逼他检举我说
“为什么李某如此信任你?”这也算他的错吗?人不可以被信任吗?
还有可笑的是忽然把我们都集中到一间屋里,然后还推推搡搡把唐焕新推 了进来,我们知道唐也成了此案的牺牲品。人齐了,忽然那干部开始朗读毛的文 章《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还令我们一句句地跟着念,念 了许多遍,这又不是咒语,我们也和杜聿明、南京政府完全是两码事,这真叫人 啼笑皆非。
又有一天上午,我被那农场的姜百清叫去提审,那是一间大屋子,我背 对着门,被锁在椅子上后,只见那姜百清坐在提审席上咬牙切齿地朝我怒视了 好久,然后忽然一拍桌子怒吼道:
“你只承认这些,叫我们怎么判你!”
我说:“你这是什么话?凭什么非判不可。”
他于是恼羞成怒走了下来对着我就打了一个耳光,我马上指着墙上的标语 大叫:
“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时躲在门外从观察孔向内看的几个上海公检法 的提审员从我背后走了过来,喝道“不许胡说,谁打你了。”我指着地上被打碎的 眼镜说:
“没人打眼镜会碎吗?”他们不理我却将眼镜拿去,押我回到监房去了。
下午,我被叫到楼梯拐弯处的一间小屋里,主提审员和颜悦色地将修好的 眼镜交给我(后来我才知道是他们打电话叫我妻去修的,而她那时也被学校关在 私设的牢房,即所谓的牛棚里许久,要诈她说出不利于我的事来。)然后对我说:
“你不要叫冤枉,本来在你的档案里有着一个很大的问号,现在我们都替 你澄清了。这不很好吗,关这几天弄清了这么大的问题不是很上算吗?谁让你要 当头头呢,许多事都是别人的,例如明明是别人要逃跑又怎么也扯到你头上了呢。 现在我们帮你把问题都搞清楚了,你出去以后交朋友要小心谨慎,我不希望再见 到你。”总之他对我好言安慰一番。
又过了半月,忽然我们又都被用一辆中吉普押回了农场,仍在放马场拘 “留所关起来。我被关在一间大房间里和两个逃跑的在一起,他们几位则分关 各牢房,仍互不能见面。关了又有约半月,忽然一天把我们押到总场,总场正 要开大会,会场气氛紧张,我们在一间小房间里被绑了起来,我是被特别地五 花大绑的,还在颈上套了一个细绳圈,将我们押到大会的戏台上,每人被两个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