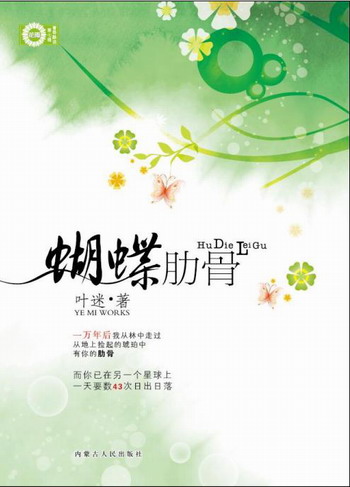蝴蝶效应-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店之类的?所以首先,我们应该调查各种旅店,我想通过电话来查,直到查到她为
止。你看呢?”
“祝你好运,小伙子,这个由你来干。在你向日本各类旅店的服务生询问他们
的客人并试图弄懂你得到的回答时,我去拜会拜会那个叫南义的家伙,朱丽可能见
过他。这样行吗?”
“行。听我说,我查过这座城市的资料。它很庞大,你知道,就像多伦多,至
少有两百万人口。生意人、游客,这些都是饭店等行业赖以生存的基础,他们遍及
每一个角落,这我懂,而且在这件事情上不用英语还不行呢,相信我。”
“我想你是对的。有个建议,给自己行个方便,去当地的旅游信息中心试一试,
也许车站上就有一个。就像你说的,在偌大一个城市里,他们可能有懂英语的服务
人员吧。不要别的,就要一份旅店名单。如果你能在那里找到人帮你打电话,那效
果肯定会更好。”
“好主意,就这么办。我会在她住宿的旅店里给咱们俩也登记上房间。
与此同时,你就去找那可恶的南义。怎么样?”
“行。就假设她在某个地方登记了住宿而你也能找得到好了。”
“那么但愿如此吧,对吗?”
海伦和威尼共同商议着他们的未来计划。离开东京两小时之后,他们抵达名古
屋。列车非常准时。
10。名古屋
名古屋火车站是一个功能繁杂的地方,在日本,火车站本身仅仅是一系列单位
的中心纽带。名古屋火车站周围的单位包括地下通道,购物走廊,连接单个地铁线
路的进出口,三条地铁线路,一个公共汽车终点站,中心邮局,以及一个旅店,办
公大厦和百货商店的群落,等等。数里长的地下人行通道在成百上千的商店、旅馆
和咖啡屋之间迂回曲折地延伸着,通道的尽头以及突现眼前的楼梯深井又把你带到
陌生的街道之上。这些精心的设计却让每一位外国或国内的陌生旅客如坠云山雾水
之中,不知所措。大多数国内的旅客读得懂那些标识牌,而外国人只能望牌兴叹了。
不过,既然骄傲地自诩为“国际城市名古屋”,自然也有一些被写成罗马字母或英
语的标识牌。这种牌子在这儿简直太多了。问题是如何从铺天盖地侵扰着早已疲惫
不堪的旅游者们视线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标识、图片当中,选取一些有用的信
息,然后才能跟着前行不致迷路。
海伦和威尼还算幸运,他们离开站台一进中央大厅,便瞥见了名古屋旅客咨询
中心的标识牌,于是扒开人群,兴冲冲地向标识牌指示的方向奔去。
事实上,威尼在前面开路时,神色漠然,一片迷茫,海伦则提着行李箱紧紧尾
随其后。
“请让我看一看名古屋的旅店名单。”威尼向柜台后面一个穿着整洁的中年男
子说道。中年男子不解地瞟了一眼眼前这位长相粗野的个子高大的外国人。看样子,
他是过于自负了,满以为自己的英语别人也听懂了呢。威尼拿起一本英文小册子翻
着,目光停在名古屋市区的地图上。沿地图的一侧列着一长串旅店的名字,一共有
四十九个旅店的名称及其电话号码。蒂伦在小册子的空白边缘上写下“朱丽·派普”
四个大字,然后把小册子翻转过来面对中年男子。
“好极了。现在我要你逐一给这些旅店打电话,查找一个名叫朱丽·派普的女
人住在哪一家。”中年男子疑惑地瞪了他一眼,嘴里叽叽呱呱说着什么,伸手抓起
电话。海伦也目睹了这一幕。这时候,另一个职员也译好了南义的地址,并把它写
成连出租汽车司机也看得懂的简单文字。如同日本一般的公共场所一样,这里也是
无处可坐。海伦离开柜台,靠在墙上,凝望窗外扰攘的人流。
“搞定!”威尼挥舞着手中的名古屋车站的地图得意洋洋向她走来。“朱丽就
住在名古屋宫古饭店,它就在车站附近,一直穿过地下通道走到宫古大道的尽头便
是。根本不必坐的士,甚至不必走到街上。”
“真快。”
“没错,是名单上的第三个。很走运吧?否则我们可能会在这里耗上一整天呢。”
威尼自得其乐起来。他举起自己的皮包,然后做宽宏大量状,把海伦的包也提了起
来。“这个我来拿。我一个人去宫古饭店登记住宿吧,你见了南义后在饭店跟我碰
头。好吗?”
“好的。”
“嗨,跟我在火车上说的没什么两样吧?”
“不错,确实如此。”
“今晚的酒我请了。”威尼笑着步入迷宫般的地下通道里。
11。初遇庆子
南义会计事务所位于市区一幢写字楼的第八层。乍一眼望过去,仿佛就是由一
个巨大的房间加上一打左右坐在计算机和各种会计事务所必备的设施之前的人们组
成的。海伦走了进来,不安地四处张望。坐在距离大门口最近的一张桌前的一位稍
有姿色的中年妇女急忙笑容可掬地迎上前来,并不住地点头哈腰。接下来便是这位
白领丽人一连串的叽里咕噜的发问,海伦听得迷迷瞪瞪,一头雾水。
“你会说英语吗?我不懂日语,我叫朱丽·派普,我要找南义先生。”
海伦一字一顿地大声说道,如同一个说英语的人打电话时遇到了一个不会说英
语的人。结果毫无反应,显然这女人不懂英语。谁也没有扭头,但海伦知道整个屋
里的人都在等着她来解决这个问题。她便操起从伯利兹《旅游日语》中学来的最为
初级的日语一字一句地说道:
“这儿有谁会说英语?我不会说日语,我叫朱丽·派普。”
那个女人随后也迸出了几句日语。仅懂得几句足够发问的话而听不懂对方的回
答看来还是毫无意义。海伦摇摇头,又用审慎的英语缓慢地说了一遍:
“我不懂日语,请原谅。这里有谁会说英语?”
坐在后面的一个年轻女人站了起来。她简要地向那位早已如释重负般退回原位
的中年女人说了几句,然后转向海伦说:
“我叫上木庆子,很高兴见到你,我们一直在等你。请跟我来。”
她领着海伦穿行于一张张办公桌之间,来到一扇极隐蔽的门前。这扇门又引出
一间小小的私人办公室。里面有两张桌子、一对椅子和一个空空荡荡的文件柜。海
伦暗忖这就是南义的办公室,可能也是他的事务所里唯一的私人办公室。庆子在其
中一张椅子上坐下,向海伦指了指另一张。
“我很抱歉,南义先生今天不能来这里跟你见面。你来真是太好了。我们都在
为你担忧,伯克先生还打过电话问你到了没有。希望一切都还顺利,没遇上什么麻
烦吧?”庆子的英语非常流利。
她二十八九岁模样,身材娇小玲珑,齐肩的长发与白皙的面庞正好相称。
她身穿蓝色衬衣,外罩宽松的白色真丝短外套,脚上是一双黑色线口无带皮鞋,
与裙子搭配得非常和谐。从她的外表和言谈举止来看,她是一个见过世面而且颇有
城府的女人。海伦也不管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便直接将其与受过西方影响的人物
等同视之。
“谢谢,我很好。很抱歉让你们担心了,为此请接受我的道歉。至于意料之外
的情况嘛……无论如何,我现在来这里是代表伯克先生准备履行他对草下先生的承
诺的。”
听到草下的名字,庆子漂亮的眉毛顿时微微收缩了一下。
“是的,很好。南义先生会感到高兴。我们为草下先生管理业务,他有很多生
意。他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繁忙的人。”
“我也这样认为。”海伦好奇地注意到,庆子一贯流利的英语竟然有些磕巴起
来。“我希望这笔八千美元欠款的延期交付还没有给草下先生造成过度的不便。”
海伦说完扬了扬眉毛。难道像草下那样的重要人物会因为少了这区区一笔钱而有所
不便?这是不言而自明的。
“没有,没有。不是这个问题。我只是关心你,派普小姐。你知道,因为伯克
先生来过电话,像出了什么事似的。就是这样。那笔钱根本无所谓。”
庆子跟前桌子上的电话铃响了。海伦把身子倚着椅背,一声不响,尽量避免引
人注意。这种“逐渐被遗忘”的伎俩是她早已谙熟的。她全神贯注地盯牢电话,试
图从这场用“外国语”进行的短暂的交谈中获取些什么。从庆子提高八度的声音,
频频地点头哈腰,以及每隔两秒钟便“嗨”,“嗨”,“我明白啦”的样子,海伦
猜测电话那边的是一位男性上司,也许是南义,也可能是草下。在谈及某一点时,
庆子向海伦迅速瞥了一眼,显然,那人在询问她的情况。管他是谁呢。在庆子作出
回答之后——可能对她的拜访者描述了一番——便陷入长时间的沉默。接着又是一
连串的点头哈腰和“嗨,嗨”
声。庆子似乎在接受训斥,或许是关于海伦的,或者可以说,是关于海伦不得
已伪装成的朱丽的。
接下去的半个小时里,庆子给海伦叫了一杯茶。她是彬彬有礼地通过电话让那
位“白领丽人”连同茶托一起端上来的。那位丽人依然是一副点头哈腰的笑眯眯的
样子。庆子和海伦一边品着绿茶,一边闲聊,聊的多是海伦对于日本的印象之类的
话题。庆子对海伦——朱丽在日本呆了多久,她的所见所闻,她在名古屋的住所以
及下一次她计划去什么地方,去多长时间等等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真像是热情周
到的主人对客人细致入微的垂询一般。海伦提到了威尼说过的那家车站旅店,然而
礼貌地没有发表评论。她说她想去京都看看——这是旅游者不可不去,而且可以迅
速到达的地方。说这话时她的视线穿过了庆子的头顶,庆子则希望海伦有时间去参
观参观名古屋的风景名胜,比如名古屋古堡、寺院和博物馆等。或许她还可以陪同
海伦游览?她不敢冒昧地与海伦共进晚餐,不过也许她们可以安排一下第二天的游
览计划?名古屋值得一看,庆子向海伦保证。海伦勉力装出兴致盎然的样子。她没
有提及威尼·蒂伦。
茶水饮毕,礼节性的询问也告一段落,于是言归正传。海伦移交了八十张面值
一百美元的钞票,并收取了一张印制精美的浅黄色收据,上面有日英两种文字的漂
亮手写体,还有庆子的亲笔签名和她的私人印鉴。在日本,办理国外资金交易是非
法的,两个女人对此谨慎地闭口不提。
庆子陪着海伦穿过人头拥挤的办公室,一直把她送到前门。又经过一番彼此客
套话别,海伦才离开这儿。
12。酒吧谈话
威尼坐在饭店酒吧昏暗的灯光下,海伦发现了他,便走到他的身边坐下,要了
一瓶爱彼森啤酒。威尼交给她一把房门钥匙。
“这是你的,我就住在你的隔壁。你猜厅堂另一边住着谁?”他倒像在自己找
乐似的问道。
“朱丽?哦,妈的!怪不得你要同我住在同一层楼。她什么时候住进去的?住
多长时间了?你弄清楚没有?”
“当然啦。她是昨天住进去的,那时候你正在怀疑她是否已经乘坐东京至名古
屋的那趟火车走了,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