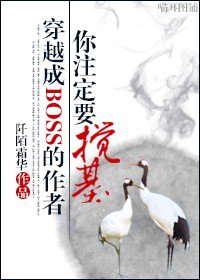三兄弟 作者:约翰·格里森姆-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们没有看守。”斯派塞回答,“记得吗?那是个戒毒所。他们有心理顾问。”
“可它是一级防范的禁闭场所,对吗?那就有大门和围墙,肯定周围有一两个看守仑假如里基在浴室或更衣室受到某个对他的肉体感兴趣的下流看守的袭击,那会怎样?”
“不能是性攻击。”雅伯说,“那或许会吓着柯蒂斯。他会认为里基得了性病什么的。”
于是他们一边为可怜的里基制造更多的痛苦,一边编着故事:他的照片是从一位囚犯的公告牌上取下来的,由他们的律师在一家快速冲印照相馆印制,现己邮寄给全美十几个笔友。照片上是个微笑的大学毕业生,穿着海军蓝的毕业礼服,头戴方帽,一个非常英俊的小伙子。
他们决定让比奇花几天工夫斟酌新故事,然后起草给柯蒂斯的下一封信。比奇就是里基,就在那个时候,那杜撰出来的受尽折磨的小伙子正分别给八个不同的、有爱心的人写信倾诉他的苦难。
雅伯法官是拍西,也是个关在戒毒所的年轻人,不过现在已戒掉了毒,即将获释,正在寻找甜爹【注】与之共度美好时光。拍西已钓到了五条鱼,正慢慢地收网。
乔·罗伊·斯派塞没有文采。他负责协调骗局,帮助编故事,让故事前后连贯,和带邮件来的律师碰头。此外,他还管钱。他拿出另一封信说:“这封,法官阁下,是昆斯写来的。”
比奇和雅伯呆呆地注视着信,一切仿佛都停滞了。从他和里基所通的六封信来看,昆斯是衣阿华州一个小城里富有的银行家。像其余的人一样,他们是通过藏在法律图书室的一份同性恋杂志的私人广告钓到他的。他是第二个猎物,第一个忽然起了疑心,消失得无影无踪。昆斯的照片是在湖畔拍的快照。没穿衬衣,肚子凸出,胳膊上青筋直暴,头发渐秃,五十一岁,家人环绕左右。照片拍得很蹩脚,昆斯挑中它无疑是因为即使有人想试一试,也很难认出他来。
“里基乖乖,你想念念吗?”斯派塞问,把信交给比奇,比奇接过来,看着信封:素白色,没有回信地址,是打印的。
“你看过了吗?”比奇问。
“没有。读吧。”
比奇慢慢拆开信,一张白纸,上面用老式打字机打得满满的,不空行。他清清嗓子,开始读起来:
“亲爱的里基:都办好了。我不相信是我干的,可我的确做成了。我用了公用电话和一张汇票,这样什么一也不会被发现。我想我没留下什么痕迹。你推荐的纽约那家公司不错,非常慎重,帮了大忙。坦率地说,里基,这把我吓坏了。预约一次同性恋的旅行是我做梦也没想过的事。知道吗?这令人兴奋。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们订了一个套间,一千元一夜,我都等不及了。”
比奇停下来,从架在鼻梁中央的老花眼镜上方扫视着两个同伴。他的两个同伴面带微笑,品味着内容。
他读下去:
“我们于二月十日启航。我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主意。我九日到达迈阿密,这样我们就不会有太多的时间会面及介绍自己,让我们在船上的套间里见面吧。我会先到那儿登记,备好冰镇香槟,等着你。是不是很有趣,里基?我们将有三天属于自己的时间。我们可以一直呆在房间里。”
比奇禁不住笑了起来,一边笑,一边厌恶地摇头。
“想到我们的旅行,我多么兴奋啊。我终于决定要发现自己到底是谁,你给了我迈出第一步的勇气。虽然我们还没有见面,里基,可我已对你永远感激不尽。请尽快写信给我并再次确定会面日期。保重,我的里基。爱你的昆斯。”
“我想我要吐了。”斯派塞说。可他只是说说而已,要做的事太多了。
“我们敲他一笔吧。”比奇说。其他人很快赞同。
“敲多少?”雅伯问。
“至少十万。”斯派塞说,“他的家族已有两代人开银行。我们知道他父亲在商界依然活跃,你可以想像,如果他的儿子被逐出家门,他会发疯的。昆斯绝不肯丢掉家族的肥缺,所以不管我们开什么价,他都会付的。这机会千载难逢!”
比奇已经在做记录了。雅伯也一样。斯派塞在小屋里踱来踱去,像悄悄跟踪猎物的狗熊。主意慢慢地形成了,措辞,看法,策略,一切都考虑好了。没多久信就写好了。
比奇读着草稿:
“亲爱的昆斯:收到你一月十四日的信真是太好了。很高兴得知你预订了同性恋航行的船票。听起来不错。可有一个问题,我不能去。有几条理由,一是我还要过几年才会被释放。我在监狱里,不是戒毒所。我也不是同性恋者,根本不是。我有老婆和两个孩子,眼下他们穷得要命,因为我在蹲监狱,不能养活他们。这就是派你用场的地方,昆斯。我要十万美元。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封嘴钱。你寄钱来,我就忘了里基和同性恋航行那档子事,在衣阿华州贝克斯市,没有人会知道这件事。你的太太、孩子、父亲,还有其他有钱的家人,永远也不会知道里基。如果你不寄钱来,我就让你那个小城塞满我们信件的复印件。这叫做敲诈,昆斯,你被逮住了。这是犯罪,很残酷,很卑鄙,但我不在乎。我需要钱,而你正好有钱。”
比奇停下来看看四周,等待着夸奖。
“好极了。”斯派塞说。他已经在想怎么花赃款了。
“真恶心。”雅伯说,“可如果他自杀怎么办?”
“那不太可能。”比奇说。
他们又读了那封信,争论着时间是否选得恰当。他们没提到骗局的非法性,或他们如果被逮住将要受到怎样的惩罚。几个月前,当乔·罗伊·斯派塞说服其他两人和他一起干时,这些话题就不再谈起了。同可能的回报相比,风险是微不足道的。中了圈套的昆斯一家不可能跑去警察局报告受到敲诈。
可他们还没敲诈过谁呢。他们正同大约十二个可能的受害者通信,都是中年人,都犯了同样的错误,给下面这则广告写了回信:白人俊男二十出头觅四五十岁善良稳重之绅士为笔友。
这则用小号字体登载在一本同性恋杂志封底的广告收到了六十封回信。斯派塞的工作是从这堆垃圾中挑选出有钱人作为目标。开头他觉得这事很恶心,后来渐渐产生了兴趣。现在它成了正经事儿,因为他们将从一个完全无辜的人那里敲诈十万块钱。
他们的律师会提取三分之一的利润。这份额并不过分,可依然令人痛苦。他们别无选择。他在这个阴谋中是个关键人物。
他们花了一小时推敲给昆斯的信,然后同意耐心点,第二天再最后定稿。还有封信是个化名胡佛的人写的。这是他的第二封,写给拍西的,四页纸上没完没了地谈论着观察鸟类的事情。雅伯以拍西的身份回信之前不得不研究了一下鸟儿,声称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显然,胡佛极其胆小。他没谈到任何私事,也没提到钱。
三兄弟决定给他多上点绳索。谈谈鸟儿,再把他引到肉体关系这个话题上。如果胡佛不接受暗示,如果他没有透露自己的经济情况,他们就不再理他了。
在监狱管理局内部,特朗博尔被官方称做拘留营。这个称呼是说它周围没围墙,没铁丝网,没了望塔,没有持枪的看守等着抓逃犯。拘留营意味着最低限度的防范,任何犯人,只要他愿意,就可以逃跑。特朗博尔有一千名犯人,可没什么人逃跑。
特朗博尔比绝大多数公立学校都要好。宿舍装有空调,干净的食堂提供一日三餐。还有健身房、台球、纸牌、网拍式墙球、篮球、排球、慢跑跑道可供娱乐。甚至有图书馆和教堂。值日的牧师、顾问、社会工作者一应俱全。探视时间也没有限制。
特朗博尔对被划为低危险类的犯人来说是够好的了,他们中百分之八十是毒品犯。大约四十人抢劫过银行,可并没伤着或吓着谁。剩下的都是白领阶层,他们中有骗术不怎么高明的小骗子,也有像弗劳伊德医生那样的高级骗子。弗劳伊德是外科医生,二十年的时间里他的诊所从老年保健医疗基金中骗取了六百万美元。
特朗博尔不允许暴力存在。也没有威胁。条条框框很多,但管理部门实施起来得心应手。假如你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他们就把你送走,送到中级防范的监狱,那里有铁丝网和粗暴的看守。
特朗博尔的犯人也乐于安分守己,一天一天打发日子,大家相安无事。
在乔·罗伊·斯派塞到来之前,在监狱内从事严重的犯罪活动是闻所未闻的。在倒霉之前,斯派塞听说过安哥拉骗局的故事,它发生在臭名昭著的路易斯安那州监狱。那里的几个犯人完成了敲诈同性恋者的计划。事发前他们从受害者那儿敲诈了七十万美元。
斯派塞来自靠近路易斯安那州边界的乡村,在那里安哥拉骗局尽人皆知。他从没梦想过会照葫芦画瓢,也来这么一手。可一天早晨当他在联邦监狱里醒来时,他决定利用他所能接近的每一个人。
他每天下午一点在跑道上散步,常常独自一人,总是带着一包万宝路香烟。在被关押前他有十年没抽烟,现在一天两包。他散步的目的是想抵消抽烟对肺部的损害。三十四个月中,他已走了一千二百四十二英里,瘦了二十磅,尽管可能不像他所说的那样是锻炼造成的。禁酒才是最大的原因。
三十四个月在散步和抽烟中度过,还有二十一个月的监禁。
偷来的九万赌资实际上藏在他家的后院,离他的房子半英里,靠近工具棚,埋在他老婆不知道的一个自制的混凝土地窖里。她帮他花掉了其余的赃款。总共有十八万,联邦调查人员只找到了其中的一半。他们买了辆凯迪拉克,飞到拉斯韦加斯,坐头等舱离开新奥尔良,到哪儿都乘坐赌场轿车,在豪华套房过夜。
假如他还有什么梦想的话,那么其中之一就是成为职业赌徒,总部设在拉斯韦加斯以外,让各地的赌场闻风丧胆。他玩的是二十一点,尽管输了很多钱,但他依然确信能赢。加勒比海有他从未去过的赌场。亚洲的赌业也日趋红火。他会坐头等舱周游世界,带不带老婆无所谓,住在豪华套房里,要求提供客房服务,让任何二十一点的发牌人惊恐不安,乖乖地给他发牌。
他会从后院取出那九万块钱,加上这次骗来的钱,搬到拉斯韦加斯。带不带老婆无所谓。她过去每三周来一次特朗博尔,可已经有四个月没来了。他常做噩梦,梦见她翻后院的土,寻找埋藏的财宝。他几乎确信她对这笔钱一无所知,可仍疑虑重重。在被送去监狱之前,他有两个夜晚一直在喝酒,他说了些关于那九万块钱的话。他记不起原话了。他试了多次,可怎么也记不起来他告诉了她些什么。
走到一英里处他又点燃一根万宝路。或许她现在有男朋友了。丽塔·斯派塞是个有吸引力的女人,某些部位有点儿肥硕,可九万块钱可以掩盖一切缺陷。如果她和新男友找到并已开始花那笔钱怎么办?乔·罗伊常做的噩梦来自一部蹩脚的电影,丽塔和某个陌生的男子在雨中像疯了一样用铁锹挖着土。为什么会下雨,他也不知道。但总是在夜间,在暴风雨之中,电闪雷鸣,他能看到他们步履艰难地走过后院,每次都离工具棚越来越近。
在一个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