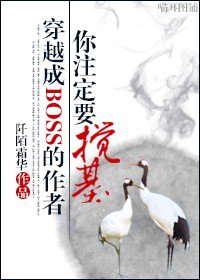所有的 作者:黄蓓佳-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向她的布匹柜台一睹芳容。
我和艾早也去看过一次,我们共同的看法是。
有一点像演《刘三姐》的那个黄婉秋。她好像跟张根本约好了故意穿成一种招摇的“情侣装”:上身是一件白色的真丝双皱短袖衫,下身一条米色的确凉长裤,尤其是头上也戴了一顶草帽,宽边,软顶,帽侧钉着一个用蓝丝带打出来的蝴蝶结。我在青阳城里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洋气的草帽,一时间竟有点呆愣。
张根本似笑非笑地说:“是她让你盯着的吧? ”
我张口结舌,本来就热得通红的脸,那时候一定红得发了烂。
“履女人! ”他低低地咒骂了一句。他嘴边的咬肌紧起来,纠成一个疙瘩,在脸颊处缓慢地滑动,看去让人无端地慌张,觉得接下去会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一个强悍男人的引而不发最让人恐怖。
我抬着头,着迷地看着那个女人,又心慌意乱地看着张根本。汗水从我的头发根里源源不断流出,蜿蜒地爬过额头,有的在眉毛处受阻,滴滴答答地落在下巴上或者地上,有的越过眉毛挂在眼帘,很狼狈,同时也把眼睛渍得生疼。
张根本掏出一块格子图案的男用手绢扔给我:“擦擦! 你看你那副猫样。”
我用他的手绢擦汗。手绢是刚洗过的,有一股好闻的阳光和香皂的气味。
也许是我的狼狈模样让他好笑,他终于哼着鼻子笑起来:“你还侦察我? 你知道不知道我是侦察兵出身? ”他伸出手,在我的额头上试了一试,“呀”了一声:“烫得像火! 你要中暑的! ”
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就哭了起来,有一些伤心,也有一些委屈,还有一些任务没有完成的惶惑。
他抓住我的肩膀,把我的身子掰转过去。
催促说:“回家回家。告诉你妈妈,就说我说的,没屁眼儿的事情少做! ”
说完这话,他转头对女人扬了扬下巴,两个人就一前一后地走了。从后面看,两个人一样的草帽,一样的白色上装和米色下装,身材都是高挑挺拔,连走起路来的起落摆动都一样,真的是郎才女貌的一对。
回家之前,我没有忘记看一眼烟杂店里的挂钟:一点五十六分。就是说,张根本在那个女人的家里耽搁了整整一个午休的时间。
六指老头儿缩在躺椅中看完了一出好戏,幸灾乐祸:“晚上回家,你爸爸要罚跪床踏板了。他之前跪过没有? ”又说:“回去让你妈想开点,是男人都花心,我年轻时也这样。”
我差点儿笑出来,心里想,谁会稀罕长六根指头又是满脸黑麻子的人? 除非她自己的手指头同样多了一根。
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李艳华在门帘后面上马桶,屋子里有一股淡淡的臭味。我进门之后下意识地瞥一眼床前的踏板,思忖着人的膝盖跪上去会是什么感觉? 骨头是不是硌得很疼? 这屋子毕竟是艾家酱园几十年的老屋,房间高而且深,屋檐又阔,阳光轻易照不进窗户,屋里有一股陈年的阴森气,我进门不到两分钟,身上的汗水很快就收干了,汗毛居然爹了开来,凛凛地发凉。
李艳华坐在马桶上,很惬意地出恭,同时隔着一道花布门帘,听我汇报。每次都是这样,我盯梢张根本回来之后,时间、地点、人物,事无巨细,都要描述得详尽而精确。偶尔我出于紧张遗漏了什么,或者嫌哕嗦故意略去细节,李艳华总会聪明地发现,然后一针见血指出漏洞,让我惊惧而羞愧。
“你说他们两个人戴了一样的草帽? ”
“是的。”
“一模一样吗? ”
“不是。一个是宽边,一个是窄边。”
我知道李艳华隔了布帘能看到我的脸,可是我在外面看不见她的。
“烂货! ”她恨恨地往地上啐一口唾沫。我能够想象出她此刻咬牙切齿的模样,她脸上白皙细嫩的皮肤会因为憎恨而皱成碎片。“贴上来的贱东西! 骚到大街上去了。”她的声音恶狠狠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从枪膛里进出来的一样。
我用指甲抠着自己的手心,考虑着要不要把张根本叫我转告的话说出来。后来我决定不说。我已经十二岁了,知道世界上的事情孰轻孰重了。张根本一天到晚难得在家里照面,大多数时候我必须跟李艳华独处,我应该服从她,尊敬她,做她的密探,仆人,甜饼,饵食。我是心甘情愿这样。我这样做了之后,才能在他们两个人之间获得一个自由的转身。
整个暑假中,我一天一天地游荡在青阳城的大街小巷里,在张根本的身前身后,在他那些不停变换着的女人的身前身后。我不知道张根本是不是极度地讨厌我,他当初答应李艳华领养我,现在是不是后悔得肠子发青。他肯定没有想到,把我收纳进门抚养多年之后,我居然成了寄生在他身上的一个尴尬的脓包,一颗随时都会拉响的炸弹,一抹怎么都拂不去的碍眼的尘埃。盯梢任务繁重的这个暑假,最早的一天,我曾经在清晨四点被李艳华摇醒,睡眼惺忪地踏着张根本的露水脚印出了大门。最晚的一天.街边的梧桐树都已经垂下枝叶打起了哈欠,我还像一只可怜的病猫一样蜷在人家檐下,等着张根本从桥下的理发店后门出来。
我无法理解张根本对于女人的喜爱。在我看起来,那些女人大多数不如李艳华,没有她漂亮,没有她会撒娇弄痴,没有她这么好的护士职业,更没有一个宽敞气派的艾家酱园。可是张根本不嫌恶她们。他跟她们在一起的时候,体贴,风趣,轻松,和谐,从骨子里散发出来一种满足快乐。他眯缝着细细的眼睛,仰头大笑,下巴颤动着,喉结像老鼠样地上下窜动,连带着他的整个身子一起一伏,搭上一股风就能够飞起来的感觉。他会凭借自己的权力和关系,全心全意地为她们办事:孩子上学,老公调工作,单位里评先进,房子维修,买几斤计划外红糖,一挂猪油,甚至就是叫个工人往家里拉煤球。他在工作之外有非常多的精力,不把这些精力往女人身上用出去,说不定就会炸翻了他自己。
他并不在意自己的形象。青阳城里,张根本就是这样一个人,有手腕,有本事,大大咧咧,不拘小节,天生有女人缘。他把自己的形象公开化之后,做什么都不会畏首畏尾,相反还故意地往大处、往明处、往极致处靠一靠,弄得一部分群众反而因此对他生出亲切和敬佩,觉得这个人魅力十足,是条汉子,也是青阳城的一个异数。
李艳华一天一天地坐在马桶上,咀嚼和吞咽着这些秽气。她表面精明,实际蠢笨,想疼了脑仁儿也想不出对付张根本的办法。慢慢地,她接受了这个现实:只要张根本不跟她离婚,不把外面的女人带回家里,不把工资收入拿出去花,那就眼不见为净。
“张小晚,”她坐在马桶上对我掏心窝子,“我现在只有你了,老了以后全都要靠你,我把你从五岁养大,将来还要让你在艾家酱园结婚,你可不能没有良心。”
她的声音带着很重的鼻音,呢喃似的,像一个女人刚刚睡醒之后对男人索求的娇嗲。我很奇怪她干吗要对我这么说话,除非她把我当成了张根本。
暑假一开始的时候,艾早就决定了要在这两个月当中学会游泳。
说起来原因非常简单。上个学期中,北方的一个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在青阳县中招走一个女生。这事在县城里引起的轰动,一点儿不亚于不久前林彪的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落。
人们都传说,这女孩子被招过去是要培养当间谍的,那学校就是培养间谍的学校。人们还说,女孩子的长相也就是中等偏上,学习成绩同样不算拔尖,被选中的原因,是她会游泳,拿过地区青少年游泳比赛的冠军。她将来要被培养了当“水鬼”,专门潜入海底,炸敌人的军舰、鱼雷、潜水艇。
“艾晚你想想,当间谍哦! ”艾早把裤子褪到腿根,坐在公共厕所里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两只眼睛亮得像两颗小小的太阳。
大概因为我总是在张根本和李艳华的夹缝中生活的原因吧,我那时候已经变得很有城府,做事喜欢思前想后,不会轻易表态,更不会冲动,盲动。我告诉她说,当间谍肯定要求家庭成分好,这一条她就不够格。再就是,要有强有力的人推荐她,也就是俗话说的“走后门”,这也不行,艾忠义和李素清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有这样的“后门”关系吗? “他呢? 他也不能做到吗? ”艾早盯住我的脸,嘴巴嘟嘟着,鼻尖上闪着一个油光光的亮点。
我明白她指的是谁。在我们家所有的孩子中,张根本唯独对她有一种降贵纡尊的屈从和迁就。可是她凭什么就认为他会在所有的事情上为她效劳? “我不知道。”我老老实实地回答她。
艾早皱着眉头看了我好半天。她大概对我的缺乏激情和不予配合感到失望。
但是艾早不是一个轻易就会被困难击退的人,相反,事情的某种艰巨性会刺激她的斗志,让她显露出平常少见的个性坚定的一面。
那段时间,每次走在街上,艾早都是目光炯炯,捕捉着马路上走过去的每一个穿军装戴领章的人,尤其是那种中年的看上去像大学老师的人,她会猜测他们是不是仍然在青阳城里寻找目标,那所外国语学院还要不要再招收一些学生。她常常激动不已地跟着他们走上很久,梦游一样,身不由己一样。她好像忘了那年她才十二岁,连中学校门还没有跨进去。
艾早决定要学会游泳。技能就是资本,艾早小小年纪已经悟到了真理。
要学游泳,赵三虎现成的就是老师。胡妈家住在闸桥下不远,三虎从小在水边长大,会走路就会在水里扑腾。三虎拍着胸脯向艾早担保,一个星期就能把她教会。当然他也保证了同时教会我。
三虎把他家里刚刚箍好的一只扁木盆顶在头上,带我们去城外的护城河。他很内行地跟我们说,闸桥下的河水太脏,水底下淤泥多,脚一踩下去,污泥翻出来,水又臭又浑。护城河比较好,水底下是沙土,怎么扑腾都没事。
去到河边,我们才发现在这条河里扑腾的人很多,大部分是放暑假的孩子,有一些我们还认识。大家穿的都是家常的短裤,男孩子光裸着晒得油亮的上身,女孩子有一件花布做的背心。河中漂浮的救生用具也是各式各样,比较高级的是汽车轮胎,次一些的是晒干的大葫芦,然后还有木盆,木板。还有几个孩子把家里的门板卸下扛过来了,一块门板两边簇拥了十来颗黑黑的脑袋,很有气势。每年护城河里游泳都会淹死人,但是每年夏天河里都是孩子的天堂。家长们管不住,也没有特别要管的意思。
哪家没有三五个孩子啊,总不能有三五双眼睛‘整天盯着吧? 三虎的确游得很溜,他是自学成才,用的是“狗爬式”,入水之后始终抬着头,两只胳膊一个劲地扒拉着水,两只脚把水花打得飞溅。
动静很大,气势逼人。他最得意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能够游到对岸,再转个身子返回,脚踩着河底站起来时,头发还是于的。
三虎带过来的木盆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和艾早把鞋子脱在岸上,一人抓着木盆的一边试探下水。三虎在木盆的前方,身子倒退着往前游动,一边扯着木盆往前。木盆渐漂渐远,慢慢地离开河岸,往河心逼近。河边的浅水被太阳暴晒一天,微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