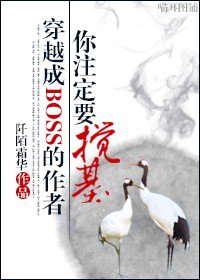所有的 作者:黄蓓佳-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上车以后我才猛醒,这辆车的名字叫“陆虎”。我在艾飞收集的汽车图片中见过这款车型。艾飞说,这是他喜欢的车。艾飞喜欢的车都是价格昂贵、外形超酷的车。难怪刚才有那么多人对这辆车看了又看。
开陆虎车的小伙子。
我再一次感觉不安。在我的生活中,还从来没有跟这种时尚阶层打交道的经验。贾铭开的车是“帕萨特”。陈清风在加拿大开一辆“日产丰田”。张根本活着时,司机为他开车,是比较老款的“奔驰”。开陆虎越野车的人是怎样的生活状态,我完全不知情。
“你去哪儿? ”拐上了广州往深圳的建成多年已经破旧的高速公路之后,李东转头问我。
我跟艾早的律师约在事务所见面,所以我告诉李东,在罗湖火车站附近。我问他那附近有什么酒店可住? 我强调说,不要太贵。
他打开车上的一个电子导航系统,一边开着车,一边拿遥控器熟练地搜索。从我坐的副驾驶座上,只看见一块一块红红绿绿的市区地图在半块砖头大小的屏幕上掠过。
“五月花酒店,行吗? ”他征询我的意见。
听上去不是太豪华。跟着我想起来,“五月花”应该是一艘船的名字。十七世纪初,一群逃亡状态中的英国人驾着这艘三桅帆船漂过大西洋,落脚在新大陆,制定了著名的“五月花公约”,而后开始拓荒者的充满传奇和艰辛的生活。在他们的后人手中,终于诞生出一个了不起的美利坚合众国。
“没错啊! ”李东利索地换挡,右脚点着油门,在车海人河中把他的“陆虎”开得左右逢源。“开那个五月花酒店的老板,听说是从宁夏过来的人,西部移民。从宁夏到深圳,不必横渡大西洋,可也得过黄河,过长江,挺了不起。”
我望着他优雅地搭在方向盘上的那双手,问他:“你是移民吗? 或者你父母? ”
他不直接回答我:“走在深圳街上的人,十个人当中起码有九个是移民。”
我忽然又想起艾早。艾早也是这个城市的移民,还有张根本。当年他们是随着大潮游进这个欲望之海的两尾鱼,经过惨烈的生存搏斗,经过大鱼吞吃小鱼的优胜劣败,他们幸运地活了下来,长成为某一个级别的“鱼王”。可是为了什么,曾经的王后要起杀戮之心? 张根本,我从前的养父,一个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的商业国王,他对于艾早还会有什么样的威胁和伤害呢? 我不急着去酒店了,我想先赶到律师事务所,弄清这个巨大而阴森的秘密。我觉得我已经被一种无形之影压迫得透不过气。
李东什么也没有说,把陆虎车开得更快更急。他坐在我的身边,离我这么近,一定能够感觉到我的心急如焚。他感觉到了却没有主动提问,只是把车速提高到一个与“焦急”适配的程度,这是一种修养和文明。
电梯口拥满了人。因为不在上下班的高峰时间,四部电梯只开了两部,其中一部还只停十五层以下。人们都急着办事,免不了骂骂咧咧,还说要投诉这幢大楼的物业管理会。穿制服的保安无动于衷地站在一边,大概他已经看惯了每天、每时这样的混乱。他没必要费口舌过去安慰,调解,这跟他的饭碗没有关系。他个子矮小,皮肤黝黑,眉毛上有一个破相,脸颊上还带着长年累月在田间劳作留下的晒痕。也许还要过个十年八年,这种带有身份标志的痕迹才会完全地从他面容上消失,使他成为一个底气十足的深圳人。
一个穿白色上衣和玫红色裤子的女人,大概要上到高层,可是稀里糊涂挤进了只达十五层的电梯,片刻之后一脸愤怒地随着电梯又下到一层。保安忍不住噗哧地笑了一下。那女人有点恼羞成怒,张口就骂了一句广东粗话。保安听懂了,他面红耳赤。我看见他的一只手在裤袋旁边动了一动。如果是在工作场所之外的任何地方,他可能就会豹子一样扑上去了。可是在这儿,他只能选择忍耐。他也用他的家乡话嘀咕了一句什么,声音却很小,完全是自己给自己解气。
高层电梯终于来了,穿玫红裤子的女人顾不上再吵下去,一个箭步插到我的前面。她身上有一股浓得发腻的香水味,也许是摩丝或者睹喱水的味。她的头发高高盘在头顶,用太多的化学材料固定得僵直梆硬,仿佛脑袋上顶着一个黑糊糊的鸟窝。这样的发型,十年前我到深圳的时候,见得很多,没有想到十年之后在这儿还有市场。深圳城市的变化很大,可是深圳本土人的生活观念并不想跟城市发展同步,他们有自己的习惯和喜好。
律师事务所在二十四层。大楼进门处的一面墙上钉满了各间公司、中心、办事处、事务所的锃亮铜牌,其中就有一块写着“二十四层A 座:宏伟律师事务所”。
从电梯门出来,拐一个弯就是A 座。透过一排玻璃门,事务所的标牌用黑色的隶字铺排在迎门墙壁上。推门进去,室内空调打得很低,冷不丁地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一个很年轻的女孩,长着讨人喜欢的大眼睛和小虎牙,笑微微地从桌子后面站起来,问我有没有预约。
我说了“纪宏林”这个名字。女孩点点头,说一声:“请跟我来。”
我们走过了一个一个用玻璃钢和铝合金制品隔开的空间。开敞的空间里,每张桌上都有一个白色塑料的姓名牌。名牌后面的主人都很年轻,有人在接听电话,有人在电脑上起草文件,还有人用裁纸刀和订书机装订材料。他们无一例外地紧张,严肃,脸上有一种与年龄不太相称的老成,甚至是漠然。我从他们身边走过去时,他们知道不是自己的客户,眼皮都不抬,完全的与己无关。
纪宏林的姓名牌钉在一个房间门上。沿着走廊大概有五六个这样的房间,彼此紧挨,亲密共存。我猜这些房间里的律师应该具有更高级的身份,是事务所的合伙人。这些房门全都紧闭,门内悄无声息,气氛不无神秘。偶尔外面的某个桌上有电话铃响起,坐在桌后的年轻人接听之后,立刻起身,拎起手边早已准备好的一份文件,小跑着走近其中一扇门,抬指轻轻一敲,而后转动门把手,恭身闪进,回手习惯地将门又关上。我很难猜想门内律师手里代理着一个何种性质的案件,是替一个被玷污的灵魂申冤讨债,还是筹谋着将一个原本清白的好人打入地狱? 无论如何,每一扇紧闭的门内都是一个小小的战场,文件和文件、档案和档案时时刻刻都在厮杀搏斗,硝烟弥漫中打出钞票的腥甜。
纪宏林是一个小个儿、精瘦、剪着一个利索的平头的中年人,一件浅灰色衬衫扣得严严实实,左手的无名指上戴一枚圈形婚戒。他面前的桌子上,除了电脑之外,电话机,传真机,扫描仪,手机,笔形录音机,超薄相机,U 盘……全部高科技的电子设备一应俱全,闪出金属特有的幽秘之光。拍纸簿上搁着一支拧开套子的黑色钢笔,刚刚他就是用这支笔在签署一份文件。我已经好久没见人用过这样老派的书写工具了,一瞬间又觉得恍惚起来,仿佛时间沿着这支笔杆倒退了二十年。
最现代的和最传统的,在这间小小的律师办公室彼此相安,和谐共存。
他起身,客气地跟我握了手。目光落在我身上的时候,他眼睛里曾经流出过一丝诧异。
或者说,是一种近似于恐惧的惊讶。他心里想的肯定是,艾早明明已经投案自首,怎么又会在他的办公室里出现? 很多人第一次见到我们姐妹之后,心里都会惊叹我们的相像。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几乎一模一样,而后渐渐出现差异,二十岁的时候差异明显,甚至高矮胖瘦都有区别,没有人相信我们是一胞双胎。到了现在,容貌却又有重合的趋向,眉眼神情,声音腔调,步态动作,惊人的相似,活像由一个克隆了另外一个。
纪宏林伸手向墙边的沙发:“你请坐。我们早晨已经通过了电话,不算陌生。”
我迫不及待提出要求:“我姐姐在哪儿? 我想见她。”
他苦笑一下:“对不起,这不可能。她现在是杀人嫌犯,就连律师见面都要事先申请。”
“你申请了吗? ”
“我提出保释。四十八小时会有答复。”
“这就是说,我要一分一秒地等完四十八个小时? ”
“其实你不需要等。以我的经验,像艾早这样的情况,保释要求基本不可能答应。我提出要求,不过是要走完一个法律程序,以免留下遗憾,也是给家属一个交代。”
他嘴里的每句话都像一颗子弹,简洁,冷峻,置人于死地。
“为什么? ”我问他,“艾早为什么要这样? 他们已经离婚十年了! ”
他摇了摇头。“他人是地狱。”他说,“黑暗而幽深的地狱。我们这些置身事外的人,无法窥见一个人完整的内心。”
“张根本的太太呢? 她在场吗? ”我想说的是,张根本被杀时,他年轻的老婆是否亲眼见到? 她做出了什么反应? 纪宏林告诉我:“半年之前,张太太办妥了投资移民,带着小孩子去了澳大利亚。”
我张大嘴,惊愕不止。这事张根本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艾早也没有提起。
纪宏林又说:“其实我已经没有义务介入这个案件,因为张总的公司不久之前已经清盘,作为张总公司的律师,我跟他之间同时结清了一切。如果你需要我继续服务,你要签署一份家属委托书,另外,我必须按小时收费。你同意吗? ”他冷静地看着我。
我还没有从刚才的惊愕中走出来。我此刻的模样,一定像个傻瓜,浑浑噩噩什么都不知情的傻瓜。
我问他:“为什么清盘? 公司不是一直做得很好? ”
纪宏林摊开手:“是张总的决定,我不清楚原因。张总把公司股份卖给了一家香港商业集团。谈判时间很短,几乎没有什么讨价还价。”
“一定有原因。”我说。
他沉吟一下:“也许张总倦了,不想再做下去了。”
说到这里,他打开抽屉,拿出一张银行卡,放在桌上,用中指推到我的面前:“艾早委托我转交你这张银行卡。她说是张总卖掉公司后分给你的一笔钱。你是张总的养女? ”他忽然问了我这句话。
我迷迷瞪瞪地看着他,完全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拿出一些文件,一张一张地递给我:“这是银行卡的签收单。你把卡号写在这儿。这是律师委托书。你需要委托我吗? ”
我需要委托他。我在这儿只有他这一个指靠得上的人。
我拿起他递给我的大号钢笔,在文件上签了字。
“纪律师,请你想办法尽快见到我姐姐。求你一定要帮她! ”我的声音里有一点颤抖。
“我会尽力。这是我的责任。”他很严肃地回答我。
可是他没有给我吃定心丸,也没有给我开任何空头支票。
我们握了手,然后我从他的办公室里走出去。猛地一下子,我心里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空落,五脏六腑都抽走了,腹内空空,走路飘忽,平衡尽失。
法律是一堵冰冷的墙壁,我撞上之后才稍稍清醒。原来我此行见不到艾早,这事比我想象的更加严峻。
关键就是,艾早有了一个明确的身份定位:杀人嫌犯。
1994年春节,我第一次到深圳。
艾早和张根本刚刚结束了他们在海南的资本原始积累期,转战深圳,注册了一家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