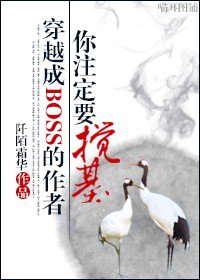所有的 作者:黄蓓佳-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94年春节,我第一次到深圳。
艾早和张根本刚刚结束了他们在海南的资本原始积累期,转战深圳,注册了一家公司,购买了高档生活区内的商品住房,雄心勃勃着手筹建一个张姓商业王国。
艾早给我打来电话说,房子装修好了,专门给你留了一个客房,来住几天吧。她还说,知道你很快要去美国进修,你要是来,我给你好好买几身衣服,深圳的衣服多得让你挑花眼,你关在南京的校园里,想象不出华服美鞋可以怎样地重塑一种人生。
我爸爸妈妈催促我接受邀请。艾早离开青阳整整五年,没有回过家。爸爸妈妈嘴里不说什么,心里一直惦记她,不知道她跟着张根本变成了什么样。1989年张根本变卖了我们家的房产,带着全部卖房款携艾早登上长途客车时,爸爸妈妈发誓跟他们断绝关系。老两口都是好面子的人,说出去的话没有理由再收回,所以我成了他们跟艾早之间的联络员。
艾早开着新买的美国车去机场接我。车是他们从海南买回来的,海关走私货,比市场便宜近一半。几年之后走私车像鸟儿一样落满了那个热带海岛,通过海口和湛江之间的轮渡源源不断运往大陆,终于酿成震惊全国的大案。
那时候张根本已经把美国车换成了正经渠道进口的奔驰车,开始享受财富带给他的极速飞升。
艾早的气色很好,看上去似乎比我年轻,大概如她所说,是用了一种瑞士产的生物化妆品的缘故。她穿着一套藏青色的裙装,上衣短而窄,领口一直翻开到腰线,饱满的胸部有呼之欲出的危险。沿衣边用仿水晶的小钉子镶出一道亮闪闪的线条,使朴素沉稳的藏青色立刻改了面孔,端庄中透出华贵,华贵中又有一点点俏皮。她脚上的鞋,手里的包,都是跟衣装精心搭配出来的,相补相衬,说不出来的和谐。我在见她的第一眼,恍然明白了什么叫一个人的“着装品位”。
当时我在牛仔裤里面还穿着一条厚毛线裤,脚下是咖啡色腈纶绒的保暖鞋,一件紫红色的腈纶轧花棉袄已经脱了,鼓囊囊地抱在肘弯里,跟身边很多走出机场的北方旅客一样,既老土,又狼狈。
艾早先是正面端详我,又抓住我的肩,将我反身过去,从背后打量我。她一句嘲讽我的话也没有说,先把车开到国贸中心,给我换装。
在琳琅满目的品牌店里逛了一圈之后,她帮我挑了一条咖啡色的针织背心裙,里面衬一件薄薄的奶白色羊毛衫。她还给我配了一条披肩,一个米色手袋,一双褐色皮鞋。我们在商场的试衣间里换上新衣服,然后她把我脱下的冬装卷成一大团,塞进两个带拎手的购物袋,轻轻松松地出门。她是用商场消费卡付的账,我甚至没有看清一共花了多少钱。
出了商场门,艾早用她的“大哥大”电话跟张根本联系。张根本已经在楼下的粤菜餐厅里给我们订了位。张根本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跟你姐姐越来越像了。”
可是张根本的模样跟几年前有了不少变化,他开始发福,一件肩头和肘弯处镶着咖啡色软皮的毛衣绷在肚子上,笑起来的时候,鼻尖上沁出闪亮的油脂。从前总觉得他的脑袋有点小,还有点尖,透着机巧和精明,现在因为胖,脑袋上长了肉,不觉得小了,可是前额却又秃了顶,额头无端地宽出来,成了大片的跑马地。
张根本摸摸他的头,问我说:“小晚,你是不是看我老了? ”
艾早不客气地回答他:“你怎么会不老? 我和艾晚都已经三十多岁了。”
张根本“啊”地一声,像是刚刚意识到我的长大。而后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我:“你怎么还不结婚呢? 你要是结了婚,我也可以抱个外孙子啊! ”
我偷看艾早一眼,心里无端地跳,忍不住地慌张。
艾早没有发觉我的异常。她笑着在我面前放下一杯新鲜芒果汁:“艾晚你别理他,他是自己想儿子想疯了。”
那天的晚饭让我大开眼界,因为张根本居然点了一只两斤多重的澳洲大龙虾。穿白衬衣黑背心的俊美侍者将龙虾囚在一只桶里,送上来给张根本过目的时候,龙虾的两只巨钳还在绝望地舞动。在这之前,我仅仅是在我们教研室主任家里见过一个龙虾标本。他去海南岛旅游,从一个旅游品商店买到了那只张牙舞爪的大虾王,孩子样的如获至宝,千里迢迢捧到了南京,掉下来的一只钳子还是后来用胶水粘上去的。张根本点的这只龙虾,比我们主任挂在墙上的那只更加威武神气,我差点儿提出来别吃它了,由我带回家做标本。我甚至还想,我可以把龙虾标本送往青阳,让我的父母见识一下张根本和艾早的生活状态。
可是我终究没有开口。那只虾,生吃、盐灼、须尾烧成咸泡饭,就着啤酒和果汁,一点一点进了我们的胃肠。
那晚我们还吃了青蟹,吃了鲜贝,吃了清蒸的石斑鱼。张根本很会吃鱼,他拿一根筷子竖着往鱼背上一戳,就知道这条鱼欠了火候还是蒸得老了。几年当中,他一定是吃了无数条清蒸海鱼,才历练出这样的手感。
我实在不知道他对我的款待为何如此隆重。他是我的养父,他供我念完小学、中学、大学,又在南京就业安家,即便他对我摆出为父的尊严,有一点爱理不理的矜持,那也是该着的,我不会有丝毫怨言。
席间我几次要说到我的父母,都被张根本岔过去了。他不想谈论他们。从前他就对我父母不屑一顾,现在依然如此。他在骨子里瞧不起知识分子,尤其是那种有点迂,有点倔,又有点自以为是的人。
走出国贸中心,上了艾早的车,我才想起来,从见面到现在,我还没有喊过他一声“爸”。
当然,当着艾早的面,这称呼会使大家难堪,所以我不喊是对的。我问艾早,他怎么不一块儿回家? 艾早说,这会儿就回家了? 还有一场麻将局等着他呢。我说他什么时候爱上搓麻了,他的手气好吗? “他不能手气好。”艾早笑了笑,“他去了就是要输钱的。”
第二天一早,艾早接到一个电话。她在电话里跟对方聊了一会儿,好像还谈到了付钱不付钱的事。放下电话后,她迟疑地问我,愿意不愿意跟她走一趟。
“谈生意吗? ”
“不,去抱个孩子回来。”
我目瞪口呆。这简直太有宿命意味了。张根本二十五岁的时候抱养了我,到他五十多岁的时候又想再一次抱养一个孩子。
“男孩女孩? ”我问艾早。
“男孩。他只要男孩。”
张根本从青阳我父母家中带走艾早时,就知道她这辈子不能生育。这事儿我父母甚至不知道,但是张根本知道。当年就是他驾驶着带车斗的警用摩托,把她从乡下卫生院的治疗室里抱出来,送往邻近的地区大医院,救活她一条命。张根本的那辆摩托,被艾早身上流出来的血弄得触目惊心,他找个修车铺又冲又洗,还换掉了车斗里的海绵坐垫,才算是掩踪灭迹。
所以,1989年张根本跟艾早结婚,思想上有了这一辈子绝后的准备。
但是现在不行了,张根本的事业做大了,他比从前的任何时候都更盼望着有个儿子。有儿子才能接班,儿子才能让他享受到拼搏成功的乐趣。
艾早来到深圳之后,要做的事情之一,是频繁地为张根本寻找一个养子。
最早是张根本的司机从火车站附近捡了一个。捡来时发现是个男婴,张根本曾经欣喜若狂,以为是上天特意对他的眷顾,刚瞌睡就送来了枕头。回家养了几天,觉得不对,男孩儿尿频,从早到晚尿布上没有干爽的时候,走近小床就闻见一股尿味。仔细扒开孩子的屁股} 看,才看见小鸡鸡的后面还隐藏着另外一副完整的女性器官,有阴道,也有尿道。尿水是从后面的尿道里源源不断流出来的。张根本感觉很晦气,叫他的司机偷偷把那孩子又送回了火车站。
第二个孩子,张根本花了一万块钱、两条“红塔山”香烟,才从人贩子手里买了过来。买卖人口是重罪,张根本这么做可算冒了大险。
孩子到手时小脸发紫,哭都哭不出声,人贩子信誓旦旦说没事,从贵州过来一路辛苦,把孩子熬的,养一养就会活蹦乱跳。结果养了不到三天,小家伙一命呜呼。原来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
两次下来,张根本很受打击。可是他并不死心。这个人做事向来不屈不挠。他把任务交代给了艾早。他说艾早,这世上没有人比你更理解我,没有人比你更相信我,你如果帮我办成了这事,将来公司财产一半是你的,一半是这孩子和艾晚的,如何? 艾早回答他,别跟我提财产,我这个人不贪财。
我们这回要去的是深圳老街上的一个私人诊所。有个打工的女孩不幸怀了孕,在诊所里偷偷生下孩子,自己没法留,要送给一个好人家养。
艾早手里捏着一张记有门牌号码的纸条,领着我在东门一带走街串巷。艾早对老街地形并不熟,又不敢胡乱打听人,弄得我们两个鬼鬼祟祟活像做特务。那时候老街上房屋破旧,店铺一个挨着一个拥挤杂乱。卖服装的店面算是干净,但是高高低低的衣架一直挂到马路边上,弄得行人只好从那些牛仔裤老婆衫的空当里侧身而过。卖西洋参、当归、黄芪、益母草以及干贝、参鲍、鱼翅的店铺把他们的货品用扁扁的笸箩一样样重重叠叠地陈列出来,活像一个人当街袒露了自己的五脏六腑,浓烈的腥鲜气味熏人作呕。卖头饰、玻璃珠串、镀金项链和塑料电子表的店铺一律袖珍得可爱,如果有两个人同时进门挑货,彼此必须达到一个默契,侧身共处,才能把自己的身体安置下来。
所有这些店铺的老板都是深圳本地人。上午的生意不那么忙碌,他们有时间趿拉着塑料拖鞋,在狭窄的街巷里东家西家地串,把铿锵的广东话说出一股恶狠狠的腔调,听上去好像彼此在吵架。他们都长着一张轮廓分明的黝黑面孔,男的穿一件金利来或者是港产“鳄鱼”的无领套衫,下面的休闲裤松垮垮地系在肚皮下,显得闲适而自在。女的穿色彩夸张的针织套装,脖颈和手腕上戴着光灿灿的金饰。很多人的嘴里还镶着金牙,说话的时候,如果迎着光,嘴巴里就会光彩夺目,整张面孔都会因此而生动和灿烂。
“窦氏妇科”的招牌是一块临时挂到门外墙壁上的木板,漆成棕色的底板上写着工工整整的宋体黑字,倒也有几分庄严。诊所的门关着,有人进去,必须敲门,里面的护士把防盗铁门拉开一道缝隙,问明来意,才开门迎客。挺神秘。但是又让人心生戒备,总觉得黑糊糊的屋子里似乎隐藏着罪恶,时时刻刻都有阴谋存在,毒蘑菇一样在角落里滋生,而后长大和惊爆。
诊所的医生是男性,小胡子,鼻梁上架一副半框眼镜,看人时有点不屑一顾,好像我和艾早不值得他亲自接待。他把我们扔给了他的助手,一个头发烫成鸡窝状、皮肤很粗、长得人高马大的北方女人。
“那啥,你俩先看看孩子。”她刚洗了手,在污渍斑斑的白大褂上飞快地擦着,转过身,一撩帘子去了里屋。
里屋传出嘀嘀咕咕的说话声,听上去仿佛是北方女人跟医生商量着什么。我和艾早一言不发地等在外屋,一边很无聊地看着墙上的挂图。挂图的内容全部与怀孕和生产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