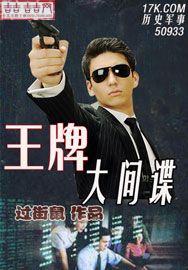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被捕,雷希曼叛变投敌。杰林只好不动,嘴上仿佛贴了封条。
杰林打的第六次败仗,也是相当惨痛的。温策尔“老师”越狱了。
德国人一共搞到了六座发报台,但是不了解每一台的作用。1942年秋天,他们在苏联空降情报员那里破获一部电台。这是由柏林小组使用的,也就成了假“乐队”手里的头一部假电台。艾弗雷莫夫投敌以后,他的电台大发假情报,极受敌人欣赏。另外还有塞赛的电台,温德林克在荷兰的电台。在法国则有肯特的发报站:铁塔一号和铁塔二号。德国人两部都用,总称三月铁塔。然而,在这个假“乐队”里始终缺少温策尔的那架发报台。
温策尔一被捕,立即关进布林敦克炮台,受了刑讯。到了11月,别动队觉得不对头。莫斯科老听不见这位独奏家的演奏,难免生出疑心。至于派个别动队员来代替温策尔,那也是不在考虑之列的。因为“老师”是发报高手,有他特殊的艺术风格,情报中心早已耳熟能详。所以,到了11月,温策尔答应“合作”,德国人听了确实十分满意。
尽管温策尔受着严密监视,他毕竟在头一次发报的时候便发出了告警的暗号。情报中心就这样获悉,今后演奏的乐章都出自敌人之手。
温策尔还跟德国人“合作”撰写并发出两个报告,名叫“日尔曼报告”。日尔曼便是温策尔的别号。这两个报告的内容是我们从苏联方面得知的。第一封电报说:“局长收。急件。与大首长的通常联系已被监视。请指示方式与大首长会晤。我认为此举十分重要。日尔曼。”
第二封电报说:“局长收。火急。从德方获悉,密码已破。会见大首长事仍未奉复。本人与局长联系畅达,似无监视。今后如何与情报中心联系,盼速复。日尔曼。”
这两个电报决刁;再让情报中心怀有任何疑虑。因为我们从来不用“大首长”这个称呼。温策尔逐渐取得别动队的信任,便在比京震旦街一间屋子里安装了电台。1943年1 月初,监守他的人背朝着他生炉子。他乘机把监守打昏,反锁在屋子里,自己从此远走高飞。
对杰林来说,真是飞灾横祸。从1942年7 月以来,比国“乐队”发生的一切情况,都有可能由温策尔报告情报中心。事实正是如此。温策尔逃到荷兰,利用一架没被发现的电台,向情报中心局发电,报告了上述—切情况。
话虽如此,别动队自从破获阿特雷巴德街的案子以来,收获却也不可低估:在五个国家,破获六个电台,向情报中心发出几十份假情报。从复电口气来看,局长仍然毫无觉察。
不过,杰林却在几星期内接连打了六个大败仗,情报中心的指令得不到执行。肯定有什么地方堵住了。他在沙滩上建筑的大厦总有一天要垮台。
看来,别动队队长手里,只剩下了一张王牌,那就是争取“大首长”合作,通过法共渠道,稳住情报中心。杰林冒的风险固然不小,但是舍此别无他法嘛。
12月底,我又跟杰林和他的助手维里,伯格会谈。谈活的气氛变了。我等待的时机已经来到。
第十七章祸不单行
我紧锣密鼓地对付杰林,但并没有忘记,我们还有几位同志没有落网。他们也要加紧对付别动队的进逼。我担心的主要是格罗斯沃格尔和卡茨。其实,我并没有理由特别为他们担心。他们既然这一次没有落网,想必已经有了隐身之地。
对卡茨来说,更不用操心。卡茨本来就在安东尼郊区有一处很可靠的藏身之地。再说,我们早就商妥,他得离开巴黎,前去马赛静候几个月。
谁知杰林的助手伯格来向我报了噩耗:“你知道么? 你们那位卡茨被捕了。”
“是吗? 什么时候呀? ”
“约莫有三个星期了。”
原来卡茨也落了网。我到后来才明白为什么卡茨也过不了关。可是为他采取的安全措施可以说是应有尽有的了。
卡茨眼见我被捕,心里没了准星,便用几天时间,准备开路。正好他的妻子塞茜尔在11月19日生了孩子。他要把母子安排妥帖才能动身。他的大儿子让·克劳德已经送去比叶隆堡他姐姐家。
我在1973年离开波兰以后,才由塞茜尔口里获悉,194Z年11月28日,她丈夫和格罗斯沃格尔一道到妇产医院去看她。他们俩都已经知道我被捕,愁得不知怎么好。12月1 日,卡茨又到医院去看她,准备第二天把她母子二人带走。可是再没有什么第二天了。就在当天,卡茨在巴黎逗留过晚,碰上了宵禁,又不愿意冒险回安东尼,他便到一位女友艾尔里希家里去借宿。艾尔里希的丈夫是犹太人,当小学教员,从前在西班牙参加过国际纵队。
自从战争一开始,他家便成了通信联络站。雷希曼就是在那/L 跟卡茨碰头的。那还是1942年年初。雷希曼被捕,做了招供,盖世太保便把这所房子监视起来。其实,我早就下令不再利用这个去处,而卡茨却不管这些,心想几个小时出不了事,明天一早就走。盖世太保的监守人员通知了巴黎别动队队长雷塞,派人逮捕了卡茨和艾尔里希。我跟杰林说,艾尔里希并没有参加“红色乐队”。我们的活动,她全不接头。可是,她后来还是被送进了集中营,并且死在集中营里。
最后轮到格罗斯沃格尔,他也给别动队逮起来了。他们之所以能够找到他,靠的是极端无耻的讹诈手段。
天下也真有凑巧的事情;格罗斯沃格尔的妻子雅纳·贝桑也在生孩子。我在牢里,自然不了解这个情况,而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这却是关系重大的事情。所以我在那时候并不怎样担心,反正一切都已经准备好,让他暂时去瑞士。贝桑不知道情况如此之严重,不肯加紧隐蔽。结果,别动队于11月26日在比京郊区一所公寓里找到了她。他们便使用了他们惯用的手法,叫她写信约会她的丈夫。如果她不肯写信,便要当她的面把孩子掐死。她丈夫觉得这里面有文章,但是按捺不住最后作别的热望,仍然如期赴约,于12月16日自投罗网。
事前四天,伯格以满不在乎的口气对我说。
“今天,我们要去逮捕罗宾逊啦。”
伯格说话,一向比较随便,他居然把别动队的行动汁划都告诉了我。这种半真不假的好感,后来却帮了我的大忙。
伯格说:“我们发现他已经有好几个月,并且决定在他赴约的时候逮住他。雷塞为此组织了一次毫不含糊的军事行动。几十名别动队员分布包围现场,各人手里都有犯人的照片,按图索骥,万无一失。我可以预先告诉你,雷塞打算叫你一道去,想看看你的反应。但是他不能让你出面。你一出面, ‘大赌博’不就全垮了? 你若是不肯去,他就可以逢人便讲,你不肯合作。”我当即回答他说:“好吧,如果没有理解错,雷塞也想摸摸我的底,给我设了个圈套……”
“你爱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好了。”
行呀!反正我已经心中有数。中午时分,我被带到雷塞那儿。他又把伯格的话说了一遍。
他说: “奥托,我们今天去逮捕罗宾逊。”
老是这么一套,反正功劳都归自己,同伙没份儿。
“你搞错啦,雷塞,这个人只会令人讨厌,他什么山不知道。”
雷塞并不相信我的话,只说:“也有可能。不过,如果你不反对的活,他到底有没有用场,还是让我们自己去掂分量吧。反正你得陪我们走一趟。”
“悉听尊便。”
我把话说得那么样轻巧随便,雷塞一下子诧异得好象订在椅子上一动也动不了。不管怎样,伯格的确不曾骗我。 我乘车前往现场,途中心里盘算自己该采取什么态度。
结论是,唯一有助于同志的办法,不外是设法让他发现我在场。事情是这样,假如德国人把我上了手铐,在现场露面,那就是说“大赌博”已经寿终正寝。因为,负责格罗斯沃格尔安全的小组组员,必然会看见我,一看见我就知道我已经被捕。可是,我的车离现场二百来米就停下了。我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同志被捕。
自从8 月里,施奈德在比国被捕,盖世太保便发现了罗宾逊的踪迹。他的前妻是柏林小组成员,和她已经参军的儿子一起被捕。为什么当时盖世太保却没有立刻动手呢? 理由是,他们以为格罗斯沃格尔还指挥着第三国际的一个重要组织。在这个组织里面还有两位重要人物。一位是第三国际从前的组织部书记德劳茨,一位是德共前领导人明曾堡‘。
这个神通广大的秘密组织,其实全是缪勒他们脑袋里的、空中楼阁,全是他们活见鬼。那时节,德劳茨已经开除出党,明曾堡则在1937年也已经由德共开除出党,同时也开除出了第三国际。1940年,达拉第政府把他关进了古尔斯地方的外侨集中营。就是在那儿,贝利亚手下的两个特务,奉命在集中营里结果了他的性命。这两个特务劝他一道越狱。那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喜事? 他答应了。结果,离集中营二百来米,人们发现他吊死后的尸首。
德国人的意图是要抓住这个幽灵组织的全班人马。因此,他们才监视罗宾逊,暂时不动他。这样才好搞一次大场面的审讯案,由格罗斯沃格尔担任主角。目的是,让“新欧洲”各国人民耳闻目睹, “国际布尔什维克”到底是什么玩意几1 盖世太保在u 月找到罗宾逊的踪迹以后,没有再从他身上找出任何线索,于是决定加以逮捕。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11月21日,在西梅克斯公司破获以后两天。我把本组情况告诉了他,彼此约定中断一切联系。就在这一次约会上,他已经知道施奈德被捕,表示十分担忧。他还不知道,他在帕西的隐蔽所,已经在盖世太保监视之下。
至于马克西莫维奇呢,他也早已被发觉了。他和霍夫曼·晓尔茨小姐订婚的时候,盖世太保照例到警察厅去查外侨的档案。晓尔茨小姐乃是奥托·阿贝茨的秘书。等到我们知道这件事,已经来不及了。我们本来想托我们在警察厅里的联系人,把有关的档案藏起来,可是盖世太保已经先下手。
他们得知马克西莫维奇一向同情苏联,当即撤销了他进出马哲斯蒂克大旅馆的通行证。这样一来,他的嫌疑已经不轻,接着沃克博士又在柏林译出了一批密电。密电的来源一望可知,于是嫌疑成了确证。他的未婚妻到德国探亲回来,告诉我们德国城市遭受破坏的情况。我们把消息报告了莫斯科。
盖世太保把材料对证一下,发现来源在晓尔茨小姐。
从10月起,马克西莫维奇已经受人跟踪。别动队队员毫不躲躲闪闪,他们径直去到比叶隆宫堡,一五一十告诉安娜,说是已经收集到一切证据,证明她自己和她的兄弟参加了一个间谍组织,反对第三帝国。他们对安娜说:“你可以帮我们一把忙,只消你帮我们约你的领导会见一位德国人,也不妨约在非占领区,我们可以完全保证你不受连累,因为这件事政治意义很大。”
安娜马上把杰林的话通知了我。我当时自然只能够把这件事当做一桩普通的绑票手段。其实,那时候,他们也许已经在想为“大赌博”打基础,争取我和他们“合作”。
把这些情况综合起来看,马克西莫维奇的处境岌岌可危。我劝他让我设法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