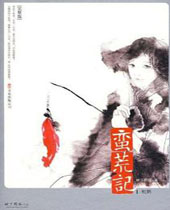汉末浮生记-第1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另几位夫人也有家信交他带来。打开一看,是丝儿手迹,字字娟秀,蕴含深情,“相公,《诗》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乱我心曲’,尽妾愁肠。君伐西戎,临战羌地,累妾等旦暮思忆,顷刻难耐。‘方何为期,胡然我念之’?妾等顿首。”
我看了几遍,只知道丝儿想我了。但其文辞华藻,却是半点不通,便传军中文牍令史来讲解。其人一看,不禁脸露诡秘笑容,道:“夫人所呈,乃秦风中‘小戎’一首,句中有‘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为期,胡然我念之’之词。”
我问道:“什么意思?”
那人见我似没读过书一般,摇头晃脑地道:“君子者,大人也。将军出征,夫人思忆挂念,言大人性情温和如玉,使心乱惆怅也……”
我老脸微臊,“出去!”把信收在贴身怀中,暗忖道:丝儿真是隐晦,写情书也要用文言文让人看不懂。若是换了小清来写,肯定是“我最最亲爱的,爱你一千一万年不变”等等,一目了然。
徐焱跪在一边,半天不见我答话,稍稍焦躁地道:“大人有何吩咐,还请示下。杨司马嘱咐小人一定要大人回话后才可离开。”
我这才省起屋内还有别人,忙回过神来,笑道:“哎呀,倒把你忘了。请起请起。还没有问你呢,近来杨速、陈林他们还都好吧?”
徐焱微微欠身,“烦劳大人关心,杨司马、陈都尉都还好。”
“你跟陈林是结拜兄弟?什么时候开始的?”
“禀大人,小人原是南郑西城戍卒,与陈都尉共同患难,情同手足。后突有一日,义兄送来书笺,称其已入颜大人麾下,而欲加招会。小人与陈都尉有死生之誓,不敢轻弃,故而投奔长安来了。蒙杨司马提拔,现忝为别部骑官。”
我点点头,心里想: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哪!现在我摇身变成大树,树下已颇有一番郁郁葱葱的小草了!怪不得古时候常有人用“盘根错结”来形容资深贵僚,依我看,这些七零八落的关系加在一块儿只怕什么样的词汇,都不够了。
第四十八章 乱世豪强
三月甲未,杨赐免,以光禄勋邓盛代。袁隗免,以廷尉崔烈代。我突然想起来,可能什么时候,我对小清说过崔烈的事情!其人乃买通灵帝的乳母,花五百万钱就买了三公之职的那个狗官。上任伊始,灵帝大叹倒霉,“少卖了五百万哩!”没想到我早当做笑话说了出去,现在历史真的发生,反倒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甲申,韩遂、边章进军酽县,烽火相望。贼众旗鼓大张,离渝麋仅有百余里路程。皇甫嵩也拔军推进,前锋终至雍县。
我立刻传令派出五路探马打听切实消息。这日清晨,司马恭怏怏不乐地来见我,卢横忙将他引了进来。
是时我正仔细盘计胜算,埋头苦思。司马恭不敢打扰,静静坐了半天,我方才发觉。忙起身笑道:“你什么时候来的,我都没感觉到嘛。”
司马恭恭敬行礼,道:“将军恐怕正想着如何挫败敌军的事情吧。”
我点点头,“是啊。你来了正好,也跟我一起想想,怎么打好这第一仗。”
司马恭吞吞吐吐地道:“在下倒有些念头,只是不知道将军能否见纳。”
我引他坐下,心想:这小子今天好像有点不对嘛,平常他的话都是直来直去的,可不像现在这么费劲,就像挤牙膏似的。正色道:“长史有话就说嘛,我们都是一家人,作甚要那么含含混混的。”
司马恭眼睛里流露出一丝担心之色,长叹起来,“在下只是有感而发罢了。西羌贼军十余万,声势浩大,而皇甫嵩以将军屯渝麋,分明是弃车保帅之举。将军若是侥幸得胜,必无余势,此时他只须分出杜阳、陈仓、雍县之守军,几路穷追,必获全胜。将军若是败了,皇甫嵩却仍可以逸待劳,以精锐之师迎头猛击,最少打个平手。而我等进亦败、退亦败,只怕难以为继啊。”
我欣喜地看着他,就像第一次认识他似的。连说了三个“好”字,道:“难得你有这般认识,我算没白教了你。现在你也知道为将的不易了吧,光要对付敌人,我已是焦头烂额了,再加上皇甫嵩等大拖后腿,这仗你叫我怎么打?”
司马恭忽地跪伏在地,道:“将军谬赞,这可不是在下想出来的。司马恭不敢夺人之美。”
我皱皱眉,道:“不是你又是谁?”
司马恭抬头看了看我,小声道:“是高敬兄弟……”
我心下恍然,不禁微微有些不悦,哼了一声,便站起身来。司马恭赶忙口不择言地解释道:“请将军恕罪,司马恭也是一心为将军着想。现在局势危急,正当用人之际,而高敬等整日禁闭冥想,于士气不利啊。他虽犯了大错,却已经痛悔前非,欲以死报将军。司马恭以项上人头担保,高敬兄弟决不敢再有丝毫违令之举,请将军宽恕!”
我来回踱了几步,刚想发作,又忖道:不如顺水推舟,卖他个人情算了。高敬既已关了不少天,想来也必会奋命以效,加上手边的确无人可用,他们三个一出来,对挽回局面大有裨益。过了很长时间,这才冷冷道:“念在长史一片挚诚,我就答应这个要求了。不过话说在前面,犯了军规不加处置,那是不可能的。高敬死罪可免,活罪难赦。你给我下去传令,命大小将领齐来都衙议事。”
司马恭高兴地应诺,又大磕了几个响头,这才离去。正整理穿戴之时,卢横在门外道:“将军,皇甫嵩的信使来了。”
我瞥了他一眼,继续系着领口,“让他也到都衙,有什么臭屁,到那里放一样的。”
卢横很是疑惑地抬头,看着我满是嘲弄的脸色,这才恍悟:“遵命!”
会议之时,诸将大多在营中操练士卒,俱是骑马赶到。渝麋县令、参军左浑第一个来到衙前。我想了想,命人取榻席请他坐在西首。这种时候,最好不要把内部矛盾有意夸张,否则定当得不偿失。
待众将会齐,先叫进皇甫嵩信使。来人是一健壮参校,取帛奉来,道:“皇甫将军命令颜校尉立刻兵发酽县救急,这是文书。”
小校接过,转呈上来。我撕开一看,禁不住冷笑起来。司马恭顿时怒不可遏地叫了起来,“什么救急,那是送死!贼势汹汹,州郡府县又有谁敢出头?皇甫嵩空白握着数万大军而不敢前来,为什么偏偏要叫我家大人去救危难呢?这里面摆的是什么诡计,一眼便看得透了!”
众人闻言也俱大怒,纷纷喝骂使者。那参校见状不妙,畏首畏尾地道:“皇甫将军只是叫小人来传话罢了,他下了什么命令,全不关小人的事。”
我挥手止住喧闹,嘿嘿笑道:“回去就跟皇甫嵩说,我颜鹰会立刻派兵北上救援,请他放心好了。”
司马恭大惊,叫道:“将军!”连鲍秉等也站出来劝止,我喝道:“都住口!来人,给我打赏,送使者回去。”
军校轰应一声,自带使者下去。我这才恢复神态,道:“你们都吵个什么,又不是皇甫嵩,对他发火有屁用?”
司马恭牙关一咬,摆出一副豁出去的架势,抱拳道:“将军,此事大大不妥呀。皇甫嵩命我军出战,分明是让我们孤军深入,正好着了韩遂等的圈套,假其手而亡我。现在将军这样轻率答允了他,难道……”
我环视众将,微微一笑,“那你让我怎么办,把使者杀了,送首级回去?”仰天打了个哈哈,道:“我才不会那么傻。现在皇甫嵩四万大军驻扎在背后,虎视眈眈,巴不得我抗令不遵呢。那时候他一封奏章发到朝廷,立刻让我等背负叛名,便可名正言顺地加以讨伐。而我等寸功未立,先入天牢,纵能分辩,也必势力大削,无复今日之勇矣。嘿嘿,他这一手,可当真是高明呀!”
众人皆都哑然,细细品味起我的话来。半晌,鲍秉道:“为今之计,将军该当派遣信使,速至京里禀报。朝廷终会有公断的罢。”
我又扫视了一眼众将,只渝麋令、参军左浑面呈不屑之态。心领神会,颔首道:“只怕左大人有些话说吧,渝麋布防精湛,又有先遣之名。各位不如先听听他的意见。”
左浑傲然出列,拱手道:“颜校尉深思熟虑,在下佩服。皇甫将军用兵,向来审慎严密,颜校尉与之深有嫌隙,那他即便不寻衅挑拨,也必定大加防范。此时吾县岌岌,而颜校尉以孤垒之势,尚且不得容,况乎其他?若派信使,等若明告于他。那时我军前后临战,安能不死?”
我见众将脸上都有恐怖之色,鼓掌大笑,“讲得好。不过依左大人看来,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左浑长揖谢道:“大人如此危急之刻,还能坐对如流,谈笑自若,真有名将风范!依在下所见,皇甫嵩此举不过欲探知大人虚实罢了。大人不加坚辞,一口应允,定然令其陷入猜疑之中。而皇甫嵩所部董卓、鲍鸿、贾琮等,计其功名,安敢加诸谶谋于虎骑?想京畿之中,权贵倾轧,而大人独以白身,加诸重号,名噪一时。谁人不知,哪个不晓?皇甫嵩加诬图构,必当徒苦其身。颜大人只需作态往援,大肆张扬,过不了几日,他必会再发军令,命大人回保渝城。”
“妙啊,妙啊!”我想了想,心想:这家伙讲起话来倒有些道理,看来有时候狗头军师还是管用的,“左大人的话真是精辟。尔等以为何如?”
大家又是一阵喧哗,交头接耳起来。司马恭道:“果如参军所说,我们暂时该当无恙。不过羌贼一日不除,我等一日不得安寝。非得想个办法,让将军脱离窘境,也好安心杀敌呀。”
我笑道:“长史说得对啊。不过现在还没什么好办法可想,只好过一天算一天了。大家回去,都要拿出几条意见来,集思广益嘛!左大人,你说是吗。”
左浑该是最明白现时处境的,也该有熟谋对付。不过时机未到,一旦决定脱困,必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我们该不该这样。对抗军帅,就已经相当于造反了。即使告到灵帝面前,我的胜算也定然不大。他微微一怔,知会地俯首道:“大人所言是极。”把刚要禀报的话强压下去。
军报一了,我立刻询问各营训练新阵形的情况。司马恭禀报有几名司马放松怠慢,我便严厉地加以处罚。皱眉道:“我不想再看到有人再敢松松垮垮,有触军纪。训练并不是为了我展开的,是为国家,为自己!训练时多流汗,战场上少流血,难道不划算吗?你们这些人不要以为我们打了不少胜仗,就骄傲自满,得意忘形,殊不知这种思想,只会让我们尝尽苦头。历史上有多少次战争,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呀,为什么强的反而不强,被弱势一方击败呢?原因就是他们骄傲轻敌!大意不得呀,各位。今日我不打你们板子,但要限期考核,达不到预定标准的,统统革职,决不姑息。还有,每人写一份检讨书,要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明天都要在各自营中宣读,我会派人监督的。”
几名司马惊出一身冷汗,赶忙谢恩退下。我突然想起刚才和司马恭谈论的事情来,瞥了他一眼,冷冷道:“前几日在漆垣战罢,给禁闭的那几名军犯呢?”
有小校答道:“都在营中。”
“给我带上来!”
高敬等三人都被剥去将领服饰,也无甚顶戴,直挺挺跪在都衙阶下。
“高敬,你可知道你犯了什么错误吗?”
他闻言叩了个头,面容悲凄地道:“大人所授军命,我没有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