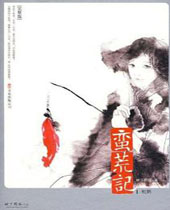汉末浮生记-第4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王越举杯饮干,朝小清看了一眼,笑道:“王越平素略有识人眼光,于陈仓马市中,看见令弟,便觉雄壮威武,他果然可以力敌十数人。可我视弟嫂,只觉平常,竟然看不出她也有那般高超的武艺,惭愧惭愧。”我微笑道:“拙荆天生异禀,所以不同常人。我的兄弟杨速,却是从小习武,力大无比,在战场上与人厮杀,敌军闻风丧胆,是我手下的第一班好汉。”
王越道:“真英雄!敢问令弟何在,怎么没见他来?”
我淡淡道:“舍弟被京兆尹张大人收为从事,现与从侄等权住长安,因此没来。”王越“哦”了一声,露出一丝失望之色,道:“令弟深具霸气,如精习剑术,可以一当百。初在陈仓之时,我便想点拨一二。”
我抱拳笑道:“如此,则真乃舍弟之福,王大哥剑法精妙,已臻化境,杨速能蒙得教授,三生有幸。颜鹰在此先谢过了。”
酒过三巡,我已饱得打嗝。会宾楼的菜蔬,如流水般上来,令人应接不暇。我肚里大叫痛快,只想一顿便把这几天受的损失统统吃回来。小清推说胃口不好,自去栏旁坐着,也无人敢于问津。王越殷勤劝酒,笑道:“我还从未这么招待朋友的,贤弟是第一人。我王越生来,便最是佩服用兵如神的将佐之才,从前听说贤弟在凉州打仗,无不是以少胜多,而终致克敌制胜,叹服甚深,只恨无缘早见。今日真是天遂我愿!能得与贤弟相聚,当畅叙三日,以解王越之疑。”
我刚要客气两句,突地楼下喧哗声起,申虎走上来,道:“王师傅,侍御史袁绍袁大人来了。”王越喜道:“是嘛!快快有请。”当下推盏而起,道:“贤弟少待,我去去就来。”我笑道:“无妨。”心中却是一跳,忖道:袁绍?!
一下子不知道转了多少念头,却又十分想见他一见。
只听楼道上王越哈哈大笑之声,一阵客套之后,便与另一人拾级登楼。我凝神望去,只见一个身材高大,体格魁梧的男子上得楼来,正与王越笑道:“……某辞叔父来此,只因不胜俗务,今天特来和王兄喝上两杯。”
当下两人执手过来,王越笑道:“贤弟,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袁本初。来来来,大家见过。”
我站起身,恭敬道:“袁大人。”便听王越向袁绍笑道:“这位是我新近结识的英雄颜鹰兄弟,有济世之才干,我是甚为敬服的。”
我老脸一红,便见袁绍走上来,抱拳施礼。其人相貌堂堂,面阔方圆,双眼有神,下颌少许胡子,倒猜不出具体的年纪。伸手与我相握,就像老朋友一般,上下打量了一番,朗声笑道:“原来是颜兄弟,久仰久仰。某平日里最是喜欢交结壮士,颜兄弟相貌不凡,又得王兄如此看重,不如大家一起聚聚,在此稍稍盘桓几日,袁某一来做个东家,二来也和颜兄弟好好聊一聊。”王越更是笑道:“正是。贤弟在京畿尚未落脚,不如先投袁大人门下,将来施展拳脚,应是大有作为。”
我禁不住心里一热,暗道:王越说袁绍能折节下士,果然不虚。我一介贫民,他就能挚诚如此……不对,袁绍他有田丰、沮授、许攸这等人才而不察其言,哪能称做挚诚!用人就要用到底,招纳了人才,不给他合适的待遇,他能为你尽心吗?更何况用人不诚,偏听偏信,更是不妙。怪不得连郭嘉这等人才也偷偷跑了。不禁犹豫起来。
袁绍见我脸色数变,以为我还在考虑,笑道:“颜兄弟似有不愿哪,来来来,喝茶,喝茶。”笑着和王越讲了几句。王越道:“贤弟,袁大人和你一见如故,深自喜欢,故而相邀,贤弟千万不要心存疑忌,倒让王越不安了。”
我考虑妥当,心中又不免好笑:袁绍官渡之战失利,也是十几年后的事情了,我害怕什么,难道刚刚竟存了为他效命的念头了?哈哈。面露微笑,道:“王大哥多虑了,我一见袁大人,便觉惺惺相惜,甚是敬重。倒不免猜想,我一介布衣,可没有私人袁大人府邸的资格。”
袁绍仰天大笑,道:“颜兄弟过谦,过谦了。某也自闲散惯了,这些日子方人朝为官,因此深知绿林草莽,实乃是藏龙卧虎之处,能聚敛英雄、豪杰于门下,当有昔日孟尝之风,每念至此,不禁得意忘形,而必欲达先人之神采也。”
王越也自大笑,附掌道:“袁大人果然是丈夫气概,若能收尽天下英雄,则囊括四海,易如反掌尔。”
我装作愉快的样子呆笑,一面心道:袁绍把自己比做战国四君子,岂不是要追求“食客三千”这层面子吗?给人吃饭,不让他发挥才干,还不是形同虚设一般?转念又想:在袁绍手下谋职,绝非长久之策,只因我已看破了他,其一言一行,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往坏处考虑,和讨厌的人在一起,也会变得越来越犯嫌,而最终将被自己的感觉所淹没……不禁暗暗好笑,听他们如何答话。
袁绍闻王越之言,摆了摆手,正色道:“此话万不可轻言,某未应辟命之时,中常侍赵忠便与会诸阉,言某‘坐作声价,不应呼召而养死士……’哼哼,若王兄这话被他们听到,袁某项上人头不保。”
正自闲谈,忽闻楼外有喧闹之声,众人皆是一怔。片刻,申虎满面惊慌地上楼来,,在王越耳边嘀咕了两句。王越脸上失色,急忙随申虎去了,连招呼也忘记打。袁绍不大高兴地道:“是什么事?颜兄弟,我们也去看看。”
我应了一声,袁绍便像老朋友一般搀着我的手径自下楼。我想甩开手,又觉不大礼貌,只得心中暗道:袁绍千万别是个同性恋,要不然我可惨了。这个时代,对于这类问题,可没什么明显的界限。悻悻地回头看去,小清一双眼,正笑眯眯地盯着我,似在说:“跟男的牵手可以,跟女的牵手不可以!”
方自走到楼下,便听楼外叫骂之声尤重。袁绍跨前两步,突地又停住脚,抽了一口冷气,道:“不好,是张让的车马!颜兄弟——”
我趁势甩开他的手,心道:张让(@!*#)!妈的,今天一天过得真是迷糊,什么不该见的,都见了一遍。赶明儿一定要在洛阳城翻个底朝天,把曹孟德这小兔崽子搜出来。
抱拳道:“将军何事吩咐?”
袁绍手足无措地道:“无事无事,唉,我们有麻烦了。
张让此人,素来对我袁家不满,自太傅、司徒以下‘,无人不曾被其欺侮。他若是见我在这里,定会在皇帝面前说三道四,则某家危矣。“
我凝神静气,只听到门外有人尖着嗓子叫骂道:“好大的胆!张大人的车驾,也敢挡吗?你莫非不要性命了。”紧接着王越的声音道:“请大人恕罪,楼前车马停得太多,我这就着人移去。小的怎么敢惊阻张大人的车驾!”心道:张让不过是一个太监,就这么要风有风,要雨有雨的,威风得不得了。若索性变态一番,那还了得!暗暗好笑,装作慎重的样子道:“依将军看来,当如何是好?”
袁绍道:“我怎么知道?”叹了一口气,连连搓手,“看来只得上楼先去避一避,但愿张让没看到我才好。”
我刚欲答话,袁绍已然甩手上楼,还不住抱怨自己运气不好。心里不由得苦笑:一个太监就把他吓成这样,也不演戏了、也不搀手了,就只是光顾着老命了。若来个比张让再大一些的家伙,恐怕他得打个洞躲下去了。缓缓在厅旁坐下,众食客有的早已惊得面色苍白,还以为张让下旨来砍他们的脑袋哩。
只听楼外那尖声尖气的声音又道:“王越,你的面子可真不小,这许多车马,都快比过我们大人的侯府啦。”王越道:“不敢。王越不过是一介布衣,朋友虽多,却没几个王公大臣,怎敢与张大人相提并论!”
那尖利的声音怒道:“王越,你竟敢放肆!你屡次藐视张大人,叫你人宫也不愿,叫你人府也不愿,你到底想干什么?想造反么?”王越沉声道:“在下虽无职司,但忠于朝廷,日月可鉴。我不愿人宫,实有不得已之处,大人体察下情,自会原谅在下。”那尖嗓子的家伙叫道:“好你个王越。你今天强阻大人车驾,到底是仗着谁的势啦?来人——把他给我捆起来,我倒要看看,谁敢出头救人。”
此人这几句话,其实色厉内荏之至。京畿王越,声名不凡,会宾楼藏龙卧虎,人才济济。要是这时候动起手来,不知道谁会输呢。此时申虎等一班弟子,此时已都冲到楼外。
我默忖道:王越必不会动手。此事该由张让占据上风。
果然,王越喝道:“你们都退下去,这儿没你们的事。”申虎呼呼喘气之声,也听得清清楚楚。我见外头的局势一触即发,手心里不由得捏了把汗,起身便要出楼。忽地,一人的声音慢慢道:“慢着,何必为了一点小事大动干戈呢……”
我松开拳头,走出门去。正见面前停着一驾马车,紫盖,黄椽,轮柚红色。车顶一束五彩斑斓的鸟尾,披舆前方,还左右挂着两串金制风铃,极尽奢靡。一人从车中缓缓步出,马上便有仆役跪倒,那人便高傲地踩着其背走下。
我心里“哼”了一声,见张让年纪也不算大,穿一身蜡色宫袍,戴方冠,腰缠玉带。个头很矮,背着手、抬着头,那旁边的小于便屈腿躬腰,显出比他还矮的样子,笑道:“大人,您也别太大度了。这么就饶了他,未免……”
张让“哼”了一声,摆摆手令他退开,两眼忽地冷冷看着王越,“我若跟他计较,还不让人说了闲话。这一回我们便算了……”眼光一斜,突地停住下面的话,脸上肌肉一牵,放开了声音道:“那是谁的车子?”
张让手底几个小厮慌忙去楼前查看。过不了一会儿,便回来在张让耳边密报。我见王越脸上神色大乱,知道必是袁绍的车马无疑。心中不由得犹豫:若这呆头鹅有难,我到底是救呢,还是不救?
张让的脸变得青青的,呼呼地喘了半天气,才尖着嗓子叫道:“袁绍,袁绍!你给我下来,袁绍!”
我吃了一惊,心道:张让是不是想杀人哩,这般大呼小叫的……他和袁绍有什么关系,难不成是仇家?念头还没转完,只见袁绍魂不附体一般从楼上跑下来,出得楼来,大礼参拜张让,“袁……袁绍见过张大人。”
张让指头几乎戳到了对方的鼻子,“你……是你……你在会宾楼上干什么?”
袁绍道:“我,我只是偶然经过会宾楼,因此上去坐坐,消遣而已。车马,车马阻挡了大人行路,望,望请大人莫怪。”
张让手一挥,道:“原来是你在看我的热闹!好,好得很。你一个小小六百石的侍御史……嘿嘿。”一转身便要上车,那小厮不解地道:“大人,就这么算了吗?也太便宜他们了。”张让挥手便是一个嘴巴,把他打得吐出两颗门牙,这才怒气不息地登上车,尖声叫喊:“走,快走哇!”
张让的卫兵连忙在前开道,将一千行人、车马蛮横地统统赶到一旁,官队便急匆匆地离开了。王越缓缓摇头,走上前道:“真是抱歉,王越令将军受累了。”
袁绍只是叹息,良久方道:“非是王兄之过。张让这人,当真捉摸不透,脾气怪异,常常不知为何,便触怒了他。”
我心里雪亮,忖道:这帮阴阳人个个都这样,一会儿便发嗲,一会儿又转脸不认人。他们的话,全没一句是可信的。张让这厮,只怕还是好的,若到了明朝、清朝,那才不得了呢。又自好笑:今天袁